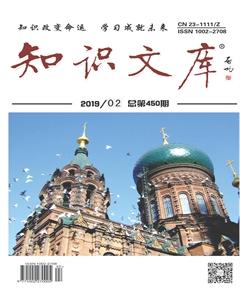傳統文化型旅游景區問題和對策
張江凌
在改革開發初期,傳統文化景區是旅游市場的主流,但隨著消費需求的變化和大量主題鮮明、特色突出的新景區不斷涌現,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傳統文化景區開始面臨強力挑戰。從很多方面反映了一些問題,那么如何針對問題制定相應的對策呢?
1 傳統文化型旅游景區問題
1.1 難以擺脫的“一次性”經濟現象
傳統文化型景區一般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文化影響力,對于遠程游客具有一定的感召力,許多游客都是“慕名而來”,觀光之后覺得“不過如此”,來一次也就夠了,不會再來第二次或更多次。甚至一些曾經是一個地方的“必游景點”也對初次到來的游客缺乏吸引力更談不上重復旅游。而本地的游客由于受到旅游求新、求異的動機的影響,一般也不會重復去一個只有簡單觀光性景點而沒有休閑娛樂產品的景區。如桂林的蘆笛巖景區、三亞的天涯海角景區,曾經都是國內外游客的必游景點,但隨著周邊大量休閑娛樂和度假景點的開發,接待游客從90%以上下降到60%左右。
1.2 表面的繁榮與入不敷出尷尬
傳統文化型景區多數還是單一的門票經濟。在旅游旺季游客量雖然大,但由于盈利模式單一,游客的疊加性消費支出少,所以景區的經濟效益不高。
1.3 難以放下的“厚重”歷史包袱
多數文化型景區都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有說頭”,但厚重的文化如果沒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和表現,就很有可能曲高和寡,游客看不明白,往往來時興致高,結果卻是在歷史的長河中迷失。很多地方講自己的文化是“中國最早的”、“中國第一”、“××文化的發源地”等等,談起來津津樂道,但游客卻不得其樂。
1.4 保護與開發“平衡木”上獨舞
很多文化景區都是珍貴的文化遺產,也有一些在爭取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以進一步地吸引國際游客,這反映了文化經營和管理部門對文化的重視,是一種進步。但對于文化遺產如何進行旅游開發卻缺少創新的思路,一方面是嚴格的保護,反對旅游開發,這是一個極端;另一方面是以文化遺產為旗幟進行大體量與遺產主題毫不相干的開發,這是另外一種極端。
1.5 艱難的空間拓展挑戰
我國多數文化型景區位于城市(城鎮)的中心,周邊用地條件受到限制,或者周邊的建筑風格與景區文化品位差異很大,致使空間萎縮,旅游冷清,缺少發展的戰略空間。比如很多城市內的文化名勝等。
1.6 迷茫的時尚陷阱
受到新型消費需求的沖擊和一些新建景區的影響,“傳統對接時尚”成為傳統文化景區文化旅游開發的一種主要策略。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時尚是變化很快的東西,很多景區在對接的過程中過分強調時尚,而忽視自己本身的文化特色,缺少清晰的定位和穩定的品牌形象,不知不覺間讓游客敬而遠之。
2 傳統文化型旅游景區的對策
事實上,傳統文化型景區的發展正面臨著很好的發展機遇。一方面,政府對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的大力支持為文化景區的發展提出了一個新方向;另一方面,從全球市場來看,文化旅游在游客心目中備受青睞,世界上最有特色的度假勝地無一不具有特色的文化。
那么,國內的傳統文化型景區應該如何做才能重現輝煌?除了我們經常所講的豐富產品、加強營銷、品牌化經營等方面,筆者認為還有以下幾個方面:
2.1以休閑驅動觀光
傳統文化型景區除了重視對遠程觀光游客的形象推廣外,更要重視對近程休閑度假和文化娛樂型市場的推廣,開發針對家庭周末休閑度假、情侶休閑娛樂、青少年知識教育等休閑度假產品。文化休閑策略利用得比較好的景區很多,如上海楓涇古鎮的水鄉婚禮。
2.2以品牌提升價值
國內的景區越來越重視品牌的力量,一些文化景區品牌也正在成長,如三亞南山佛教文化苑等。以品牌提升價值需要以景區品牌建設為核心構建品牌價值,注重對近程可能發生重復性旅游的游客的開發,為景區進行清晰的品牌形象和主題定位,豐富產品功能,完善配套設施,提升旅游服務,并利用知名度優勢建立品牌優勢。
2.3以體驗打動人心
體驗式營銷是文化型景區最有效的營銷方式之一。越來越多的景區在以其特色文化為主題開展以游客體驗為導向的營銷,如少林寺的各式各樣的武術表演。不僅如此,體驗營銷還能創造出新的盈利模式,從而構建景區更豐富的產業鏈,如演出活動的收入、印象制品和特色商品等都可以豐富景區的收入。
2.4以產業發展經濟
利用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拓展文化產業鏈,在這方面上海的創意產業已經聞名全國,利用舊的倉庫、廠房等設施通過引入文化藝術產業而創造出新的產業發展模式。新天地以時尚消費文化與上海傳統里弄文化和紅色文化相復合創造出的“新天地”模式也迅速為其它城市文化發展所效仿。
文化創意產業園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重要載體和依托,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對旅游業的貢獻業極為突顯。國內各城市紛紛根據自身優勢和特點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園,園區的發展模式可分為政策導向型、藝術家主導型、開發商主導型、資源依賴型、成本導向型及環境導向型六種。國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呈現出速度快、數量多,投資主體多元化及中小型民營企業為園區主體的發展特點。
2.5以經營盤活資產
景區也是企業,雖然其產品不像一般制造型企業那樣看得見摸得著,但是性質還是一樣。然而卻缺少一般性企業的靈活機制,歸口管理部門多,難以協調。目前在景區經營機制方面的探討比較多,也正在實踐。一般來講,市場化程度高的企業化經營機制有較多的成功案例。
3 結論
在我國建設世界旅游強國和“大國崛起”的進程中,中國文化世界化的潮流勢不可擋,文化型景區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遺存和載體體現是文業界最看好的“潛力股”和“績優股”,而如何抓住機遇,通過產品的轉型、復合盈利模式的導入、產業平臺的架構等手段的綜合運用建立動態的核心競爭優勢,就是文化型景區贏得未來的關鍵。
(作者單位:承德廣播電視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