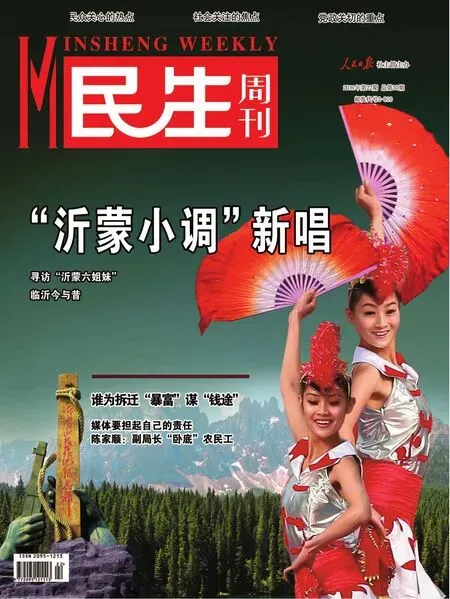陳家順:副局長“臥底”農民工
□ 本刊記者 趙志偉
陳家順:副局長“臥底”農民工
□本刊記者趙志偉

陳家順在工廠與女工交流。圖/受訪者提供
他先后5次在浙江義烏附近工廠“臥底”做“農民工”,帶出了7000多名務工人員,其中不乏做到了管理層的工人,甚至有人通過外出務工已經做上了小工廠的老板。
他身兼云南省曲靖市駐義烏工作站站長、沾益縣勞務產業辦副主任、沾益縣勞動保障局副局長、沾益縣駐義烏工作站站長4個職位。多年來,奔波于義烏、沾益兩地,開展勞務輸出工作,至今如此。
他自認為“我是做小事的人,做不了什么大事,所以只能踏踏實實做好小事。”
他叫陳家順,現任云南省曲靖市沾益縣勞動保障局副局長,主管勞務輸出。他因“臥底”而成名,也有人說他是作秀。“如果這樣也叫作秀,那我們歡迎多幾個這樣作秀的官員。” 來自沾益縣的民工徐樹榮曾如此評價陳家順。
義烏上任,輸送家鄉民工
沾益縣位于云南省東部,曲靖市中部,自古有“入滇鎖鑰”之稱,是戰略要地。自1997年沾益恢復縣制以來,經濟實現了快速發展。2004年,沾益縣委、縣政府提出把農村勞動力轉移輸出作為農民增收的一項產業來抓。
“為有效解除外出民工‘怕上當受騙、怕找不到工作、怕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的心理,縣委、政府決定在省外用工量大的地方設立一個專門對外出民工進行跟蹤服務和維權的工作站。通過考察,2007年,沾益縣在著名的小商品城——浙江義烏建立了云南省首個駐外省勞務工作站,我是首任站長,當時的首要任務就是如何把家鄉政府組織輸送過來的民工兄弟穩定好。”陳家順說。
事實上,早在2004年,原本擔任中學校長的陳家順,就被借調到縣里的勞動局出任就業中心副主任,負責沾益縣的勞務輸出工作,“我原來是個教師,沒有想過仕途,我現在的官職是偶然中得來的。”此后,陳家順組織鄉親們到廣東、浙江等沿海經濟發達省份打工。
“當時的壓力很大,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們不能有效穩定民工,導致他們乘興而來,痛苦而歸,這不僅給他們經濟上造成極大的損失,心里投下陰影,還會影響到政府的公信力。”陳家順說,“但是,你怕哪樣就來哪樣,首批輸送的民工情緒波動很大,反映說企業的情況不像我們宣傳發動時說的一樣,還有很多民工說政府與廠家合伙騙他們。”3年下來,情況不盡如人意,“由于我縣勞動力自身的素質和珠三角用工企業存在的種種問題,我們省內轉移很成功,省外的輸出工作卻在很長一段時間處于被動狀態。”
2007年春節過后,縣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帶隊,陳家順隨行,一行人專門到長三角考察勞務市場。一圈下來,考察組分析認為,義烏等地用工量大,對員工素質、年齡都放得寬,“與我縣勞動力素質基本相匹配”,遂決定設立義烏勞務工作站,陳家順走馬上任。
“臥底”企業,邊打工邊考察
外派的站長陳家順,當時手下只有一名縣里的警察。剛到義烏,便首戰失利。陳家順考察推薦的廠子,老鄉們不滿意,當年的返鄉率高達60%。這逼著他不得不去“臥底”打工。“當初進廠打工時,腦子里根本就沒有閃過‘潛伏’這個詞,也沒想到會引起社會的關注,更沒想到自己會出名,僅僅是想把企業的用工情況搞個清楚明白,把務工人員在企業工作、生活中產生的想法、遇到困難的情況搞個清楚明白,以便我們在宣傳發動時說得真實、準確、全面,在做民工思想、解決民工困難時能有的放矢。”陳家順說。

陳家順(右二)在醫院探望工傷病人。圖/受訪者提供
陳家順選擇的第一個企業是一個飾品企業,因為飾品企業不同性質的崗位多,對員工的知識、技能、年齡、性別要求都不高,能接納沾益縣大批量年齡差距大、文化程度低的農民工。“真正當了農民工,完全按照要求做下來,才真正體會到農民工的累。”陳家順說,“我所進的企業每天工作12個小時,除去早晚吃飯時間,在車間的時間整整11個小時,遇到廠家趕貨,時間就更長了,有時會達到14至15個小時。做了一個月,我還了解到員工請假、辭工特別難,車間幫派體系嚴重,基層管理人員、老員工對新員工態度也不好,我覺得我們家鄉的員工肯定吃不消,就撤出來了。”
第二次,陳家順選擇了一個只有200多人的小型飾品企業,也是做了一個月。“這個企業的硬件環境比第一個企業差了很多,但工作時間短,每月都有1000元的保底工資,請假也好請,辭工也相對容易,做了一個月我出來后,介紹了22個人進去。”
2008年9月,“家鄉的幾個50多歲的民工要過來,這些人在土地上耕種了一輩子,聽說義烏打工還行,就一門心思要過來,我當時想,這些人大字不識一個,除了干農活,其它什么技能都沒有,年齡又大,進廠肯定吃不消,但已經下定決心要過來,你勸也勸不住。如果沒有幫他們找到合適的工作,就必然造成他們經濟上損失和精神上的打擊。針對他們的實際情況,我選擇了一個大型養殖場當飼養員。”陳家順說,這次“臥底”養豬場,是第三次,“剛進去時,主要是氣味受不了,我飼養的又是病豬欄,經常要處理死豬。開頭幾天處理死豬時,常會嘔吐,吃不下飯去,但一個星期就挺去了。后來,我介紹11個大齡民工進去時,他們嫌臟嫌臭,嫌沒面子,我給他們講了我的經歷,告訴他們這最適合他們。”
第四次“臥底”是在2010年。“2010年,我們組織的輸出人員中,90后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他們的吃苦耐勞精神無法跟60、70、80后的人相比。如果一天工作12個小時、沒有周末和節假日,他們肯定做不下來。但在揚州的工作時間較短,勞動法執行得較好。”就這樣,2010年3月,陳家順帶了80多人到揚州的寶億制鞋廠打工,這個廠每天的正常工作時間是8個小時 ,加班最多也不會超過10個小時,正常情況下都有雙休日。“即使是企業生產高峰期,都能保證周末、節假日休息。我帶進去的員工除了嫌工資低點外,其它都還很滿意,現在這個廠跟我們合作得很好,到現在,我們有近400人在里面工作。”陳家順說。
2010年,夫妻倆到義烏打工的增多了,小孩上學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加上沾益縣人事局和勞動社會保障局合并的事已經開始,大中專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又成了我們的一項重大工作。于是,我選擇了去義烏最大的民工子弟學校教書。一個月后,我對學校的教育教學管理有了整體認識,就介紹了3個家鄉民工孩子進去讀書。但教師工資太低,就沒有介紹大學生進去就業了。”這是陳家順的第五次“臥底”歷史。
星火燎原,務工隊伍壯大
這些年,陳家順5次“臥底”,先后帶出了7000多名家鄉的勞務人員到外省打工。“對義烏及周圍城市、我們跟蹤調查的比較多的是揚州市,但對轉移到蘇州、上海、山東的人員我們就沒有能力跟蹤調查了。據我們的跟蹤調查,在義烏、揚州工作一年左右的,月工資大多數在2000元左右,成為技術工和管理人員的,月工資一般在3000元左右,少數人員月工資在4000元以上,但也還有一個月1500多元的。”陳家順說,“年齡在40歲以上的,適合在義烏小一點的工廠就業,因為小一點的工廠管理相對寬松自由,工作時間長,工資也高一些。但對年輕一些的、有一定文化知識的人員來說,最好還是去管理規范的、技術含量高一些的企業就業。”
2010年,沾益縣實現勞務收入4.5億元。“在義烏建立工作站之前,出去的人已經很多了,但長期穩定在一個地方的人很少,外出務工情況怎么樣,老百姓心里總沒有個譜。建立了義烏工作站之后,長期穩定在一個地方的人多了,外出務工收效如何,老百姓看得就很清楚了。義烏在我縣的勞務產業發展過程中,承擔了一個典型示范帶動作用。可以說,沒有建立義烏勞務工作站,我縣勞務產業絕對不會有今天的規模、效益和影響。”陳家順說,“2011年勞務產業收入計劃是5個億。”
陳家順的“臥底”經歷,不僅帶動了沾益縣的勞務產業收入大幅增長,而且,跟他出來的打工者,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思想變化是最大的。不少曲靖出來的人,依賴心理較強,無論是小問題還是大困難,總想等著別人來解決。”陳家順說,“我們2007年帶出來的一個民工叫徐樹榮,剛出來的時候對我們說,我跟你們過去看看,好干就干,不好工就回來種地。現在,他成了一家五金廠的技術骨干,現在常對剛過來的家鄉人說,如果抱著干干看、不好干就轉的思想,肯定干不了,因為沒有什么事開頭是好干的。只有下定決心,耐著性子干熟了,什么都會好干的。”
除此之外,“言行變化也很大。有些人員剛來時,說話不注意禮貌,做事我行我素,不講衛生,煙頭廢物隨地亂扔,現在說話文明禮貌用語多了,也會講究個人和公共衛生了,做事能考慮企業和他人的感受了。”陳家順說,“再就是形象變化大,特別是年輕女性幾乎判若兩人,皮膚變白晰了,穿著講究了,氣質變好了。”
截至目前,陳家順還是義烏、沾益兩地奔忙,“義烏及周邊城市、揚州企業實地考察、合作洽談,民工的安置、跟蹤服務、維權,家鄉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宣傳發動、組織培訓、輸出護送主要是以我為主。”陳家順說。
陳家順“自降身份”的5次“臥底”經歷,在別人看來是一件奇聞,其實更有許多外人無法理解的“臥底”背后的辛酸。
“我最艱難的是2007年。我家只有一個女兒,那時孩子上初一,情緒波動較大,叛逆心理較重,我妻子那年身體又多病,根本管不了她。”陳家順說,“2008年以后情況就好多了。妻子現在也在義烏工作站,她一年有2/3的時間跟我在一起,相互之間的照顧也沒有多少問題了。”
“一個人的名字就像一個商品品牌,我要的品牌就是實用、誠信。當別人提到我時,說我這個人做事踏實,對人真實,就是我要追求的境界。”成名后的陳家順坦言,“我喜歡做實事,組織給我什么平臺,我盡力去把它做好、做實就是了。”
□編輯尹麗麗□美編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