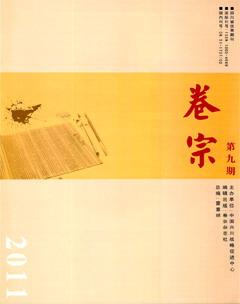為科學與宗教關系史正名
楊戀潔
摘 要:本書的直接目的在于對科學與宗教的關系作出事實性陳述和總結。作者從二者紛爭的源頭開始,以史實為基礎,對二者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關系進行客觀的還原,按照時間順序,選取科學與宗教(或者說理性與信仰)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事件為切入點,對二者從古至今關系的發展與變化作出詳盡的說明。最終,通過對這些史實精確而完備的敘述,意圖向讀者展現科學與宗教關系史的真實面貌。譯者對此書進行翻譯,目的在于為我國的相關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自然哲學;基督教;科學與宗教;理性與信仰
一、本書目的
長期以來,科學與宗教都被視為對立的兩極,水火不容。近年來,隨著科學與宗教等相關領域領域學者們對話、交流的增加,有關二者關系的研究在西方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理論體系。相比之下,我國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才起步不久。因此,《科學與宗教——從亞里士多德到哥白尼》一書翻譯、出版的目的,便是要通過研究西方學者對于科學與宗教關系的探索史,為我國的相關研究提供借鑒。
二、從宏觀視角看科學與宗教
首先,作者對“從亞里士多德到哥白尼”這一時間的截取作出了解釋。以亞里士多德作為開端,是由于他是真正開始科學與宗教對話的人,甚至使他的老師柏拉圖都相形見絀;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發表標志著中世紀世界觀走入末路,因而成為本書的結尾。
從自然哲學的角度來看,亞里士多德作為這段時間之內科學和自然哲學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的自然哲學對于科學和宗教的關系最為重要,它一方面被宗教人士用作解釋世界的工具,一邊又與宗教世界關于世界的由來及運轉的觀點相矛盾。
從宗教的角度來看,以西方宗教界的中流砥柱——基督教為例,它崛起于羅馬帝國時期。這一時期人們對于科學的貢獻僅僅是促使其發展和進步,并未有突破性進展,所以基督徒所使用的科學,仍然可以說是來自于希臘時期的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
那么,看似和平共處的二者,又是為何開始針鋒相對呢?本書第四章(基督教最初的6個世紀:基督教對希臘哲學和科學的態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盡的分析。
三、基督教的勝利
基督教在其形成初期并未對希臘科學體系表現出直接的排斥,而是以它為工具來幫助解釋“六日創世說”。相對的,很多自然哲學家也吸收了宗教教義的某些觀點,用來解釋自己所看到的世界,特別是一些超自然現象。但這種相互借鑒的融洽局面隨著狄奧多西大帝將基督教定位羅馬帝國的國教而終結。自此以后,任何與基督教相悖的組織,無論其屬性是科學的還是宗教的,都被視為叛逆受到壓制,其中尤以科學為重。
首先,在基督教中,上帝在六天之內創造了世界。希臘科學和哲學體系從未認同這一說法,而是本著哲學的根本精神——理性的批判對這一觀點進行反對。盡管這并不針對基督教,但在基督教剛剛站穩腳跟的時期,它理所當然成了為教徒們的眼中釘。
另外,懷疑是科學進步的必須態度,但基督教需要的是虔誠信奉。因此,作為科學和宗教的兩大代表,希臘科學和基督教從根本原則和研究態度上都南轅北轍。盡管希臘科學長期以來占據著統治地位,但也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和基督教的傳播,漸漸擁有了越來越多的反對者--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們對科學的態度源自于希臘和拉丁時期的教父。他們大多明確地排斥科學和哲學,總試圖證明它們的缺點、證明基督教的可靠。即便是最溫和的態度,也認為自然哲學的唯一用處在于解釋《圣經》與神學。這就是著名的“婢女傳統”。
隨著基督教的廣泛傳播、教徒的穩健增長,“教會”這一組織機構逐漸形成。最初,教會人員的任命權在王室手中。通過十二世紀初的“教廷革命”,教廷從國家政體中獨立出來。隨著權利的回歸,教廷迅速地發展成為一個強大、集權化的官僚機構。這更為宗教的發展以及對科學的壓制提供了堅實的后盾。
四、“理性至上”思潮的崛起
基督教的傳播不會一帆風順,教廷的權威也不會長久地凌駕于科學之上。
公元814年,查理曼大帝去世。日耳曼人和維京人在入侵羅馬帝國之后,逐漸安定下來,經過五到十世紀的大融合,徹底與本地民族融為一體。在這場民族與風俗的大融合中,對于科學與宗教的關系來說最重要的變化是人類思維的轉變。
1、思維方式的轉變
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人口的急劇增加、商業活動的繁榮、貨幣的進步等等,都是人們的思維方式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開始對理性和合理性進行高度強調。
理性是一種批判性思維,它要求人們對一切進行邏輯分析,接受合理性、批判和改善不合理性。這其實是在向所有權威提出挑戰,包括科學和自然哲學,當然也包括教廷權威。由于科學和自然哲學本身便是以“懷疑”和“批判”為發展動力,強調“無條件信仰”、“神圣不容侵犯”的教廷權威,便首當其沖地成為了眾矢之的。
另外,在十一世紀末,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命令大教堂和修道院建立學校以培育有文化的牧師。這些機構為神職或非神職人員提供了免費的教育機會。這一舉措為理性思潮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2、思維內容的轉變
11世紀末期,野蠻人入侵、新歐洲形成的歷史階段進入尾聲。西歐人成功地將托萊多和西西里兩大學術中心據為己有,大量的科學、哲學文獻被翻譯成西歐的學術語言:拉丁語。與此同時,由教會創辦的教會學校也逐漸演變為享有自治權的大學,有能力將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著作納為基礎教材,自然哲學和邏輯學逐漸成為全歐洲的學者的必修課。
對此,宗教勢力不再對自然哲學強硬壓制,改用“定罪”的方式來進行反擊。1277年3月7日的巴黎大定罪中,坦皮埃主教給自然哲學界219條論題定了罪,其中任何一條論題的支持者都將被驅逐出教會。但自然哲學的學者們一心研究物理世界,在1272年強制所有人文學院的成員們起誓在研究中避開神學問題。若無法避開,則遵照宗教信仰予以解決。
由此可見,在這一時期,科學與宗教的關系仍是針鋒相對充滿敵意的。
五、塵埃落定
隨著理性思潮逐漸深入人心,神學家們逐漸發現自己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不可避免使用自然哲學原理。盡管他們意在利用自然哲學對神學進行合理的解釋,但他們努力的必然結果,是促使科學與哲學在人文學者被禁足的領域中融合起來。
相比之下,自然哲學所研究的對象是是物理世界,與神學無甚關系。因此,神學對自然哲學的研究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唯一貢獻只是由于自身以“解釋”為研究方法,促進了邏輯學等分析性學科的發展。
至此,科學與宗教的關系史可以歸納為由相安無事,到宗教勝利,再到理性思潮帶來的相互交融。本書的主要內容已完結。接來下,作者又對空間線索進行了補全。
六、三個文明世界
在中世紀晚期,約公元1150~1500年之間,存在著三個文明世界——西方拉丁語世界、拜占庭帝國與伊斯蘭世界。是何種原因,使得科學與宗教的交流和融合發生在西歐世界,而不是自然哲學的起源地——伊斯蘭世界或者是希臘正教的家鄉——拜占庭帝國呢?
第一,拜占庭帝國實際上是羅馬帝國的直接繼承者,也繼承了羅馬帝國的動亂與戰爭,使得科學與宗教的發展處于停滯狀態。另外,拜占庭帝國政教合一的的制度不僅不利于宗教的發展,還使得皇帝有權關閉柏拉圖學院,迫使大量學者離開拜占庭帝國。
第二,伊斯蘭世界同樣實行政教合一,但伊斯蘭教的地位要遠遠高于基督教在拜占庭帝國里的地位。因為伊斯蘭教有著自己的軍隊,他們的目的就在于征服他人,并使這些被征服者信奉伊斯蘭教。另外,哲學家們在伊斯蘭世界中是最底層的學者,自然哲學也成為底層學科,完全被踩在宗教腳下,只有在對宗教有益時才被拿來使用,從未性成果任何學者群體、研究方法或學術體系。
綜上所述,科學與宗教的交流與融合最終發生在了本章中所提到的第三個世界——西方拉丁語世界。本書內容到此結束。
七、線索梳理
縱觀本書內容,科學與宗教的關系史可總結如下:
1、在亞里士多德所處的時代,科學與宗教并沒有明確的劃分,更沒有尖銳的沖突,相安無事。
2、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宗教開始占據上風,視自然哲學為“婢女”,向其施壓。自然哲學家們則希望能避開宗教問題,潛心研究物理世界。
3、十一、十二世紀開始,歐洲興起理性思潮。自然哲學開始受到熱烈歡迎,獲得相當大的進展。基督教仍視其為眼中釘,采取“定罪”的形式繼續對它施壓。
4、十四、十五世紀,理性思維站穩了腳跟,自然哲學因此而獲得廣闊發展空間。宗教界不得不使用自然哲學原理來解釋神學問題。
5、與此同時,在拜占庭帝國,戰爭阻礙了一切發展;在伊斯蘭世界,宗教占絕對統治地位,自然科學毫無進展;但由于政教合一,神學也無實質性發展。
6、到了十五世紀,科學與宗教的關系基本塵埃落定——科學為宗教提供了解釋世界的工具,深深滲入其中;而宗教對科學的發展幾乎毫無影響。
八、啟示——為科學與宗教正名
本書以大量史料為基礎,以時間為線索,詳盡地敘述了科學與宗教的關系史,對于二者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發展狀況以及相互關系進行了客觀的還原。
閱讀此書,有以下三點意義:
1、本書對科學與宗教各自的發展歷史有了客觀、系統的了解,其中還包含著對二者發展過程中重大事件的詳細論述。
2、本書以史實為基礎,撇開世俗觀念,對二者的發展進行了客觀而詳盡的論述,特別是對于二者發展史上的幾個轉折點進行了細致的說明與分析。
3、本書中作者幾乎并未給出個人的主觀見解,為讀者留下了廣闊的思考空間。
筆者在閱讀此書的過程中,對于科學與宗教的關系也有了全新的認識。
第一,科學與宗教同根同源——解釋世界的不同方式。
科學與宗教都起源于古希臘時期,來源于古代學者們對自身、對人類社會和宇宙的探索。雖然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存在徹底的分歧,但都是人們解釋自己的存在、解釋世界的存在的方式。
第二、科學與宗教的矛盾所在——懷疑與相信。
二者最顯著的不同之處在于,科學致力于通過精準的研究方法,通過研究物理世界所發生的客觀現象,來解釋人類的客觀存在、解釋人類所生存的物理世界;而宗教則致力于從信仰上解釋人類的由來以及世界的存在與發展。
科學的本質決定了,學習科學知識的意義在于以客觀性為衡量標準、以精準的科學方法對我們已掌握的知識進行檢驗,以達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的目的。因此,“懷疑”是科學發展的動力。
而宗教自從其產生開始便以多種教派的形式存在,它們獲得發展的前提是讓教徒虔誠地信奉本教派的教義。因此,宗教發展的動力,在于“相信”。
因此,二者發展的原則和動力是完全相反的,這也是二者的根本矛盾所在。
第三、權利對科學與宗教關系的影響。
在沒有外力干擾時,科學與宗教用自己的方式解釋世界。雖然多有分歧,也仍都以不同的方式傳播著,并沒有產生針鋒相對的矛盾。但由于基督教成為國教,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以“相信”為原則的宗教對以“懷疑”為原則的科學發起了壓制,這才使得科學與宗教陷入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也使人們對二者的關系形成了固定的印象。
第四、理性至上。
作為有智慧的生物,人類對自身和對世界的探索欲與生俱來,不可停息。因此,人類從根本上講,是理性的生物。無論是科學還是宗教,無論用什么樣的方式解釋這個世界,解釋人類的由來和發展,都必須要經得起人們理性思維的檢驗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
所以,宗教在理性至上的思潮中,漸漸開始采用科學的方式來解釋自己,科學深深地滲入其中,使宗教成為一門分析性學科;而科學的發展只是受到過宗教的壓制而有所阻滯,并未受到實質性影響。
綜上所述,科學與宗教從本質上講,是人類解釋世界的不同方式,雖然存在著矛盾,但并不足以未針鋒相對。但受到歷史事件的影響,在權利的驅使下,宗教與科學的矛盾才開始激化。現如今,科學與神學都已經成為了擁有完整體系的學科,二者的發展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而進步著。
由此可見,不僅是科學與宗教,無論是哪種學科、哪種思維方式占據主導地位,都不如人類在了解世界的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求知欲來的重要。相比于學科之間的較量,更值得人們尊重和學習的,是人類對自身、對世界的積極探索和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
參考文獻
[1]B.C.謝苗諾夫,鄭鎮.科學與宗教:相互關系、對抗與前景[J].世界哲學,2009,(1):134-151
[2]徐艷梅.科學和宗教:從對立到對話[J].江蘇社會科學,2004,(4):49-53
[3]格蘭特.科學和宗教:科學與宗教:從亞里士多德到哥白尼[M].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