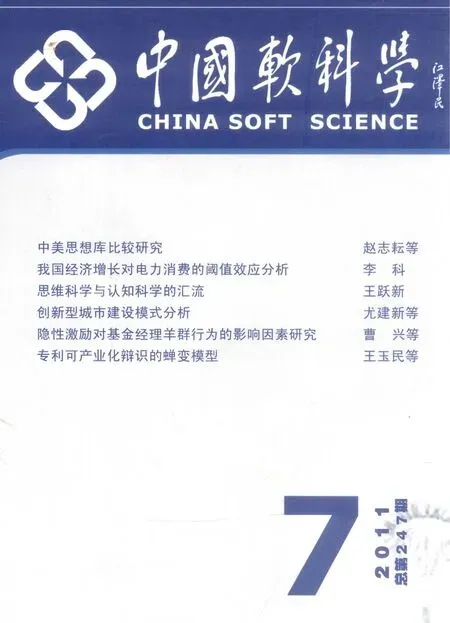隱性激勵對基金經理羊群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
曹 興,鄔陳鋒,聶雁威
(1.中南大學 商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3;2.湖南工業大學 商學院,湖南 株洲 412003)
1.引言
在證券投資基金中,投資者與基金經理之間是一種雙重委托代理關系,兩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函數可能出現不完全一致,基金經理投資行為往往會出現道德風險問題。證券市場中存在的羊群效應現象就是基金經理“敗德行為”的一種典型表現。基金經理出于個人聲譽、報酬的考慮,在選擇投資行為時往往會推斷、模仿、跟隨同行業內其他基金經理的買賣行為,正是基金經理的這種內在特性,其投資行為容易產生羊群行為。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內外學者就開始了金融市場中羊群行為的研究,其重點在于分析證券市場中羊群行為的存在性以及對證券市場所帶來的影響。Becker、Ferson(1999),Chan、Chen 和Lakonishok(2002)分析了基于聲譽激勵基金經理投資行為的特點,認為基金經理的投資行為和規避風險的保守投資者相似,大多數基金經理會模仿市場指數或遵循一種以市場指數為參照點的選股策略,很少基金經理會采取偏離指數過多的投資組合,也就是基金經理具有羊群行為傾向性[1-2]。Graham(1999),Li Xi(2002),Bertrand、Marianne和Schoar(2003)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即基金經理特別與同類型其他基金經理相比,聲譽和收入較高的經理為了維持現有收益水平將會采取羊群行為[3-5]。Arora、Ou-Yang(2001)通過構建兩期連續時間的動態委托代理模型,分析認為經理人的最優選擇是跟隨作為業績衡量指標的基準組合,即最優投資組合策略應該是采取羊群行為[6]。侯紅衛、李雪峰(2010)基于行為金融理論,從實證分析方法的角度也對投資者的羊群行為作了歸納與分析[7]。以上文獻研究表明,基金經理隱性激勵會對基金經理的投資行為產生影響,進而引發羊群行為。從影響基金經理羊群行為因素方面,國內外已有研究,Holmstrom、Milgrom(1991)認為在考慮職業前景的條件下,年輕的基金經理會更加努力工作,而到了年老時候則會顯得懈怠和松散,有可能更偏向羊群行為[8]。Chevalier、Ellison(1999),羅真、張宗成(2004)研究得出,年輕的基金經理比年老的基金經理更容易受基金業績的影響,進而產生消極的職業狀況,這會導致年輕的基金經理更可能發生羊群行為[9-10]。Scharfstein、Stein(1990),Leora、Inessa(2002),Nicole M Boyson(2009)分別對不同的基金進行研究,認為基金經理的職業經歷與羊群行為之間呈正向相關性,職業經歷較少的基金經理會選擇積極的態度,職業經歷豐富的基金經理則會采取保守、消極的態度[11-13]。龔紅(2005)研究認為,從業時間短的基金經理在實踐中確實產生羊群行為,而且小規模基金的經理人更容易發生這種行為[14]。
綜上所述,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基金經理基于隱性激勵的考慮會采取羊群行為,但對于基金經理自身的哪些特性會對隱性激勵產生影響,進而促使基金經理采取羊群行為的研究還不多。雖然,一些學者提出基金經理的年齡、職業經歷是重要因素,但并非立足于中國基金市場,或者其研究與當前中國基金市場的現狀相隔時間太長,沒有真實地反映中國基金業呈現出特點,以及對股票市場所產生影響。因此,本文結合近幾年我國基金市場發展情況,綜合考慮基金經理個人素質,以及基金管理公司聲譽對基金經理羊群行為的作用,從基金經理隱性激勵的視角,通過深入剖析隱性激勵方式,以及對基金經理羊群行為的影響,檢驗現行基金經理隱性激勵方式的有效性;從基金經理自身的角度,探尋導致隱性激勵作用扭曲引發羊群行為的關鍵因素,為基金投資者正確選擇基金經理,制定更為完善的激勵措施提供參考依據,對維護基金投資者的利益,以及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二、實證設計
(一)變量分析與測量
1.隱性激勵測量指標
Chevalier、Ellison(1999)[9],龔紅(2005)[14]在基金經理激勵機制的實證研究中,采用了職業關注作為基金經理聲譽好壞的測量指標,尤其是我國基金市場基金經理具有頻繁跳槽與更替的特征,據wind金融數據庫數據統計,歷任基金經理擔任1只基金的平均時間只有不到13個月,任職不到1年就被更換的基金經理占到更換基金經理總數的26%。因此,本文關于隱性激勵效應(YJ)采用基金經理的職業發展情況進行衡量。

表1 隱性激勵測量指標
2.羊群行為測量指標
從 Scharfstein、Stein(1990)[11],Devenow、Welch(1996)[15],Lakonishok、Shleifer、Thaler 和Vishny(1992)[16]等學者觀點可知,發生羊群行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規避風險。在證券市場上,基金投資風險包括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兩種。因此,本文采用系統風險偏離度(BD)和非系統風險偏離度(UD),測量基金經理投資行為的風險規避程度,即基金i的系統風險值、非系統風險值分別與樣本基金平均值的之差的絕對值,規避程度越高也就是說明基金經理的羊群行為程度越高。
朱毅飛(2006)認為,基金如果存在羊群行為,那么基金十大重倉股所占基金凈資產的比例將與其它基金對這些股票的偏好顯著相關[17]。羅真、張宗成(2004),龔紅(2005)等人,在研究羊群行為程度時采用了行業選擇偏離度[10,14],用于衡量基金經理將其投資組合集中于不同于當時普遍流行的行業的行為。該指標相對比較宏觀,基金投資對象總共只有13個行業,通過測算行業選擇偏離度,雖然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基金經理投資行為相似程度,但還不夠深入和具體。基金重倉股是指一種被多家基金公司重倉持有并占流通市值的20%以上的股票。基金重倉股不僅占據基金凈值較大的比重而且能夠準確反映基金經理的投資策略。因此,本文提出了重倉股選擇偏離度(SD),并進一步延伸到基金經理對當時股票市場普遍流行的股票選擇的趨同行為的研究。其中xij代表基金經理i投資在股票j的市值,yi代表基金經理i所管理基金總凈值,m代表重倉股總只數,n代表樣本基金的個數。

3.影響因素測量指標
(1)基金經理個人素質
Financial World在對各個領域公司的CEO進行聲譽評價,采用的評價標準既包括財務業績、外部環境,也包括了CEO的個人特征。潘松挺、姜濤(2011)則將聲譽從宏觀、中觀、微觀3個層面進行了系統歸納與分析[18]。孫世敏、趙希男、朱久霞認為,CEO個人素質評議指標主要包括倫理道德素質、知識素質、能力素質和社會反響等4個方面[19]。在基金經理激勵機制實證研究方面,Chevalier、Ellison(1999)[9],羅真、張宗成(2004)[10],龔紅(2005)[14]等人采用了基金絕對業績、基金經理年齡、從業經歷、基金規模等指標進行了研究。
本文綜合前人研究,提出了新的影響因素:基金經理個人特征,包括行業經驗(ME)、個人年齡(MAGE)、學歷水平(MX);任職背景主要指基金規模(FS)以及基金成立年限(FA);基金經理能力及財務業績主要指相對業績排序(RP),需要指出的是基金業績排序日益成為投資者了解基金經理經營能力的重要依據。
(2)基金管理公司聲譽
學者們通過研究認為組織聲譽與員工職業發展及個人聲譽相關,Frank、John(1998)的研究表明經理的報酬和企業聲譽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20]。關于公司聲譽的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從財務績效的角度進行考量,Rose、Thomsen(2004)通過實證研究認為公司的經營業績的高低會影響到公司聲譽的水平[21]。Brammer、Pavelin(2006)得出了與前者相似的結論,發現財務業績是決定公司聲譽的一個重要因素[22]。基金管理公司的規模(CS)及基金管理公司的業績(CP)兩個指標代表基金管理公司的聲譽,良好的組織聲譽是吸引優秀人才,保持員工忠誠,并提高員工士氣的重要因素。

表2 羊群行為測量指標

表3 影響因素測量指標
(3)調節變量
基金的類型(FS)是本文實證研究的調節變量。于宏凱(2003)分析指出成長型基金的經理人比收入型基金的經理人的離職概率更大[23]。根據投資風格的不同,可分為成長型基金、收入型基金和平衡型基金。本文引入不同投資風格的基金目的在于研究基金風險的不同,是否會影響羊群行為程度及其影響因素的顯著程度,由于成長性基金代表著高風險,其取值為1,收入型基金和平衡型基金代表著低風險,其取值為0。
(二)樣本選取及數據來源
基金行業開放式基金已成為了主流,目前(截至2010年9月14日)占據了市場的93.8%。由于本文研究目的,在于分析基金經理隱性激勵對其投資策略上采取羊群行為的影響,因此,樣本范圍限制在股票基金。指數基金通過購買一部分或全部的某指數所包含的股票,來構建指數基金的投資組合,目的就是使這個投資組合的變動趨勢與該指數相一致,以取得與指數大致相同的收益率。這樣并不能充分體現基金經理的投資管理基金能力,而且指數基金的引入也有可能擴大無意的基金經理羊群行為的程度,不能準確反映基金經理出于自身內在原因、為了獲取正向的隱性激勵效應而采取羊群行為的本意。因此,本文最終的研究對象是普通型股票基金。
本文選取在2007年1月1日至2010年1月1日期間,并擔任2009年1月1日之前成立的開放式普通股票基金的基金經理為研究對象。由于本文只能從基金管理公司以及相關金融數據或者網站得到一只基金整體的業績,無法明確一只基金經理團隊中單個基金經理的真實能力和業績,進而無法斷定基金經理的隱性激勵效應。所以,僅保留每年1月1日由單獨一個基金經理管理的開放式普通型股票基金,最終確定實證研究樣本數為220個。
本文實證中的重倉股選擇偏離度(SD),采用以2007年的53只樣本基金共持有重倉股種類161只股票、2008年的74只樣本基金共持有重倉股種類180只股票、2009年的93只樣本基金共持有重倉股種類220只股票,共統計了42313個數據。
本文實證研究中原始數據均來自于Wind金融數據庫以及金融界網站、和訊基金網、好買基金網等多個金融網站提供的基金季報、年報、招募說明書及其它資料。
三、實證分析
本文的實證分析從3個方面進行:確定影響基金經理隱性激勵的重要因素;檢驗基金經理隱性激勵與基金經理投資行為中羊群效應存在性的關系;證明基金經理的隱性激勵存在的問題是將會促使基金經理在投資行為上偏向于羊群行為。在此基礎上,分析隱性激勵中的主要影響因素對基金經理的羊群行為產生的影響,并結合不同投資風格的基金,研究這種影響程度是否會隨著基金投資風格的不同風險情況而有所不同。
(一)基金經理隱性激勵的影響因素
1.假設條件
基金獲得高收益不僅能為基金經理帶來當前的收益,而且給基金市場發出積極信號,有利于樹立基金經理聲譽。基金市場上有很多基金評級機構以及一些金融網站都會對基金業績進行排名,基金投資者可以通過這些排名,簡單、直觀的獲取基金經理的信息,作為選擇代理人的參考依據。所以,本文推測:在基金經理更替頻繁的情況下,基金相對業績排序越高,基金經理保住原有的職位或者升遷的機會愈大,取得正向隱性激勵效應的可能性越高;相反,基金相對業績排序越低,基金投資者和基金管理公司給予的支持也會降低,面臨降職或者離職的危險,負向隱性激勵效應的可能性越高。
假設1:基金相對業績排序是影響基金經理隱性激勵效應的主要因素,與基金經理消極的隱性激勵效應負相關。
基金經理的行業經驗豐富,代表著在證券市場的歷練時間長,說明基金經理的能力得到了鍛煉,其投資管理能力和應變突發事件的能力可能會比行業經驗尚淺的基金經理更強。基金經理在通過基金市場的競爭,多年之后仍然生存下來,說明已經得到同行及投資者的信賴。因此,即使行業經驗豐富的基金經理即使出現個別次數的投資決策失誤或者業績滑落,相比剛入行的或者行業經驗較少的基金經理,其聲譽受損程度可能會小一些。
假設2:行業經驗與基金經理消極隱性激勵負相關,這種相關性的敏感程度隨相對業績排序而不同。
2.模型構建
由于隱性激勵效應值是1或0的虛擬變量,用簡單的線性回歸模型來分析其與自變量之間的關系是不恰當的,因此,本文采用了二元Probit模型來進行分析。具體模型如下:

3.結果分析
公式(1)中構建了隱性激勵與相對業績排序、行業經驗以及這兩者相互作用項關系的模型。此外,本文考慮了學歷水平、年齡、基金規模、基金成立年限、公司規模、公司業績對隱性激勵的影響。為了全面、獨立的分析每個變量對隱性激勵的作用,以及在隱性激勵下,這些變量對相互業績排序的敏感性,本文分別將每個控制變量及其與相互業績排序的相互作用項,單獨加入實證模型中,通過Eviews 6.0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基金經理隱性激勵效應的影響因素回歸分析
根據以上分析,具體的研究結果如下:
表4第一列結果表明,隱性激勵與相對業績排序(RPit)顯著正相關。基金業績的排名越靠前,基金經理越可能在基金市場上贏得良好的聲譽,進而獲得基金公司和投資者更多的信任,得到更多的職業發展機會。相反,相對業績排名落后就會給基金市場一種消極的信號,使得基金公司和投資者對基金經理失去信心,產生一種消極的隱性激勵效應,這驗證了假設1。回歸結果發現,行業經驗(MEit)、相對業績與行業經驗相互作用項的結果都不顯著,這是由于我國基金行業是從1998年開始擁有第一只基金,到2001年才有了開放式基金市場,基金經理的行業經驗整體不足,所以造成相關性不顯著。而且,這種結果的產生與基金投資者注重短期經濟利益的投資理念相關,投資者更關注的可能是基金經理近兩年所管理的基金的業績和收益如何,證券市場是瞬息萬變的,僅靠基金經理行業經驗來斷定其業績可能不太科學。
表4第二列顯示學歷(MXit)和相對業績排序與學歷相互作用項(RPit*MXit)的回歸結果并不明顯。這跟我國基金經理整體學歷水平比較均衡相關。從調查樣本顯示86.36%的基金經理擁有碩士學位,8.16%是博士,僅5.46%基金經理是學士,說明碩士學位成為了基金經理資格的一個必備條件,即使存在極少數的基金經理是學士學位,但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會去獲取更高的學歷,而博士學位或者被基金管理公司定格為不“適合”,或者由于自身感覺“大材小用”,并沒有成為基金經理主流群體。
表4第三列考慮年齡(MAGEit)及與相對業績排序相互作用項(RPit*(MAGEit-對隱性激勵效應的影響,和以往國內外學者對該項研究結果略有不同,它們與隱性激勵相關性并不顯著。這與國外基金市場幾十年發展歷程相比,我國基金市場發展相對短暫,因此基金經理的年齡主要集中在30-40歲之間(調查樣本顯示,92.27%的基金經理在這個階段),而在國外基金經理年齡的分布廣泛,甚至到了60歲以上,所以,在我國基金市場上,基金經理年齡對隱性激勵效應產生的影響難以得到充分檢驗。
表4第四列顯示了基金規模(FSit)及其與相對業績排序相互作用項(RPit*FSit)的回歸結果。基金管理公司通常會讓投資管理能力強的經理管理大規模基金,管理大規模基金等同于向市場發出了一種高能力、高信譽的信號。所以,基金規模與隱性激勵存在著正相關性,這也在實證中得到了證實。基金規模與相對業績排序相互作用項顯著負相關。基金管理公司將大規模基金由能力強的基金經理負責管理,偶爾出現偏差的業績時,由于公司難以找到更合適的基金經理更替,轉換成本較高,而小規模基金可替換的基金經理相對較多,基金管理公司轉換成本較低也相對簡單。
表4第五列加入了基金成立年限(FAit)及與相對業績排序相互作用項(RPit*FAit)。結果顯示,這兩個變量對隱性激勵效應的影響不顯著。這是因為:一方面,基金成立年限代表了基金的生命力,在同類型基金中具有較高的影響力,形成了基金品牌效應,管理這種基金的經理會受到這種品牌影響力的作用帶來積極的激勵效應;另一方面,新成立的基金往往是基金管理公司認為具有良好發展前景,需要重點管理和保護的基金,基金管理公司往往會委派管理投資能力強、以往業績相對較好的基金經理進行操作。因此,基金成立年限對基金經理隱性激勵效應的影響并不是絕對的。
表4第六列結果顯示公司規模(CSit)及其與基金相對業績排序的相互作用項(RPit*CSit)與隱性激勵效應的關系顯著正相關。這是因為基金管理公司規模越大,代表著公司的整體實力雄厚,在行業中具有較大影響力,身為大規模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經理也會為此而得到一種好的聲譽。同時,大規模的基金管理公司的企業文化通常要更好,擁有優良的基金經理團隊,對基金經理技能的提升產生積極作用。但是,當基金經理相對業績排序滑落時,大規模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經理受到處分的可能性會更高,因為大規模基金管理公司旗下有眾多優秀基金經理,轉換成本不高。小規模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經理人才儲備不充分,在基金市場上很難招到合適基金經理,轉換成本就比大。
表4第七列顯示公司業績(CPit)與隱性激勵顯著正相關,但與基金相對業績排序相互作用項(RPit*CPit)結果并不顯著。由于公司業績良好使基金管理公司在基金行業及投資者群體中提高了聲譽,將會對基金經理產生一種“暈輪效應”,使得基金投資者認為在這個團隊中的基金經理都是投資管理能力、專業素質很高的代理人。同樣,與大規模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經理隱性激勵效應對相對業績排序比較敏感的原因相同,基金管理公司業績良好的基金經理的隱性激勵效應對相對業績排序也更加敏感,但是這種結果并不顯著。
綜上分析,相對業績排序是決定基金經理隱性激勵主要的影響因素,基金業績排名在同行中越靠前其留職或升職的隱性激勵概率越高。此外,基金規模、公司規模、公司業績也是影響基金經理隱性激勵效應的顯著性正向因素。而且,小規模基金的經理人在基金相對業績排序落后的情況下,面臨著降職、離職的風險要比大規模基金的經理人高。任職于大規模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經理的隱性激勵效應會隨著相對業績排序的變化而敏感的發生變化。
(二)基金經理隱性激勵與羊群行為關系
1.假設條件
在基金市場上存在著專業機構對基金的業績進行排名,賦予星級基金經理稱號,一旦基金經理業績不能達到要求,將面臨著基金投資者和公司高層的批判和問責,所以基金經理是否會為了保住職位,維護聲譽而采取“從眾行為”是本文實證分析的目的。此外,不同投資風格的基金代表著不同的風險程度,基金經理為了獲取穩定基金業績,保持相對良好的職業聲譽,通常對風險采取規避的態度。因此,本文推測:基金投資風格風險程度越高,基金經理在投資策略的選擇上就越可能采取從眾的跟風行為。
假設3:基金經理羊群行為與隱性激勵效應之間存在正相關。
假設4:基金經理羊群行為與隱性經理的關系受基金投資風格風險程度的正向調節。
2.模型構建
本節采用重倉股選擇偏離度(SDit)、系統風險偏離度(BDit)、非系統風險偏離度(UDit)三個變量來測量羊群行為程度。通過構建二元Probit回歸模型,檢測基金經理是否會為了隱性激勵而采取羊群行為,進一步分析不同風格的基金(STit)對基金經理羊群行為所帶來的作用有何區別。

3.結果分析
本文運用Eviews 6.0分別對公式(2)、公式(3)、公式(4)進行二元Probit離散選擇模型的回歸分析,其標準化系數與檢驗結果對應于表與中的1、2、3三列,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5 隱性激勵與基金經理羊群行為關系的回歸分析
通過實證分析,認為基金經理基于隱性激勵的目的,會影響其在投資策略選擇上偏向于采取羊群行為。實證分析中,分別用基金重倉股選擇偏離度、系統風險偏離度、非系統風險偏離度3個變量來解釋羊群行為,研究發現三者與隱性激勵的關系都是負向相關的,尤其系統風險偏離度變量回歸結果顯著而其它兩者回歸結果的顯著性較差。在基金市場上,開放式股票基金由于面臨著市場贖回的壓力,基金經理在付出努力的同時還會考慮基金同行競爭者的投資行為選擇,雖然冒險的投資行為可能會為基金經理帶來比行業均值更高的基金業績和經濟利益,但一旦失敗后將面臨著降職、離職或者其它方面的消極處罰,基金投資者對基金經理信心的動搖及基金贖回壓力,基金評級機構及相關中介、媒體的業績排名產生的負面影響,基金經理為了維護隱性激勵效應,在投資行為上會產生“羊群效應”現象,假設3成立。
本文還分析了不同投資風格的基金經理對采取羊群行為的敏感性。表5研究結果顯示:投資風格風險越高的基金與基金經理隱性效應負相關,高風險投資風格的基金往往難以得到市場基金投資者的支持,所以管理該基金的經理人得到隱性激勵的難度比管理低風險基金的經理人更難。一旦高風險基金的經理人得到了基金投資者的注資,由于這部分投資者看重的是長遠的高收益,對業績短期利益高低的敏感性比起低風險基金的投資者來的小,即低風險基金的經理人面臨著相對業績排序,以及基金穩定收益的壓力比高風險基金的經理人大,迫使基金經理在投資策略選擇時加劇了羊群行為的偏好性。
(三)隱性激勵下基金經理羊群行為的影響因素
1.假設條件
以上分析表明,基金經理的相對業績排序在同行中的名次越低,那么他們面臨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投資者等多方壓力及消極影響的可能性越高,基金經理為了避免降職、離職等消極隱性激勵效應的出現,他們有可能會忽視自己獲取到的信息,而采取跟風的“從眾行為”。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小規模基金的基金經理在基金業績較差時,也更容易受到基金管理公司的負面懲罰;而大規模和業績良好的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經理在基金業績較差時,被管理公司解雇或者降職的可能性更大。為了穩妥起見,小規模基金、大規模和業績良好的基金經理通常因為擔憂自身的職業發展、維護自身聲譽,獲取一種正向的隱性激勵效應,跟隨同行基金經理們的投資策略。此外,在基金經理隱性激勵與羊群行為關系的實證分析中得出投資風格不同對基金經理投資行為所產生的影響有所差異,低風險基金的經理人基于隱性激勵的考慮,在選擇投資策略時更偏向于采取羊群行為。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以下假設:
假設5:基金相對業績排序越低,基金經理越可能采取羊群行為的投資策略;
假設6:基金經理管理的基金規模越小會使得羊群行為更容易發生;
假設7:基金管理公司的規模越大,基金經理投資時越可能發生羊群行為;
假設8:基金管理公司的業績越好,基金經理投資時越可能發生羊群行為;
假設9:基金投資風格對基金經理羊群行為起到調節作用。
2.模型構建
為了檢驗在隱性激勵下,基金經理偏向于采取羊群行為的主要影響因素,本文運用OLS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實證方法,通過構建3個研究模型,檢驗基金相對業績(RPit)、基金規模(FSit)、公司規模(CSit)、公司業績(CPit)對基金經理羊群行為的影響,以及基金投資風格(STit)對各個影響關系所產生調節效應。

3.結果分析
根據以上3個實證研究模型,運用Eviews 6.0將全部解釋變量分別帶入,進行回歸分析,檢驗這些變量分別對重倉股選擇偏離度、系統風險偏離度、非系統風險偏離度的影響,其標準化系數與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隱性激勵下基金經理羊群行為影響因素回歸分析
表6的回歸結果顯示,基金規模與重倉股選擇偏離度顯著負相關。由于基金經理管理的規模越大,基金經理只要保持原有的基金業績,維護良好聲譽,就會吸引到更多基金投資者的注資,提升未來的管理費收入和更好的職業發展。倘若基金經理采取偏離性的高風險投資策略,雖然大規模的基金經理的隱性激勵效應可能不會因為偶爾一兩次的業績下降而嚴重受損,但終究還是造成不良影響,尤其在基金經理數量不斷增加,經理頻繁更替的背景下,大規模的基金經理具有采取羊群行為的傾向性。
基金管理公司規模與系統風險偏離度顯著負相關。大規模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經理在投資組合策略選擇時更加偏好于市場上的常規趨勢。上文中指出在基金經理相對業績排序滑落時,大規模基金管理公司的經理人對于消極的隱性激勵更加的敏感,他們受到處分的可能性更高。因此,在大規模基金管理公司任職,由于公司通常擁有優良的基金管理團隊,受到身邊其他優秀的基金經理的威脅的概率更大,其投資行為更可能趨向保守,羊群行為這種跟風策略更加容易發生。
基金投資風格風險越低,基金經理在投資行為上表現為重倉股選擇偏離度和系統風險偏離度越小,即越有羊群行為傾向性,與上文實證結果一致。基金投資風格的調節效應表現為:業績排序靠前的基金經理在采取投資行為時,基金投資風格風險越小則選擇的系統風險偏離度越低,即越具有羊群行為的偏向性;大規模基金經理在采取投資行為時,基金投資風格風險越小則投資的重倉股選擇偏離度越低,即越具有羊群行為的偏向性。
此外,相比于2009年,2007年樣本中各開放式普通股票基金投資組合中系統風險值、非系統風險值更加相似,基金經理彼此之間的投資策略雷同的程度更高,說明基金經理的羊群行為在2007年牛市中表現的更加明顯。但在2008年證券市場受次貸危機的影響,其所表現的基金經理羊群行為程度是否比2009年更加嚴重并沒有通過實證的數據顯著性檢驗。
四、結論與啟示
通過實證分析,研究了隱性激勵與基金經理羊群行為的關系以及影響因素,本文認為:基金相應業績排序、基金規模、基金管理公司規模、基金管理公司業績,這幾個因素與基金經理消極隱性激勵顯著負相關;基金經理在選擇投資組合時為了維護聲譽,保持一種正向的隱性激勵效應,會偏向于羊群行為;大規模基金的經理人以及任職于大規模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經理在實踐中更容易產生羊群行為,同時在考慮基金投資風格的調節作用時,基金投資風格風險越小,大規模基金、相對業績排序靠前的基金經理在選擇投資行為時發生羊群行為的概率明顯提升。
在隱性激勵下,基金規模、基金管理公司規模是影響基金經理羊群行為正相關的重要因素。而且在投資風格風險越小的基金中,大規模基金、相對業績排序良好經理的這種羊群行為偏好會更加突出。此外,證券市場行情也會成為基金經理羊群行為偏好程度的一個影響因素。基于以上研究,對增強我國基金經理激勵的有效性,本文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培育基金經理市場,提高基金經理素質水平。隱性激勵有效性前提條件是根據準確的聲譽信息作出對應的獎懲,否則由于羊群行為所產生的“浪得虛名”會使得隱性激勵失去激勵約束作用,導致基金經理過分關注虛名、盲目跟風等低效率行為。培育充分競爭的基金經理市場是一種有效的解決方式。當前,我國基金市場規模和基金數量急劇增長,建立完善的基金經理進入和退出市場機制,有利于降低基金經理羊群行為和保證隱性激勵的“質量”。
(2)在培育基金經理市場同時,也應提高基金經理的素質水平,因為羊群行為的產生最終歸結為人的因素。一方面,提高基金經理的職業道德素質,明確代理職責,防范以公謀私,有效約束基金經理的故意羊群行為;另一方面,提升基金經理專業素養和管理能力,樹立理性投資理念,充分認識羊群行為的危害性。
(3)提倡實施基金經理持基激勵。2005年美國證交會規定共同基金經理必須公開其是否有自購基金和自購份額,2008年晨星美國的報告顯示了基金經理自購行為有利于提高基金業績。通過國外公布的數據和經驗可看出,基金經理自購行為有利于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和預防基金經理羊群行為。這種自購行為實質是持基激勵,是基金經理的一種自我激勵方式。基金收益直接影響了基金經理的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分攤了投資者的風險水平,同時也鼓勵基金經理不斷為更高的收益而努力和創新,減少了基金經理的羊群行為等道德風險現象。
(4)完善基金經理業績評價體系。我國當前的基金報酬標準單一,短期業績排名增加了基金經理投資業績的壓力。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環境下,基金經理頻繁更替,大規模、大公司的基金經理可能偏向于羊群行為,其他基金經理也可能采取各種方式調整投資組合和風險水平來提高或者維系已有的業績。因此,建立一套長期、科學、客觀、準確的評價體系,在衡量業績時能綜合體現多方面的能力,如考慮創新性、設置最低工資水平、對盈利者設置額外獎賞。這種方法對羊群行為將十分有效,真正發揮隱性激勵對基金經理的長期化行為的激勵約束作用。目前,多數發達國家認可的全球投資表現標準(GIPS),值得國內借鑒,,主要分為對數據要求、計算方法要求、基金分類要求、信息披露要求、報告演示要求等,業績計算的時間長度至少為5年。
(5)改善監督管理環境。羊群行為等道德行為的預防離不開完善監督管理,一個有效的監督管理環境既包括外包監管又包括內部監管:外部監管體系建立要以證監會、證券交易所監管為中心,基金行業自律協會、投資者訴訟機制相配合的多層次監管機制。內部監管體系一方面要在公司內部專門設立監管部門,負責檢查稽核工作,向公司董事會和證監會匯報;另一方面通過立法加強基金托管人的監督作用。此外,應引入獨立董事制度來代表投資者利用。
[1]Becker Connie,Wayne Ferson,Dacid Myers,Michael Schill.Conditional Market Timing with Benchmark Investor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9,52:119 -148.
[2]Chan,Louis K C,Hsiu - Lang Chen,Josef Lakonishok.On Mutual Fund Investment styles[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2,15:1407 -1437.
[3]Graham John R.Herding among Investment News Letters:Theory and Evidence[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9,54(1):237-268.
[4]LiXi.Performance,Herding,and Career Concerns of Individual Financial Analysts[R].Vanderbilt University,Working Paper,2002.
[5]Bertrand,Marianne,Schoar Annette.Managing with Style:The Effect of Managers on Firm Polici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4):1169 -1208.
[6]Arora N,Ou-Yang H.Explicit and Implicit Incentives in a Delegated Portfolio Management Problem:Theory and Evidence[R].Working Paper,2001.
[7]侯紅衛,李雪峰.基于行為金融理論的投資者行為研究方法現狀與展望[J].科學決策,2010(2):83-93.
[8]B Holmstrom,P Milgrom.Principal-agent Analyses:Incentive Contracts,Asset Ownership and Job Design[J].Journal of Law,Econmics and Organization,1991,7(1):24 -52.
[9]Judith Chevalier,Glenn Ellison.Career Concerns of Mutual Fund Managers[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14(2):389 -432.
[10]羅 真,張宗成.職業憂慮影響基金經理投資行為的經驗分析[J].世界經濟,2004,18(4):63 -71.
[11]Seharfstein D,J Stein.Herd Behavior and Invest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0.
[12]Klapper Leora F,Inessa.Corporate Governance,Investor Protection and Performance in Emerging Markets[R].World Bank working Paper,2002.
[13]Nicole M Boyson.Implicit Incentives and Reputational Herding by Hedge Fund Managers[J].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09(10):1 -17.
[14]龔 紅.證券投資基金經理激勵問題研究[D].湖南大學,2005.
[15]A Devenow,I Welch.Rational Herding in Financial Economic[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6(40):603-615.
[16]Lakonishok,Shleifer,Vishny.The Impact of Intitutional Trading on Stock Pric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2,82:23 -43.
[17]朱毅飛.證券投資基金的羊群行為分析[D].湖南大學,2006.
[18]潘松挺,姜 濤.企業家聲譽結構及聲譽驅動機理的研究綜述[J].科學決策,2011(2):76-83.
[19]孫世敏,趙希男,朱久霞.國有企業CEO聲譽評價體系設計[J].會計研究,2006:75-79.
[20]Winfrey Frank L,Logan John E.Are Reputation and Power Compensation Differentials in CEO Compensation?[J].Corporate Reputation Review,1998(2):61 -76.
[21]Caspar Rose,Steen Thomsen.The Impact of Corporate Reputation on Performance:Some Danish Evidence[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04,22(2):201.
[22]Stephen J.Brammer,Stephen Pavelin,Comporate Reputation and Social Performance:The Importance of Fit[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6,4(3):435 -455.
[23]于宏凱.基金經理人激勵機制解析[J].證券市場導報,2003(1):3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