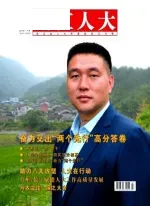發現真問題更重要
■潘啟雯

假設這樣一個場景:高速公路上發生了車禍,有輛車不幸被撞翻,一個人被困在了車里。如何解救,有三種辦法:其一,立即報警,代價是警察可能來得很慢,被困者生命垂危,等不及了。其二,過路人跟被困者商量:如果給10萬元,就把你救出來,并及時送到醫院救治。但可能的情況是,被困者一下子拿不出10萬元。其三,過路人中有幾個特別善良的站了出來,無償幫助被困者。
第一種辦法,叫做“找政府”;第二種辦法,叫做“找市場”;第三種辦法,叫做“找社會”。事實上,政府、市場、社會,恰恰是我們開展公共生活的“三種機制”。從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保衛社會》中同樣可以找到這“三種機制”的影子和三者間的某種尷尬。單看書名,全書的核心思想就一目了然:對于解決某些問題,我們有必要回過頭去,“重新發現和保衛社會”。
近年來,鄭永年以獨立而深入的中國研究,以及視角獨到的專欄寫作,日益引起國際學術界及中國政府決策部門的重視。“對中國時局非常清醒”,是學術界和讀者對他共同的評價。毫無疑問,一場長達30多年的中國社會改革,有成功的欣喜,亦有迷惘和陣痛,而對于當前的中國研究而言,能發現真問題顯得更為重要:一方面使我們清晰地看到中國改革30多年來積淀下來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又難得地賦予我們客觀而冷靜的視角,為新的開始創造轉機,為評估具體“社會”安全、保衛“對象”找尋具體的切入點,譬如住房保障、收入分配、社會道德、教育改革等等。
在“中產階級與社會改革”一章中,鄭永年以“樂此不疲的信念”告訴人們,以GDP為中心的經濟增長,不僅造成可持續經濟發展的瓶頸,使內需始終無法打開,而且意味著貧富分化和收入差異,社會正義和維護這種正義的制度手段都將得不到尊重,即使獲利者也會感覺到不安全。要實現正義或者表面上的正義,僅靠“到點自行掉頭”,希望渺茫。
再以住房政策為例,鄭永年在“中國住房政策的癥結在哪里”一文中口氣毫不含糊:中國房地產問題最突出的一點,“莫過于發展房地產市場的主導思想的嚴重失誤。簡單地說,在中國,房地產被視為僅僅是經濟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會政策的一部分。因為商品房兼具投資和消費價值,人們對其價格上漲有預期。開發商利用這樣的預期去囤積土地和新房,購房者也會迫不及待地去買房,從而一步一步地把房價逼向新高。”“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漲價之外,住房的社會功能的缺位,更體現在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供給的極度缺乏。”誠哉斯言,怎么看都不像是泛泛而論,而是有的放矢。
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進步在于通過市場化轉型發現作為個體的“我”,那么中國下一步的挑戰則是如何給社會松綁,通過保衛社會來發現作為集體的“我們”。因此,《保衛社會》所搭的不僅是中國社會的脈搏,也是關乎整個民族未來的脈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