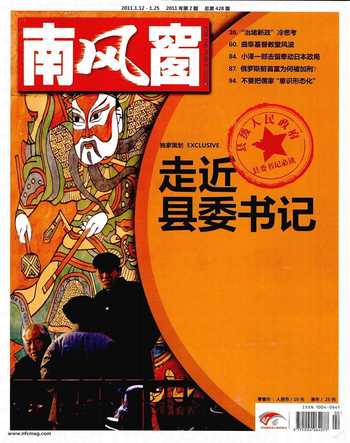創業教育的革新
田 磊


“正是因為這個社會有這樣那樣的不足,才需要你們去創造,去解決問題,那些滿腹牢騷、抱怨社會的人請馬上離開這里。”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副書記徐飛在剛剛成立的創業學院給他的54名學生上了第一課。
過去的一年里,中國的大學刮起了一陣創業教育熱潮。越來越多的高校,尤其是理工科見長的大學專門成立創業學院,打出了培育產業巨子的口號。英特爾、微軟這些跨國公司組織的各類全球性創業比賽上,中國的學生也越來越多地成為獲獎的常客。
上月底,在英特爾和伯克利大學共同舉辦的全球大學生創業大賽上,一共有3支來自中國的代表隊進入了最后的決賽圈,比東道主美國人還要多。“中國的學生,對于創業的熱情,讓人吃驚,他們看起來一個個都雄心勃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創業與創新中心主任Jemme Engel說。
篤信技術萬能、崇尚財富、崇拜成功,在很多方面,這一代中國理工科的大學生,越來越變得跟扎克伯格這樣的美國同齡人沒有什么差別。他們對于國家命運的思慮,對于制度好壞的擔憂,很容易就被對財富、技術的樂觀情緒所取代。
“我們比美國人少什么?”
2010年12月底,扎克伯格終于來中國了。這個美國制造的新一代財富英雄僅僅是在中關村的幾家互聯網公司轉悠了一圈,就引起了無數中國粉絲的追捧。在過去的一年里,26歲的扎克伯格和他創立的Facebook風靡全球,這段屬于80后一代的創業傳奇激勵著全世界的年輕人,中國也不例外。
在互聯網世界,國界之分早已日趨模糊,最先進的思想和技術在全世界各地的傳播基本上都是沒有落差的。可是為什么這些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創意仍然源源不斷地只從美國產生?
向禹辰是上海交通大學的一名在校生,上月帶著他的團隊參加了英特爾公司和伯克利大學共同舉辦的全球大學生創業挑戰賽,他拿這個問題曾經不止一次追問那些美國最知名的創業教育大師和風投專家。
“美國人給出的答案很簡單:像扎克伯格這樣的人,成功的路徑,都是先找到某個社會群體的特定需求,然后用他們所掌握的知識,為這些需求找到一個實現的渠道,沒有什么復雜的。”向禹辰說,而我們創業的思路大多是先考慮我有什么樣的想法和技術,這些技術能夠為哪些人服務,然后再去費力尋找這些想象中的需求者,結果往往就是越做越難。
事實上,在那次比賽中,各國學生之間的差異還遠遠不止這些。在創業方向上,伯克利、劍橋、曼海姆等這些來自于歐美發達國家學校的學生,他們帶來的參賽項目絕大部分都是基于互聯網在游戲、教育、社交等領域的應用。這些國家早已度過了物質和能源匱乏的發展階段,于是,如何更好滿足人們社交和娛樂需求變成了創業的最大機遇。
而中國、巴西、阿根廷、印度、多米尼加等這些國家的學生帶來的則多是基于能源開發和應用領域,來自中國的3個項目就分別是廢油回收利用,LEC照明技術,芝蘭碳素應用。對于這些正在高速發展中的國家來說,對各式能源的龐大需求,總是蘊藏著巨大而誘人的財富潛力等待那些掌握技術的年輕人去發掘。
那場比賽結束后,當被記者問及中美兩國學生有什么差異時,一位來自加州一家知名風險投資公司的評委說,中國學生給出的項目總是很宏大,基于社會問題的解決,而美國學生則只是基于個人用戶的需求,致力于給人們帶來更好玩的東西。“我個人很喜歡中國學生,他們身上普遍有一種要為自己民族解決問題的宏大責任感,從價值層面來說,他們的項目也比美國學生的項目更大,但就創業而言,顯然美國學生的思維方式更容易取得成功。”
清華大學的廢油回收項目,在大賽上受到了廣泛關注,尤其是團隊中一個在歐洲長大的中國女孩趙筠婷,在做項目介紹時,其流利的英語,敏捷的思維,可謂技驚四座。但清華大學的項目最終僅僅獲得了最受觀眾喜愛獎。在陳述時,就有評委不斷追問,“為什么你們的項目設計中要提到這么多次‘政府呢?”學生們的回答也很坦誠,“因為在中國做這些事情,需要政府的幫助,尤其是地方政府,沒有這些幫助,我們很難做成什么。”
事實上,去年,這項比賽的一等獎就是被清華大學一個可降解納米骨釘項目團隊拿走的。但回去以后,這個被評委們一致看好的項目很快就被擱置了,“專利權方面有些問題,學生們有的考研出國了,有的考公務員了,創業的事情也就沒人做了”。當時帶隊的老師、清華大學中國創業研究中心張幃副教授說,從創業比賽的成功到創業成功還有很多路要走。一方面是創業外部環境,還有很大欠缺,另外則是創業文化,我們對失敗的容忍度,一個年輕人要想創業所背負的壓力,都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在比賽結束后,記者就曾經問過清華大學的一個團隊成員:“當你畢業時,如果有三份工作,一個中央部委的公務員職位,一個知名跨國公司的offer,一個前途未卜的創業項目,你會怎么選?”他很爽快地說,我會去創業,因為我的家庭條件還可以,我沒有太大謀生壓力。但我想,我的大部分同學可能不會這樣選。
誰來創造中國未來?
“技術普及、滲透的技術越來越快了,電視從誕生到全球普及,一共用了75年,手機用了15年,而互聯網上的新技術往往只需要三五年。”Jerome Engel教授說,現在人類社會正在迎來一個創業的偉大時代,而創業對于經濟和就業的推動作用是巨大的,也因此,他堅信美國人能夠走出目前的經濟困境。
但在中國,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尤其是名校學生選擇投考公務員、躋身待遇豐厚、壟斷性強的國有企業,這樣的情境正在成為一種潮流,在今天的大學校園里,那些對創業還保有熱情的年輕人更顯得彌足珍貴。
在徐飛看來,這一代大學生稱得上是中國最正常的一代人,“他們思維活躍,知識集成能力強,與西方同齡人沒有落差,是真正的可造之材。因此,作為一名教育者,我們應該想辦法激發他們對于創造力的熱情,而不是任其被社會現實所裹挾。”
上海交通大學今年成立了創業學院,首批招了54名學生,徐飛親自擔任院長。“我最想教給他們的其實是一種信念,要樹立為我們民族創造新的東西,解決社會問題的使命感,而不是去抱怨這個不完美的社會。”徐飛說,大學教育缺的不是“術”,而是“道”,理工科的學生尤其如此,交大成立創業學院,除了在“術”的層面培養一批創業者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布道”,將對于創新的熱情根植于全校學生的心中。
事實上,今天這一代大學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好時代。中國龐大的市場和豐富的人力資源、智力資源吸引了大量跨國公司,而這些公司在中國大都已經有了二三十年的經營,除了建設工廠之外,他們越來越重視在中國推銷自己的理念。像英特爾這樣的跨國公司,會投入巨額資金跟教育部合作,從小學教師的培訓,中學學科競賽,到大學的技術合作,深度介入中國教育的各個層面。
對于中國而言,這些東西比他們的工廠和商品發揮著更加持久的作用。他們不僅將篤信科技的信念根植在中國學生的心中,更為他們描繪了一幅將技術轉化成財富的現實圖景,讓這一代學生顯得比任何一代人都雄心勃勃。那些由各種跨國公司所創設的全球科技創新比賽平臺,正在極大程度地改變著今天的中國大學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學生的生活方式,在這些平臺上,他們的稟賦顯露無遺,他們早已不再像前輩仰視比爾·蓋茨那樣,來仰視今天被譽為蓋茨第二的扎克伯格了。
向禹辰也說,雖然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過自我創造的大事業了,過去的10多年里,中國本土的新誕生的大公司要么依靠資本運作,要么靠對“美國創意”的拷貝,但中國學習的速度已經越來越快了,在眾多高精尖領域完全跟得上美國的步伐,他們要做什么,中國馬上就能為其做配套。
這個生于1986年的在校大學生對于社會問題思考的成熟度聽起來讓人有些吃驚,在他的思維體系中,過往60年,整個國家的歷史更像是一部創業史,前30年是領袖創業的階段,機遇是全球動蕩,需求則是廣大工農勞工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成果是打下了重工業和裝備制造業的基礎;1978年以后則是第二產業創業,國家需要建設,必須有人來做,于是像王石、任正非、柳傳志這些人,修公路、蓋房子、造電器等等;過去的10年里,中國涌現的新公司則基本都是服務業,互聯網、購物、餐飲、連鎖酒店等等。而未來的創業機會一定是集中在滿足有錢了的中國人追求更舒適更便捷生活方式的需求。
在今天中國社會,百萬大軍趕考公務員的背景下,在大量社會財富棄實體經濟而涌向股市樓市時,這些年輕大學生們對于創業的熱情和思考顯得如此難能可貴。未來10年,他們終將從創業比賽的舞臺走上真正的創業舞臺,他們的表現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家經濟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