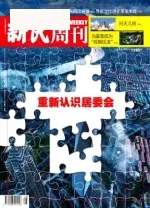讓音樂繼續蔓延
姚謙
生命中的轉折往往都超出你的預料,從來沒有想象過我會成為流行音樂的工作者。當初聽流行歌只是一種愛好,特別是在大學時期民歌的興起,正好與那個年代自己的閱讀相關,所以投入了較多的熱情。沒想到校園民歌成為了流行音樂的主流,甚至擴散到全世界華人地區,我身逢這個時代也成了其中一員。
但是隨著數字時代的興起,解構人們聽音樂的習慣,唱片逐年凋零。在與唱片最后命運奮斗的十年途中,我如候鳥般于北京與臺北每月來回,沒想到這樣的生活改變了我。讓我改變最大的原因是其間遇見的人,雖然同文同種,但因為所受的教育、經歷的世界與觀念有著很大的差異,于是在摸索磨合與接受了解的過程里,北京的朋友給我的刺激與開發最多,我特別想要提的一位朋友是吳彤。
他是地道的北京人,滿族,出身樂器世家,我們先后進入了同一間公司,卻沒有共事過。我是在公司沒有發行的母帶里聽到他的音樂的,從他的音樂聽到了深厚的華人氣息,也聽到了北京搖滾的范兒,這樣的氣質是在臺灣所不容易尋找到的。見面后才明白他還有一項驚人的專長:“笙”。這個神秘而遙遠的竹制的中國管樂器,以往我總覺得那是飛天仙女所使的,沒想到在一個北京漢子的手上居然能如此地出神入化。
聽著他講述少年時期生活的北京,總讓我聯想起年少閱讀關于北京城文章里的氣氛。一個不安分的少年,雖然舉止端正出入有禮,但是心中卻有著不安分的靈魂,自小雖受到嚴肅的古典音樂養成,卻在大學時放下了,決定組團唱起了撕心裂肺的搖滾樂。在那個搖滾音樂和臺灣流行歌曲才能表達年輕的想法的時期,他高亢的歌聲接近張雨生的壯烈,卻仍脫離不開屬于中國民樂里的端正感。吳彤與其他中國搖滾樂團歌手最大的不同,除了憤怒還有那種骨子里文人的浪漫。大學畢業后,他開始嚴肅地思考生命的存在這個問題,感到惶恐與茫然,于是選擇了一個文人的手段——閉關!
他說:那半個月都在暗室里不語,不停地閱讀著一些哲學書籍,想透過前人的智慧找到自己的答案。一直到有天早晨他決定推開窗看看今夕是何夕時,看到窗外世界茫茫一片大雪,蒼白而安靜,仿佛沒有生命氣息,這讓他有了股莫名重生的感動。從那天起他又回頭拾起“笙”,回到與自己血液相通的管道里,借由生命本能的吐納氣息,開始了另一個階段的音樂生命。
在我眼中的吳彤,談起音樂與人生,總是帶著嚴肅與浪漫融合的氣息,是個很有魅力的人。正巧那時候的我也正在思索一個問題,當臺式流行音樂不再是流行音樂唯一的主體時,下一階段屬于華人的流行音樂應該是什么?這一年來我也有了答案,流行音樂本該多元,而吳彤這樣帶著更濃郁的民族色彩也是一條路。吳彤因那一場雪創作了一首作品。一個安靜的北京子夜時分,看著我北京家窗外黑壓壓而安靜的朝陽公園,任這曲音樂在我的房里靜靜地流淌,我忽然發現自己開始沒有身處異鄉的感覺了。
這兩年透過吳彤認識了馬友友,原來近十年來他一直支持著馬友友的“絲路計劃”,他們希望把亞洲對于民族樂器有理想的年輕人聚集起來,到全世界各地去表演,這是一件多么感人的計劃啊!去年絲路又來到了臺灣,吳彤特別興奮地告訴我這個消息,并問我有什么建議。我順口說來一首臺灣民謠《望春風》吧!沒想到他卻認真了,兩天之后我在香港出差時接到他的電話,他在那頭居然清唱了一遍剛學會的《望春風》,唱完后他還讓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去糾正他的咬字,這可把我給考倒了。
不久后馬友友以“巴赫無伴奏”為序,引導著吳彤的“笙”為前奏,就這樣呈現在臺灣愛樂人群面前。可惜當時我在北京。半夜吳彤發來短消息謝謝我的建議,因為那夜臺北全場的群眾都跟著他唱完了整首歌曲。隔天我就買了機票回到臺灣,趕上他第二場演出,在晚風徐徐的臺中夜里,我情不自禁也跟著群眾合唱著《望春風》,這是我這輩子聽過最好聽的《望春風》版本。
因為吳彤我又開始對于音樂有了信心和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