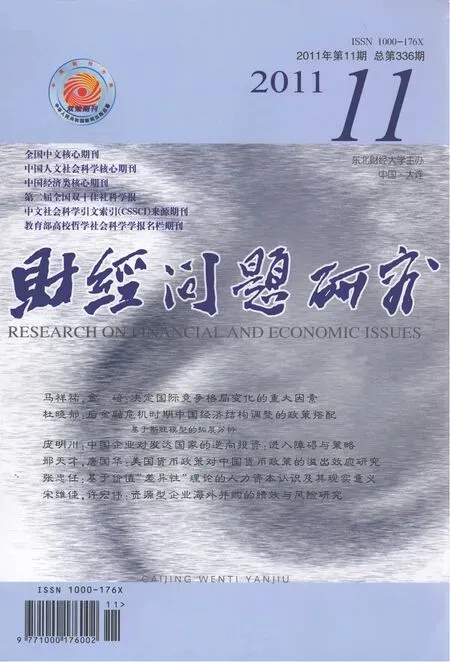住房改革、流動(dòng)性約束與城鎮(zhèn)居民消費(fèi)研究
王春娟,黃 昊
(1.東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 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遼寧 大連 116025;2.東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 研究生院,遼寧 大連 116025)
一、引 言
迄今為止,關(guān)于住房市場對居民消費(fèi)的影響,國內(nèi)外的研究幾乎都是基于生命周期假說或持久收入假說來探討房價(jià)對居民消費(fèi)的財(cái)富效應(yīng)。Elliott證實(shí)了住宅價(jià)格上漲會導(dǎo)致消費(fèi)增加[1]。Engelhard分析PSID數(shù)據(jù)時(shí)發(fā)現(xiàn),住宅價(jià)格增長對住宅所有者消費(fèi)支出具有顯著性的促進(jìn)作用,且住宅價(jià)格波動(dòng)的邊際消費(fèi)傾向大約為0.03[2]。Case等利用美國 1982—1999 年各州的季度數(shù)據(jù)以及1975—1999年14個(gè)發(fā)達(dá)國家的數(shù)據(jù)對住宅市場和股票市場進(jìn)行了分析,發(fā)現(xiàn)住宅市場具有較強(qiáng)的財(cái)富效應(yīng)[3]。國內(nèi)多數(shù)學(xué)者基于房價(jià)的財(cái)富效應(yīng)對我國住房市場進(jìn)行實(shí)證檢驗(yàn)。劉建江等對我國房地產(chǎn)市場財(cái)富效應(yīng)做了定性分析,并從消費(fèi)函數(shù)理論探討了房地產(chǎn)財(cái)富效應(yīng)的作用機(jī)制,認(rèn)為持續(xù)上漲的房價(jià)能夠擴(kuò)大短期邊際消費(fèi)傾向[4]。賴溟溟和白欽先進(jìn)行實(shí)證研究發(fā)現(xiàn),我國存在房地產(chǎn)市場的財(cái)富效應(yīng),房地產(chǎn)市場長期與居民消費(fèi)協(xié)同趨勢,短期卻抑制居民消費(fèi)[5]。然而劉旦利用2000—2006年的季度數(shù)據(jù)進(jìn)行的實(shí)證研究表明中國城鎮(zhèn)住宅市場不具有財(cái)富效應(yīng)[6]。劉國風(fēng)對天津市2002年7月—2008年6月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的實(shí)證檢驗(yàn)發(fā)現(xiàn)天津市房地產(chǎn)價(jià)格的上漲對居民消費(fèi)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7]。總之,盡管這些學(xué)者分別對我國房地產(chǎn)市場的財(cái)富效應(yīng)進(jìn)行了探討,但結(jié)論卻不盡一致,因而從生命周期假說或持久收入假說出發(fā)來探討房地產(chǎn)市場的財(cái)富效應(yīng)可能有悖于我國在轉(zhuǎn)軌時(shí)期的具體國情。也有極少數(shù)學(xué)者從流動(dòng)性理論出發(fā)提出住房改革帶來的未來支出不斷增加會減少居民消費(fèi)和促進(jìn)居民儲蓄,如袁志剛和宋錚較早注意到住房改革后在購房方面大多數(shù)城鎮(zhèn)居民的消費(fèi)行為都受到流動(dòng)性約束的影響,提出住房改革是造成轉(zhuǎn)軌時(shí)期城鎮(zhèn)居民消費(fèi)傾向下降的一個(gè)重要原因[8],但他們沒有深入探討房價(jià)上漲對居民消費(fèi)降低的內(nèi)在微觀作用機(jī)制,也沒有進(jìn)行定量分析。
本文基于流動(dòng)性約束理論研究了住房改革后房價(jià)造成城鎮(zhèn)居民消費(fèi)不足的理論機(jī)制,之后根據(jù)理論模型進(jìn)行規(guī)范而詳細(xì)的定量分析,以考察住房改革對城鎮(zhèn)居民消費(fèi)需求的影響。
二、住房改革引發(fā)流動(dòng)性約束的機(jī)理分析
1.過度強(qiáng)調(diào)“只售不租”的商品房政策
目前城鎮(zhèn)私有住房占住房總量的85%以上,城鎮(zhèn)居民住房自有率達(dá)到74%左右,住房的自有率高于國際水平 (50%—70%)[9]。反過來看,這說明我國出租住房占總住房面積的比重不到15%,與一些發(fā)達(dá)國家形成鮮明的對比,其中美國為36%,加拿大為44%,法國為48%,瑞典為43%。可以看出:以出售公有住房和鼓勵(lì)居民購買住房為主導(dǎo)的改革,使得居民只能通過購買住房解決住房問題。盡管房改的關(guān)鍵是實(shí)現(xiàn)住房商品化,但住房商品化并不等于單一的買賣商品房,其實(shí)現(xiàn)途徑包括出租和銷售兩種途徑,只要租金達(dá)到商品化租金,則住房一樣也能實(shí)現(xiàn)商品化。雖然出租和銷售對實(shí)現(xiàn)住房商品化的作用是相同的,但是出租或銷售卻對需要解決住房問題的城鎮(zhèn)居民的生活會產(chǎn)生截然不同的影響。如果我國加快租房市場建設(shè),城鎮(zhèn)居民就可避免在當(dāng)前或?qū)硪蛐柚Ц洞蠊P的購房款而發(fā)生的流動(dòng)性約束。相反,如果只強(qiáng)調(diào)購房是解決住房的唯一途徑,大部分城鎮(zhèn)居民就可能在當(dāng)前或?qū)硪蛐柚Ц洞蠊P的購房款而發(fā)生流動(dòng)性約束。
2.住房金融發(fā)展滯后
雖然抵押貸款能讓買房者分期支付住房價(jià)格的70%,但30%的首期付款仍然高于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以全國平均標(biāo)準(zhǔn)來衡量,一個(gè)家庭如果夫婦都有工作,需要拿出年收入的11倍去購買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10]。也就是說,按每平方米3 000元計(jì)算,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需要24萬元,其中首期付款就是7.2萬元。對于一個(gè)工薪家庭來說,如果居民當(dāng)期或未來某期因購房需支付7.2萬元,那么這個(gè)家庭很可能因購房而發(fā)生流動(dòng)性約束。而當(dāng)房價(jià)由每平方米3 000元上漲到4 000元時(shí),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就需要32萬元,其中首付款就達(dá)9.6萬元,這就意味著居民也要為首付儲蓄更多的財(cái)富,且居民在當(dāng)期和未來某期發(fā)生流動(dòng)性約束的可能性也會增加。
3.住房供給與城鎮(zhèn)居民購買力脫節(jié)
近些年,商品住宅平均銷售價(jià)格急劇上漲,部分大中城市房價(jià)上漲更為迅猛,有的平均房價(jià)漲幅已連續(xù)好幾年超過15%。按照國際上認(rèn)可的住房價(jià)格收入比,房屋價(jià)格應(yīng)當(dāng)是家庭年收入的3—6倍,由于我國商品房市場不斷地完善,從2003年起商品住宅價(jià)格指數(shù)每年的增長幅度都在5%以上,這使得我國房屋價(jià)格與家庭年收入的比值遠(yuǎn)遠(yuǎn)高于國際上認(rèn)可的水平。在商品住宅中,中低價(jià)位、中小戶型住宅供應(yīng)比例偏低。在部分城市,100平方米/套以上商品住宅占總量的60%—70%,有的城市高達(dá)87%。2004年全國經(jīng)濟(jì)適用住房開發(fā)投資出現(xiàn)負(fù)增長,占房地產(chǎn)開發(fā)投資的比重由上年的6.1%下降到4.6%,有的地區(qū)甚至停止了經(jīng)濟(jì)適用住房建設(shè)[9]。由于我國城鎮(zhèn)勞動(dòng)力市場出現(xiàn)了整體供過于求,勞動(dòng)工資常常被壓低,使得工資增長率有限。目前住房補(bǔ)貼的實(shí)施不到位。
4.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加快
隨著我國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的進(jìn)程加快,大量的農(nóng)村剩余勞動(dòng)力遷往城鎮(zhèn),使得我國城鎮(zhèn)人口急劇上升。我國城鎮(zhèn)化率在歷經(jīng)了1995年之前的停滯后,便以每年的1個(gè)百分點(diǎn)的速度增長,其中房改后的1999年城鎮(zhèn)化率增長了2個(gè)百分點(diǎn),到2009年,達(dá)到47%,比1995年29%的城鎮(zhèn)化率增長了18個(gè)百分點(diǎn)。城鎮(zhèn)化是一個(gè)農(nóng)村人口轉(zhuǎn)化為城鎮(zhèn)人口的過程。農(nóng)村人口在面臨當(dāng)前“只售不租”的商品房政策、住房金融的制約以及住房供給的不合理的情況下,他們?yōu)槎ň映鞘卸M(jìn)行購房時(shí)更容易發(fā)生流動(dòng)性約束。
三、一個(gè)引入購房支出的流動(dòng)性約束模型
基于住房改革后在購房方面大多數(shù)城鎮(zhèn)居民的消費(fèi)行為都受到流動(dòng)性約束的影響的事實(shí),本文在借鑒Deaton[11]等經(jīng)典文獻(xiàn)的基礎(chǔ)之上,構(gòu)建一個(gè)包含流動(dòng)性約束的持久收入假說模型,在模型中加入一次性的購房支出,則典型消費(fèi)者面臨的消費(fèi)規(guī)劃問題如下:

其中,E0=E[·|0]基于0期所有信息的條件期望;β為貼現(xiàn)因子;u(·)為齊次凹函數(shù);Ct為t期實(shí)際消費(fèi)支出;Wt為t期的收入;r為利率;At為t期資產(chǎn);Zt+1(p)為在第t+1期需要進(jìn)行的購房支出,為外生變量且與p正相關(guān),其中p為商品住宅價(jià)格。上述表達(dá)式暗含Ct、Wt發(fā)生在t期末,At發(fā)生在t-1期末或t期初,居民決策發(fā)生在t期末。
1.不考慮購房支出的消費(fèi)決策
由于在住房改革之前,我國實(shí)行的是公用單位提供福利分房的住房政策,城鎮(zhèn)居民在當(dāng)期或未來無購房支出。這時(shí)不考慮流動(dòng)性約束問題,(1)式所示的最優(yōu)規(guī)劃可轉(zhuǎn)化為:

因此,其最大化問題的拉格朗日函數(shù)為:

分別對Ct和At+1求導(dǎo),得:

把 (4)代入 (5)式得:

(6)式表明,當(dāng)居民預(yù)期不存在流動(dòng)性時(shí),最優(yōu)消費(fèi)路徑就為“理性預(yù)期—永久收入假說”的歐拉方程所描述的消費(fèi)路徑。即在沒有購房支出時(shí),居民可以通過自由出售資產(chǎn)或借貸來實(shí)現(xiàn)其跨期消費(fèi)效應(yīng)總和的最大化。
2.考慮購房支出的消費(fèi)決策
住房改革后,無住房的居民可能在當(dāng)期或未來某期因購房支出而發(fā)生流動(dòng)性約束。若居民預(yù)期流動(dòng)性約束在t期生效,(1)式所示的最優(yōu)規(guī)劃就為:

s.t.At+1≥Zt+1(p),如果在 t+1期有住房支出
因此,其最大化問題的拉格朗日函數(shù)為:

由于Zt+1(p)為預(yù)期在t+1期的購房支出,為外生變量。對At+1求導(dǎo),得:

其歐拉方程為:

根據(jù)庫恩—塔克條件,如居民預(yù)期流動(dòng)性約束在第t期生效,即At+1=Zt+1(p),有λt>0,則下面的不等式便成立:

其中,α=β(1+r)。即 t期歐拉方程不再成立,但之前和之后歐拉方程仍成立。

從 (12)式可以看出:一旦因購房支出而在t期發(fā)生的流動(dòng)性約束時(shí),居民就會減小第t期及其之前各期的消費(fèi),并進(jìn)行強(qiáng)制性儲蓄。
為了更清楚地考察購房支出對居民的第t期以及之前各期的消費(fèi)的影響,可把Ai+1=Zi+1(p)代入 (1)式得:

可發(fā)現(xiàn)居民在第t期的消費(fèi)驟然下降。為防止約束期消費(fèi)大幅度下降,理性居民就會平滑約束期及其之前各期消費(fèi),因而位于無流動(dòng)性約束時(shí)最優(yōu)消費(fèi)路徑的下方。
3.預(yù)期住房價(jià)格上漲的消費(fèi)決策
假定第t期的勞動(dòng)收入、資產(chǎn)和居民預(yù)期的購房面積不變,且第t期借債上限保持不變。當(dāng)居民預(yù)期住房價(jià)格由p上漲到p'時(shí),由于Zt+1(p)與p成正相關(guān),則下面不等式成立:

把 (14)帶入 (1)式中,并與 (13)式進(jìn)行比較,得到:

由于在約束期之前的各期的邊際消費(fèi)傾向相等,即 (11)左側(cè)成立,因而結(jié)合 (15)和(12)式,可知:

其中,0<a<1,b>0,這里我們省略了一個(gè)常數(shù)項(xiàng)。pt+1為居民預(yù)期第t+1期的住宅商品房價(jià)格。即如果居民預(yù)期因購房而在第t期發(fā)生流動(dòng)性約束時(shí),那么當(dāng)預(yù)期房價(jià)上漲時(shí)居民就會進(jìn)一步減少在第t期及其以前各期的消費(fèi),因而居民預(yù)期第t+1的房價(jià)與第t期及以前各期的消費(fèi)成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
若假定居民以適應(yīng)性預(yù)期的方式來判斷第t+1期的住宅商品房價(jià)格時(shí),即用當(dāng)期的滯后一期住宅商品房價(jià)格去判斷第t+1期的住宅商品房價(jià)格,這時(shí) (16)式可以改寫為:

而 (17)可以進(jìn)一步簡化為:

四、住房改革、流動(dòng)性約束與城鎮(zhèn)居民消費(fèi)不足的實(shí)證檢驗(yàn)
1.住房改革對居民消費(fèi)需求結(jié)構(gòu)性影響
(1)模型構(gòu)建與數(shù)據(jù)說明
1998之前,我國的住房制度就是一個(gè)由公有部門逐步將公有住房出售給單位職工的一個(gè)過程,城鎮(zhèn)居民可以以低于市場價(jià)格買到公有住房,由于住房價(jià)格與政府出售價(jià)格之間的巨大差異,使得分到住房的家庭獲得了一筆很大轉(zhuǎn)移財(cái)富。由于福利住房制度存在,無住房的城鎮(zhèn)居民預(yù)期將來也能獲得福利房,因而他們對房價(jià)的變動(dòng)并不關(guān)心。而1998年住房改革結(jié)束了實(shí)行40余年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無住房的城鎮(zhèn)居民不得不面臨來自將來某期購房支出的壓力,這種支出很有可能會引發(fā)居民在未來某期的面臨流動(dòng)性約束生效。而房價(jià)上漲則預(yù)示著居民未來購房支出的增加,且發(fā)生流動(dòng)性約束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因此住房改革之前與之后的房價(jià)可能會對我國城鎮(zhèn)居民消費(fèi)產(chǎn)生結(jié)構(gòu)性的改變。本文選取的研究區(qū)間為1991—2008年,并引進(jìn)虛擬變量來檢驗(yàn)住房改革所帶來的結(jié)構(gòu)性變化。模型如下:

為城鎮(zhèn)家庭人均在第t期的消費(fèi)性支出;IPt為城鎮(zhèn)家庭人均在第t期的可支配收入;HPt-1為在第t-1期的住宅商品房的銷售價(jià)格;υt為隨機(jī)誤差項(xiàng)。
盡管我國1998年末在全國范圍內(nèi)停止實(shí)物福利分房政策,但從1998—1999年,總體上的福利住房實(shí)物分配并沒有停止,同時(shí)由于我國土地市場的滯后,導(dǎo)致在2000年才實(shí)現(xiàn)以停止福利分房為核心的住房改革,因此本文以2000年作為斷點(diǎn)。其指標(biāo)包括城鎮(zhèn)家庭人均的消費(fèi)性支出、城鎮(zhèn)家庭人均的可支配支出、住宅商品房的銷售價(jià)格,其數(shù)據(jù)均來自1991—2008年的《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并用以1991年為基期的城鎮(zhèn)居民消費(fèi)價(jià)格指數(shù)對上述三個(gè)變量進(jìn)行價(jià)格平減。
(2)檢驗(yàn)結(jié)果及其分析
本文借助Eviews6.0對方程 (19)進(jìn)行OLS估計(jì),并剔除不顯著項(xiàng),估計(jì)結(jié)果見表1所示。

表1 OLS法模型檢驗(yàn)結(jié)果
從實(shí)證結(jié)果看,在1999年及其以前,房價(jià)的滯后一期,即居民對未來房價(jià)的預(yù)期,對居民消費(fèi)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jìn)作用。滯后一期的房價(jià)上漲1元會促使平均城鎮(zhèn)家庭消費(fèi)支出增加0.15元。這說明在住房改革完成之前,由于無住房城鎮(zhèn)居民不必考慮購房支出對其消費(fèi)的影響,而有住房的城鎮(zhèn)居民預(yù)期其財(cái)富隨著房價(jià)的上漲而增加,進(jìn)而增加當(dāng)前消費(fèi),從而拉動(dòng)整體居民消費(fèi)上升。在住房改革完成后,房價(jià)滯后項(xiàng)對居民消費(fèi)增加具有顯著的負(fù)效應(yīng),即滯后一期的房價(jià)上漲1元會促使平均城鎮(zhèn)家庭人均年消費(fèi)性支出減少0.56(=0.15-0.71)元,這說明住房改革完成之后,無住房城鎮(zhèn)居民必須考慮將來購房支出對其消費(fèi)的影響,即預(yù)期未來某期可能因購房支出而發(fā)生流動(dòng)性約束,這時(shí)為了避免在流動(dòng)性約束生效時(shí)消費(fèi)驟然劇降,他們會在當(dāng)期減少消費(fèi),增加儲蓄。這時(shí)隨著我國城市化的加快,需購房的城鎮(zhèn)居民大幅度增加,有住房的居民占城鎮(zhèn)總?cè)丝诘谋壤诓粩嗟販p少,因而房價(jià)的財(cái)富效應(yīng)也就非常有限,這時(shí)房價(jià)上漲就會抑制城鎮(zhèn)居民消費(fèi)。
2.住房改革引發(fā)城鎮(zhèn)居民流動(dòng)性約束的實(shí)證檢驗(yàn)
(1)模型構(gòu)建與數(shù)據(jù)說明
在城鎮(zhèn)居民的住房借貸能力不變及工資和資產(chǎn)水平一定情況下,又由于購房支出與房價(jià)成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這時(shí)房價(jià)越高,則居民預(yù)期將來的購房支出就會越大,因而要為了購房儲蓄更多財(cái)富,且發(fā)生流動(dòng)性約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而本文把住宅商品房價(jià)格作為流動(dòng)性大小的替代變量。由于各個(gè)省 (市、區(qū))的城鎮(zhèn)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將對全國整體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研究結(jié)果直接推廣到各個(gè)省是不科學(xué)的。因此,本部分的研究對象為1999—2008年的30個(gè)省 (市、區(qū))(不包括港澳臺和西藏)的面板數(shù)據(jù),以進(jìn)一步驗(yàn)證各省住宅商品房價(jià)格與城鎮(zhèn)居民消費(fèi)性支出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用 CPit表示 i省(市、區(qū))在第t年的城鎮(zhèn)家庭人均年消費(fèi)性支出;IPit表示i省 (市、區(qū))在第t年的城鎮(zhèn)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HPit-1表示i省 (市、區(qū))在第t-1年住宅商品房的銷售價(jià)格;υit為誤差項(xiàng)。由于各省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存在著較大差異,所以本文選用面板數(shù)據(jù)的個(gè)體固定效用模型:

若β2顯著地為負(fù),則表明房價(jià)的上漲會對城鎮(zhèn)居民的消費(fèi)具有抑制作用,即住房改革后大多數(shù)居民可能預(yù)期因?qū)淼馁彿慷a(chǎn)生流動(dòng)性約束,為了防止約束期消費(fèi)驟降,就會減少當(dāng)前消費(fèi)。
其中城鎮(zhèn)家庭人均的消費(fèi)性支出、城鎮(zhèn)家庭人均的可支配支出和住宅商品房的銷售價(jià)格的數(shù)據(jù)均來自1999—2008年的《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對30個(gè)省 (市、區(qū))(不包括港澳臺和西藏)的各年的相關(guān)統(tǒng)計(jì),并以各自1999年為基期的城鎮(zhèn)居民消費(fèi)價(jià)格指數(shù)進(jìn)行平減。
(2)單位根與協(xié)整檢驗(yàn)
首先,進(jìn)行單位根檢驗(yàn)。在面板單位根檢驗(yàn)中,LLC檢驗(yàn)、Breitung檢驗(yàn)及Hadri檢驗(yàn)為同質(zhì)面板單位根的代表性檢驗(yàn)方法,IPS檢驗(yàn)、Fisher-ADF檢驗(yàn)和Fisher-PP檢驗(yàn)為異質(zhì)面板單位根的代表性檢驗(yàn)方法。為了避免因檢驗(yàn)方法本身的局限而對檢驗(yàn)結(jié)果帶來的負(fù)面影響,本文將同時(shí)采用 LLC、IPS、ADF-Fisher和PPFishers四種方法對各個(gè)變量進(jìn)行單位根檢驗(yàn)。表2給出了三個(gè)變量的單位根檢驗(yàn)結(jié)果。其中,單位根檢驗(yàn)過程中的最優(yōu)滯后期數(shù)是按Schwarz評價(jià)標(biāo)準(zhǔn) (SC)確定。

表2 單位根檢驗(yàn)結(jié)果
從表2可以看出,無論是針對同質(zhì)面板假設(shè)的LLC檢,還是針對異質(zhì)面板假設(shè)的IPS檢驗(yàn)、Fisher-ADF檢驗(yàn)和Fisher-PP檢驗(yàn),三個(gè)變量基本上都是不平穩(wěn),而在一階差分情況下是平穩(wěn)的,因而認(rèn)為各變量均為一階單位根過程。
其次,進(jìn)行協(xié)整檢驗(yàn)。由于各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因而可以進(jìn)行面板協(xié)整檢驗(yàn)。目前有兩類面板數(shù)據(jù)協(xié)整檢驗(yàn)方法:一類是基于回歸殘差的面板協(xié)整檢驗(yàn),即Engel-Granger二步法的推廣,如Pedroni檢驗(yàn)和Kao檢驗(yàn);另一類是從推廣Johansen檢驗(yàn)方法的方向發(fā)展的面板數(shù)據(jù)協(xié)整檢驗(yàn),如Johansen-Fisher檢驗(yàn)。由于本文樣本量有限,不能采用該檢驗(yàn)方法,只能采用上述的Kao檢驗(yàn)和Pedroni檢驗(yàn)進(jìn)行面板的協(xié)整檢驗(yàn),結(jié)果見表3所示。

表3 Kao檢驗(yàn)和Pedroni檢驗(yàn)結(jié)果
從表3可知,無論P(yáng)edroni檢驗(yàn)的組內(nèi)統(tǒng)計(jì)量或組間統(tǒng)計(jì)量,都表明變量之間具有顯著協(xié)整關(guān)系,而且Kao檢驗(yàn)的統(tǒng)計(jì)量來看,也支持變量之間具有顯著協(xié)整關(guān)系的結(jié)論。因此認(rèn)為城鎮(zhèn)家庭人均實(shí)際年消費(fèi)性支出與城鎮(zhèn)家庭人均實(shí)際可支配收入及住宅商品房的實(shí)際銷售價(jià)格之間存在穩(wěn)定的長期關(guān)系。
(3)檢驗(yàn)結(jié)果及其分析
因?yàn)槲覈?0個(gè)省份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存在較大的個(gè)體差異性,所以對方程 (20)進(jìn)行加權(quán)估計(jì);又因?yàn)闅埐羁赡艽嬖谝浑A自相關(guān),因此通過添加AR(1)項(xiàng)進(jìn)行修正。估計(jì)結(jié)果見表4所示。

表4 GLS法模型檢驗(yàn)結(jié)果
從 (b)的回歸結(jié)果看,在全國平均水平上,住宅商品房價(jià)上漲導(dǎo)致城鎮(zhèn)居民消費(fèi)需求下降。滯后一期的房價(jià),即居民預(yù)期將來的住房價(jià)格與居民消費(fèi)需求在顯著性水平為1%的條件下成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從數(shù)量上來看,滯后一期的房價(jià)上漲1元將導(dǎo)致平均城鎮(zhèn)家庭人均年消費(fèi)性支出減少0.16元。這些充分表明了1998年住房改革后大部分城鎮(zhèn)居民可能預(yù)期因?qū)淼木薮蟮馁彿恐С龆l(fā)流動(dòng)性約束,為了防止約束期的消費(fèi)驟降,從而減少當(dāng)前消費(fèi)。房價(jià)的上漲則預(yù)示著未來的購房支出的增加,這不僅要求居民為未來的購房儲蓄更多的財(cái)富,而且也增加了居民因購房而發(fā)生流動(dòng)性約束的可能性,這時(shí)理性居民會進(jìn)一步減少消費(fèi)和增加儲蓄。
五、結(jié)論與政策啟示
通過實(shí)證檢驗(yàn),本文得出如下兩個(gè)結(jié)論:第一,住房改革后,房價(jià)對城鎮(zhèn)居民消費(fèi)需求的影響產(chǎn)生結(jié)構(gòu)性改變。在1999年及其以前,滯后一期的房價(jià)對居民消費(fèi)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jìn)作用,這時(shí)房價(jià)上漲表現(xiàn)為財(cái)富效應(yīng)。在1999年之后,滯后一期的房價(jià)對居民消費(fèi)增長具有顯著的負(fù)效應(yīng),這說明大部分城鎮(zhèn)居民在住房改革后必須考慮因未來購房支出而可能產(chǎn)生的流動(dòng)性約束。第二,在全國平均水平上,滯后一期的房價(jià),即居民預(yù)期未來購房時(shí)的房價(jià)與居民消費(fèi)需求顯著地成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即滯后一期的房價(jià)上漲1元,會導(dǎo)致平均城鎮(zhèn)家庭人均消費(fèi)性支出減少0.16元。這說明房價(jià)上漲,不僅預(yù)示著他們在未來面臨的流動(dòng)性約束的可能性增大,而且也預(yù)示著他們要為未來儲蓄更多的財(cái)富以購買住房,這使得他們不得不進(jìn)一步減少當(dāng)期消費(fèi)和增加儲蓄。
由于住宅商品房的銷售價(jià)格偏高是制約當(dāng)期城鎮(zhèn)居民消費(fèi)需求的主要因素,因而有必要抑制房價(jià)上漲,穩(wěn)定房價(jià),以改變大多數(shù)居民對將來房價(jià)上漲的預(yù)期,以防止居民消費(fèi)需求的下降。在穩(wěn)定房價(jià)的同時(shí),完善住房貸款機(jī)制、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加大廉租房建設(shè)和擴(kuò)大經(jīng)濟(jì)適用房,以降低居民預(yù)期因購房而發(fā)生流動(dòng)性約束的可能性,這些都會有助于拉動(dòng)居民消費(fèi)上漲。
[1]Elliott,J.W. Wealth and Wealth Proxiesin a Permanent Income Model[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0,5(3):509-535.
[2]Engelhard,G.V.House Price and the Decision to Save for Down Payment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es,1994,36(2):209-237.
[3]Case,K.E.,Quigley,J.M.,Shiller,R.J.Comparing Wealth Effects:The Stock Market vs.the Housing Market[J].Advances in Macroeconomics,2005,5(1):1-l5.
[4]劉建江,楊玉娟,袁冬梅.從消費(fèi)函數(shù)理論看房地產(chǎn)財(cái)富效應(yīng)的作用機(jī)制[J].消費(fèi)經(jīng)濟(jì),2005,(4):93-96.
[5]賴溟溟,白欽先.我國居民消費(fèi)財(cái)富效應(yīng)的實(shí)證研究[J]. 上海金融,2008,(8):15-18.
[6]劉旦.中國城鎮(zhèn)住宅價(jià)格與消費(fèi)關(guān)系的實(shí)證研究——基于生命周期假說的宏觀消費(fèi)函數(shù)[J].上海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8,(2):80-87.
[7]劉國風(fēng).房地產(chǎn)價(jià)格上漲是否促進(jìn)消費(fèi)并具有財(cái)富效用的統(tǒng)計(jì)檢驗(yàn)[J].現(xiàn)代財(cái)經(jīng),2009,(8):38-40.
[8]袁志剛,宋錚.消費(fèi)理論的新發(fā)展及其在中國的應(yīng)用[J]. 上海經(jīng)濟(jì)研究,1999,(6):2-9.
[9]賈康,劉軍民.我國住房改革與住房保障問題研究[J]. 財(cái)政研究,2007,(7):8-23.
[10]易憲容.中國的住房改革與住房金融發(fā)展[J].南方經(jīng)濟(jì),1999,(1):28-29.
[11]Deaton,A.Saving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J].Econometrica: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1991,59(5):1221-1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