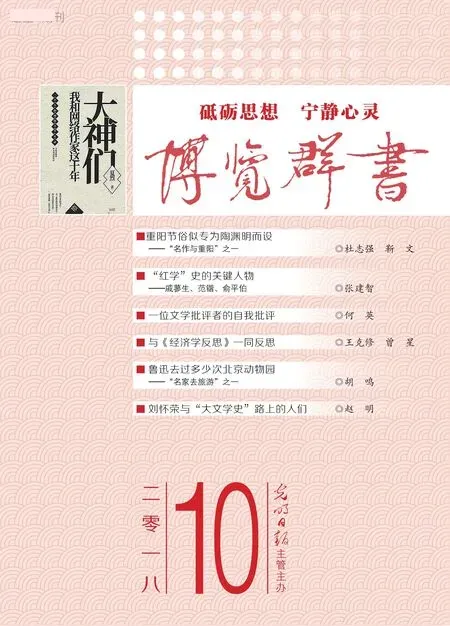明清出版的基礎研究
○陳梧桐

《十六—十九世紀中國出版研究》,章宏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明清是中國古代出版走向高度繁榮的鼎盛時期,存世的出版物數量繁多,相關的資料也極豐富。然而,目前有關明清出版的研究卻成果無多,水平也不很高,許多問題若明若暗,眾說紛紜,令人莫衷一是,有些問題甚至無人涉足,成為空白,凸顯基礎研究的不足。有鑒于此,章宏偉先生多年來致力于明清出版的基礎研究,選取明代杭州的私人出版、湯賓尹、胡正言、毛晉、《嘉興藏》、清代的滿文出版、揚州詩局刊刻《全唐詩》、馬國翰與《玉函山房輯佚書》、海關造冊處與中國近代出版業等若干課題進行個案研究,撰寫了一批學術論文,集成《十六—十九世紀中國出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下引該書只注頁碼)一書。
基礎研究要從史料的搜集做起。章先生供職的故宮博物院,藏有大量的明清文獻、宏富的清宮檔案以及殿版書版實物,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為他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他經常整天埋首其中,廣披博覽,手摩目驗,搜尋有用的史料。除此之外,他還通過各種渠道,從官修實錄、正史、方志、野史筆記、碑刻譜牒和各種文集之中挖掘史料。他還將目光投向海外,有時“為了一條難尋覓的材料,甚至求到了日本、臺灣,請友人幫助購買、復印”。(《自序》P8)由于廣泛的搜集與深入的發掘,章先生研究的每個課題都積累了大量史料,僅《方冊藏》一題,他就“找到了一百多萬字資料,一一輸入電腦”。(劉光裕《序言》P14)因此,書中的每篇論文,史料都非常豐富而翔實,幾乎每頁都有數量不等的腳注,有些頁面腳注的篇幅甚至超過正文。也就因此,書中的論述都能做到言之有據,不作無根之談,顯得厚重扎實,令人信服。
史料搜集到手之后,還有個鑒別的問題。史料缺乏或不足,固然無法展開研究,得不出結論;但如果史料不正確,卻會導致結論的錯誤,更是貽害無窮。章先生不僅重視史料的搜集發掘,更重視史料的審查考證。他狠下功夫,反復對史料進行認真的考證,去偽存真,力求做到史實考訂的準確。例如《嘉興藏》在五臺山的雕版地點,故宮一老專家曾據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提出妙德庵與妙喜庵兩地說。章先生對此說存有疑問,便將12000多卷的《嘉興藏》翻查了四遍,還將施刻文重新過錄一遍,都沒有找到妙喜庵雕刻過《方冊藏》的文字記載,從而斷定妙喜庵雕版之說,可能是將正藏第101函第4冊《大智度論》卷50第22頁施刻文中“德”字的異體字“惪”字誤認作“喜”字所致。又如海峽兩岸和日本的學者,從20世紀80年代起,紛紛撰文確認,從崇禎十四五年起,毛晉汲古閣參加了《嘉興藏》的刊刻。《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目錄》和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都將與毛晉有關的藏經著錄為毛晉汲古閣刊刻。章先生通過對《嘉興藏》的梳理,依據經文后面的施刻文,撰寫《五臺山妙德庵方冊藏刊刻編年》一文,逐年列出妙德庵的刻經活動,又寫了《毛晉與〈嘉興藏〉》一文,逐年排列崇禎十五、十六、十七年和順治年間毛晉參與《嘉興藏》的所有活動,發現毛晉作為一個佛教善信,曾捐資刊刻佛經作為功德,又曾出力參與虞山華嚴閣刊刻部分《嘉興藏》的校對工作,這兩部分藏經都非汲古閣所刊刻。毛晉經營的汲古閣極少刊刻佛經,但曾受云南木增委托,代刻《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愿常遍禮懺儀四十二卷》,后來木增將書版捐贈嘉興楞嚴寺;還曾刊刻《牧云和尚嬾齋別集十四卷》等,后來毛晉子輩將書版捐給寺院,隨同《嘉興藏》印刷流通。除代刻、捐贈書版外,汲古閣的刻工、書手都沒有參與《嘉興藏》的刊刻活動。因此,他認定:“這些與毛晉有關的藏經,都不能如《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目錄》、《“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著錄為毛晉汲古閣刊刻。”(P367)
學術研究貴在創新,而切忌人云亦云。由于作者勤于搜求,嚴于考證,這部論著多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例如,明代杭州的私人出版機構,以前張秀民《中國印刷史》著錄24或25家,羅樹寶說23家,顧志興說29家,葉樹聲、余敏輝說37家,繆詠禾說36家,張獻忠說42家。作者通過對《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等資料的梳理,參照各家的研究成果,統計出明代杭州的私人出版機構至少在223家以上(有的一人開設不同名號的機構,只按一家計算),從而提出明代杭州私人出版的地位需要重新認識,明代的出版地圖需要重建論點。又如對饾版、拱花技術是否為晚明胡正言十竹齋所發明,學術界意見分歧很大,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拱花技術始于唐代,饾版技術肇自宋代。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深入的探討,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十竹齋胡正言從萬歷末年開始出版《十竹齋書畫譜》,創立了彩色套印中“饾版”的技法,使印刷出具有水墨質感的彩色版畫成為可能。天啟六年(1626)吳發祥刻的《蘿軒變古箋譜》無論設計還是套印技巧,都較《十竹齋書畫譜》有所超越,特別是“拱花”這種具有“淺浮雕”效果的處理手法,在版刻工藝中獨具韻致。而《十竹齋箋譜》兼采“饾版”與“拱花”,作品水準較《書畫譜》又有所提高。這三譜在明代彩色套印版畫中是最具代表性的,標志著中國古代的彩色套版雕印技術達到了非常成熟、空前絕后的地步。(P67)
再如晚清的海關造冊處,這是中國最早官辦的具有現代概念的出版機構之一,它用中外文字刊印的多種出版物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某些課題的第一手甚至是唯一的資料,但是對它的發展歷史、制度建設、業績成就、地位作用等卻無人研究,只有個別的論著涉及到它的印刷廠以及印制的大龍郵票。作者翻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外務部檔案,結合當時的一些文獻資料,從出版史的角度,對海關造冊處作了專題研究,撰成《海關造冊處與中國近代出版》一文,對海關造冊處的建立、職位設置和職員、出版物的種類、編輯、發行分別作了梳理,勾畫出其發展脈絡及大體輪廓。通過研究,作者發現,以前學術界關注的多是西學東漸,重在引進,而海關造冊處則重在輸出,它出版的書刊,特別是有關中國國情的調查統計和各種重要進出口商品的調查報告對西方了解中國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在文章的末尾特地強調:“海關造冊處出版物如何向西方介紹中國,需要我們認真總結。”(P535)
任何學科的構建與發展,都離不開基礎研究。對于中國出版史這個新興學科,基礎研究尤顯重要。沒有基礎研究,就沒有新史料的發掘,新方法的發明,新理論的構建,學科就無從建立,也沒法發展。但是,基礎研究卻是一件艱苦的工作,需要花費很大的功夫,去翻檢浩如煙海的各種古籍和檔案,大海撈針似地查找有用的史料,再做認真細致的鑒別考訂,去偽存真,然后才能對這些史料進行歸納排比,分析研究,從中引出其固有的結論,發表自己的看法。這是一種慢工細活,不僅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而且十分枯燥煩悶,不是急功近利者所能為的。章先生覺得,“學問能夠帶來求知的樂趣,學問能夠產生發現的愉悅,學問還能夠帶來成就的滿足。當然,學問是苦樂相隨,但有苦才有甜,苦后才更甜”。因此,他樂此不疲,在工作之余長期堅持中國出版史的基礎研究。為此,他“放棄了應酬,舍棄了娛樂休息,每天晚上熬到深夜,第二天還要早早起來上班,沒有節假日;為寫一篇論文購買書刊資料的費用遠遠超過稿費所得”。(《自序》P9)在學術風氣十分浮躁的今天,但愿有更多的學者能像章先生那樣,沉下心來,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基礎研究之中,將我們的史學研究扎扎實實地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