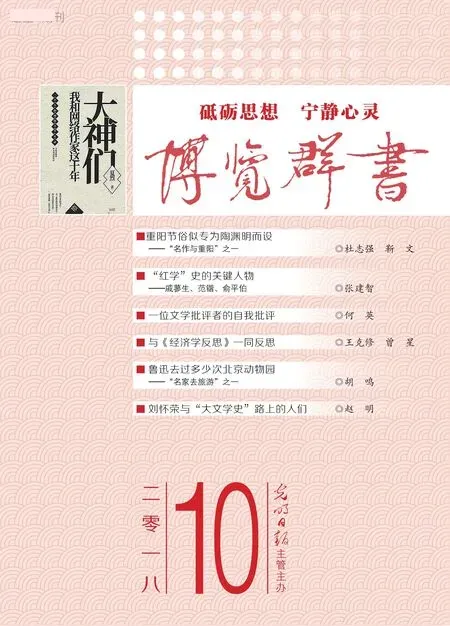中國的第一份英文刊物
○顧 鈞
《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由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 1801-1861)在廣州創辦、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的第一份英文月刊。它創辦于1832年5月,停辦于1851年12月,共20卷,232期。《中國叢報》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詳細記錄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后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這份刊物的原本現在已經很難一見,稍微常見的是日本一家出版社(Maruzen Co., Ltd)于1941年出版的影印本。2008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再次推出了影印本,極大便利了讀者的閱讀和學者的研究。

《中國叢報》,張西平主編、顧鈞、楊慧玲整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6月版
19世紀以來,西方人陸續在中國出版了各種西文報刊,近代中國最早的西文報紙是《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1822-1823),在澳門出版,為葡萄牙文。在《中國叢報》之前出版的英文報紙有兩份,一是《廣東紀錄》(Canton Register,1827-1843),一是《華差報與東鈔報》(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1831-1833),《 叢 報 》則是近代以來在中國出版的最早的英文期刊。兩家英文報紙雖然創辦早于《叢報》,但其中大部分是有關商業的內容,《華差報與東鈔報》創辦不久就停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刊載了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華專利權的文章。從份量上看,《叢報》每卷大約600頁,并不少于報紙,而從內容上看,則要豐富得多,幾乎涵蓋了中國的方方面面,它出版后很快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的最重要的信息來源。
1829年裨治文來華前夕,美國海外傳教部總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在給他的指示中提出這樣的要求:“在你的工作和環境允許的情況下,向我們報告這個民族的性格、習俗、禮儀——特別是他們的宗教如何影響了這些方面。”顯然,當時的西方人士對于這些方面的情況是了解很少的。裨治文來華后,更加深切地感覺到西方人關于中國知識的貧乏,中西之間的交流基本還是停留在物質層面,“思想道德層面的交流少之又少”,這樣的狀況不僅讓他感到“吃驚”,更使他感到“遺憾”。雖然明清之際的天主教傳教士寫過不少關于中國的報道和文章,但在裨治文看來,它們不僅魚龍混雜,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而且大都是多年前的信息了。他希望對中國進行全面的報道,提供更新和“不帶任何偏見”(《叢報》發刊詞)的信息。
裨治文的想法得到了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 支 持。馬禮遜是近代最早來華的傳教士(1807年),早在1817年5月,他就曾支持另外一位倫敦會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1785-1822)在馬六甲創辦了英文季刊《印支搜聞》(The Indo-Chinese Gleaner,1817-1822)。《印支搜聞》的內容包括“來自中國和其鄰近國家的各種消息;與印度、中國等國家相關的歷史、哲學、文學等方面的雜文逸事;譯自漢語、馬來語等語言的翻譯作品;關于宗教的文章;關于印度基督教傳道差會的工作進展;基督教世界的普遍狀況”。(米憐《新教來華最初十年》)這份堅持了五年的刊物對于英國人和其他歐洲人了解中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22年米憐去世后停刊。1827年馬禮遜計劃在馬六甲再次創辦一份名為《印支叢報》(Indo-Chinese Repository)的季刊,刊載有關印度、中國等國家的語言、哲學、習俗、文化的論文以及各地最新的信息。之所以選擇馬六甲,首先是因為它是英國的勢力范圍,倫敦會傳教士在那里已經打下了一些工作的基礎,此外馬六甲當地有不少華僑,與廣州的往來也十分便捷,有利于收集和傳遞有關中國的信息。但《印支叢報》的計劃后來未能實施,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馬禮遜會大力支持裨治文創辦《中國叢報》,因為這實際上也是在實現他自己早年的計劃。
裨治文辦刊物的想法也得到了當時在廣州的商人們的支持,特別是奧立芬(D.W. C. Olyphant,1789-1851)尤為積極,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廣州傳教站得到了所需的印刷設備。印刷機于1831年12月運抵廣州,鉛字也在數月后到達,這樣就解決了刊物的印刷問題。裨治文一開始不僅負責《叢報》的編輯,也負責印刷,1833年10月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1812-1884)作為傳教士、印刷工到達中國后,從裨治文手中接過了印刷工作,此后也參與《叢報》的編輯。1844年11月衛三畏回美國休假后,裨治文接管了衛三畏的工作,1847年5月裨治文去上海參加圣經中文本修訂,將《叢報》交給自己的弟弟負責,直到1848年9月衛三畏返回廣州為止,此后《叢報》完全由衛三畏負責,直到停刊。《叢報》最初是在廣州印刷,1836年印刷所搬至澳門,1844年10月搬至香港,1845年7月再次搬回廣州,直到停刊。
促使裨治文辦刊的一個更為直接的原因是德國傳教士郭實獵(Karl Gutzlaff,1803-1851)的日記。1831年,郭實獵不顧清政府的禁令,乘船沿中國海岸航行,從曼谷出發直到天津,歷時半年(6月至12月)。他的日記詳細記錄了沿途的所見所聞。1832年1月,裨治文結識了郭實獵,當時郭實獵剛剛結束了第一次冒險,又在準備第二次冒險(后來又有第三次)。郭實獵的日記引起了裨治文的極大興趣,在當時外國人的活動范圍只能局限在廣州、澳門的情況下,郭實獵的日記無疑具有很高的資料價值,裨治文希望為這份難得的目擊實錄盡快提供一個發表的陣地。《叢報》創刊后,郭實獵的日記以連載的形式與讀者見面,成為最初幾期的主要文章。
1834年以前《叢報》各期的體例基本固定,主要由以下幾個欄目組成:書評(Review),是對西方有關中國的新舊出版物的學術評論;上述出版物的內容節選,通常以游記和日記為主;雜記(Miscellanies),篇幅較短而帶有知識性的各類文章以及讀者來信;宗教消息(Religious Intelligence),關于各地傳教活動和宗教事務的報道;文藝通告(Literary Notices),各地有關教育、文藝和出版等的近況;時事報道(Journal of Occurrences),相當于新聞報道,一般篇幅短小,僅有個別的比較詳盡,信息的一個主要來源是清政府官方的《京報》。“《京報》所載,首宮門抄,次上諭,又次奏摺,皆每日內閣所發抄者也。以竹紙或毛太紙印之,多者十余頁,少者五六頁;以黃色紙為面;長達六寸,寬約三寸。”(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在翻譯《京報》方面,馬禮遜的貢獻最多。1834年5月以后《叢報》不再按內容劃分,而是以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來標注文章,但書評、文藝通告、時事報道、宗教消息等基本欄目都予以保留,沒有什么變化,比較顯著的變化是宗教消息逐漸減少,而書評和其他有關中國社會、文化的內容不斷增多。所刊文章涉及的范圍包括中國政治、經濟、地理、歷史、法律、博物、貿易、語言等方方面面。所以《叢報》雖然是傳教士所辦,投稿者也主要是傳教士,但宗教內容并不是主要的,重點是對中國國情的報道和介紹。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的開放,《叢報》的作者隊伍逐漸擴大,除傳教士之外,外交官、商人、旅行家、軍事將領等也紛紛給《叢報》投稿,美國學者白瑞華(R. S.Britton)指出,20年來《叢報》的“作者名單完全就是當時在華的英美中國研究者的名單”。(《近代中國報刊史》)
《叢報》第1、2卷每期各印刷400冊,第3卷增加到800冊,第4卷后增加到1000冊。這是一個不小的數量,因為當時西方著名的刊物如《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和《西敏寺評論》(Westminster Review)的印刷量也只不過是3000冊左右。《叢報》采取銷售和贈送相結合的發行方式,讀者對象主要是在中國、美國和歐洲的西方人士。以1834年為例,《叢報》在中國的發行量是200冊,美國160冊,英國40冊。但數字不能說明一切,因為《叢報》的贈送對象包括上述兩家著名雜志在內的多家西方雜志,它們常常轉載和引用《叢報》上的內容,使許多沒有看到《叢報》的人也同樣能夠了解鴉片戰爭前后中國的情況。
《叢報》的停刊,無論對于創辦者、編輯者還是作者們來說都是一件遺憾的事情。停刊的原因有多個,最重要的是經濟困難,《叢報》的資金一方面來自于銷售所得,另外則來自于商人的資助,特別是奧立芬的大力資助,1851年奧立芬在回美國途中去世,使裨治文和衛三畏失去了堅強的經濟后盾,成為《叢報》停刊的直接原因。《叢報》在前10年還可以依靠銷售收入自給自足,但從1844年開始便逐年虧損,每年約300-400美元,最后一年(1851)只有300訂戶,實在難以為繼。裨治文的離去也使衛三畏越來越感到獨木難支,1851年底,衛三畏決定停刊,給這份重要的刊物劃上了句號。
在《叢報》創辦之前,歐洲已經出版有多種亞洲研究刊物,如倫敦的《皇家亞洲學會通訊》(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巴黎的《亞洲學刊》(Journal Asiatique),但正如它們的標題所顯示的,它們是以“亞洲”作為研究對象,中國只是其內容的一部分。前文提到的《印支搜聞》雖然給中國以不小的篇幅,但南亞、東南亞的情況也是其關注的重要對象。《叢報》是西方第一份主要以中國為報道、研究對象的刊物,它的出版無疑具有相當的歷史意義,對于當下中國的清史研究者來說尤有極重要的文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