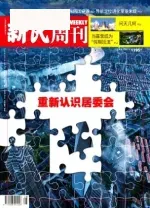《少林寺傳奇》:呼喚真功夫
張襦心


“其實每個人的夢想不一定都是練武。它傳達的就是一種精神,做什么事,都要真功夫!”
2月12日深夜,藍色月光副總經理陸健收到了齊魯電視臺發來的“賀電”:《少林寺傳奇》第三部《大漠英豪》,收視率扶搖直上,出乎意料。
眾武星打得賣力。
寒冷的冬季,在西北的雪谷、冰河、戈壁、沙漠、沙塵暴中暴打了240天。有道是“極端惡劣的天氣,催生了極端深刻的思想”。著名演員劉家輝說:“在賀蘭山的冰天雪地中打,在戈壁上八級大風中打,呼出一口氣能變成冰茬子,吸進一口氣能讓人產生站在天地間的浩然正氣。雖然是很艱苦的,但的確過癮,我覺得這是一種對中國武術一次真切的體驗。”
觀眾看得過癮。
有人說:“想看的就是這種原生態的功夫,這種一拳一腳的打,鼻涕一把淚一把的打。”
汶川大地震過后,記者去采訪重建后的災區人民生活情況,一進防震棚,發現災區百姓一家老小正圍著捐獻的電視機在看《少林寺傳奇》。他們說:“這個打得好看,也看著讓自己有股勁。”
作為一部電視劇,《少林寺傳奇》本身也創造了一個傳奇。
在不景氣的國產電視劇中,獨此一家形成一道奇特的“華流”:曾在海外30多家電視臺播出,翻譯成8種語言。并成為包括日本本國電視劇在內,唯一在日本主流電視臺黃金檔一播就是6年的“常青樹”。
導演都曉倡導的“功夫文化”,正逐步從臺下走向臺上,成為國家化的交流語言。不久前,中國外交部宴請各國駐中國大使文化聚餐,在選什么禮品上有點拿不準。突然發現了《少林寺傳奇》,通知都曉趕緊準備300套英文版。
“我就是要借娛樂的手段,把一種文化往外推,目的性很明確。”都曉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表示。
而在5年前,都曉剛提出要拍“真功夫”,就遭到一致反對。武俠劇已經在走下坡路,甚至淪落到電視臺一看就不肯買的地步。第一部拍完組織看樣片,4家電視臺,有3家當場打出了否決票。
哪里新鮮,就想去嘗試
新民周刊:身為河南電視臺副總編,為什么對拍電視劇這么熱衷?
都曉:人一定要嘗試各種可能性,要不活著就太虧了。我是學新聞的,廣院的新聞系,有很多人都是“不務正業”,比較叛逆。比如我們班的崔永元,還有魏永剛,原來是歡樂傳媒的老總,后來搞投資去了。我則跑到影視圈里做電視劇導演。
新民周刊:聽說你剛出道的時候,拍的一系列都是農村題材,被稱為“農民導演”。
都曉:剛改革開放的時候,社會的焦點就在農村。1988年的時候,電視劇2集、3集都算大戲。我拍了一個1集的,40分鐘,叫做《蒼茫的村莊》,根據我自己的小說改編的。那時候拍電視劇花不了多少錢,電視臺投了一點,我們車隊隊長社會關系比較多,又幫我去地方上拉了一筆贊助,還沒播呢就給斃了。
新民周刊:當時的電視臺還挺開放,支持你“不務正業”。
都曉:他們一開始沒想到我會拍成這樣(笑),都是鉆漏洞的事,本來是一個行業片,選題很正,結果被我給拍成藝術片了。故事大意是有個鄉村很貧窮,兄弟倆娶了一個媳婦,就拍他們怎么過。哥哥進屋了,弟弟就在外站著,一只狗陪著他,看月亮。弟弟進屋了,換成哥哥在外面陪著那只狗看月亮。現在想想,這是我拍得最好的電視劇,很含蓄、很美、很詩意化,特別像電影。所有人看了都說畫面真好,感覺到里面的東西了,可惜政治上不過關。這個事讓幾個投資者認識到都曉有才氣,就是思想太自由。
我拍的第二部電視劇也很有戲劇性。1990年底,臺里終于又允許我導戲了。給了我一個命題作文:抗洪救災。劇本總共只有30頁稿紙,9000字。那個意思很明確:都限定死了,總不可能再出亂子。沒想到我自己跑到災區考察之后,把30頁的稿紙改成了一個上下集的劇本,出來以后又給斃掉了。本來上頭希望的是洪水一來,救援部隊就來了。結果我沒有再現部隊,而是再現了一群村民逃到了一個偏遠的小山坡,等了一個禮拜還沒有人來救他們,他們是如何在這個被遺忘的孤島上展開自救的。有點像諾亞方舟,有人出去找糧食,發現大水無邊無際,又回來了。我并沒有拍他們很急躁、人性惡的一面,而是拍了他們互相之間的關愛,其實立意很大氣。名字就叫《太陽暖融融》,大家在下雨天等太陽,像散文詩一樣美。從這部開始,我拍的電視劇每一部都得獎。
拯救武學
新民周刊:你為什么會想要做功夫這個題材?
都曉:當時河南省政府希望能出一部代表河南文化的戲。一開始領導們的意圖不是想做功夫片,而是想做全面表現抗日的戲,大家都覺得不好把握,我后來就提出能不能我自己選。想來想去,選中了少林寺這個題材。基于我在國外跑得多,從非洲到美洲、歐洲,人家見到中國人,馬上會沖口而出:哦,功夫!
外國人對中國什么都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歷史不感興趣,現實生活更沒有可以溝通的地方。除了奧運會讓他們認識到原來中國那么大,他們唯一能接受的就是功夫,并且認為中國的功夫才是功夫,這一點給我震撼很大。中國功夫其實是讓國際社會了解中國的近道。
而國內恰恰是把功夫劇當成邊緣了,這是文化的不對接。想要什么,你不給他。不想要什么,你非給他。所以我們的電視劇往往在走出國門以后遇冷,即使硬送,人家也是扔到一邊根本不看。
新民周刊:中國功夫在國外知名度那么高,要感謝李小龍?
都曉:李小龍確實對中國功夫的傳播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還有很多孩子在少林寺學了功夫之后,好多都跑到國外去當保鏢、開武校,遍布世界各國,我走到哪里都能見到少林寺。一開始還只是局限在華人圈,后來慢慢被當地人接受。俄羅斯的少林武術班,連普京的女兒都去學。所以普京到中國來,就兩天時間,還專門去了一趟少林寺。南非也有一個少林佛學院。我在肯尼亞拍戲,有個黑人小孩來找工作,會打中國功夫,中國話也說得很溜。
新民周刊:武術在中國發展的現狀是怎樣的,這些孩子們為什么紛紛選擇出國謀發展?
都曉:在中國,武術只局限于體育項目,而且拼命取消實戰性,讓它變成一種表演賽,這么發展武術實際上是在毀滅武術。
孩子們學了武術之后,除了參加比賽,在國內無用武之處,只能做保安。早幾年連保安也沒有。而海外小孩從十幾歲開始就熱衷學功夫。文藝表演好簽證,很多小孩為了求生存,就跑到國外去不回來了。
新民周刊:你拍《少林寺傳奇》,是不是有振興中國武學的意思?
都曉:對。從中國武學來說,希望能夠拯救一下,讓它作為中國文化的一種受到更多重視。
新民周刊:武俠片已經被拍泛濫了,觀眾都產生了審美疲勞。你當初拍的時候,大家看好嗎?
都曉:不看好,大家都說:現在沒人看武俠劇,我也壓力很大。一是領導覺得不是主流文化,普遍認為:“什么少林功夫,不就是武打片嘛。”第二市場又出于下坡趨勢。
但我始終覺得中國功夫是有魅力的,否則怎么會在國外傳播得那么厲害?在中國會有這么多人練?光少林寺武校就有30多萬學生。包括好萊塢電影,也在融入中國功夫。《黑客帝國》三部曲打得那么精彩,全是袁和平設計的武術動作。但因為國內不重視,我們的功夫,只能作為一種元素,成就人家的品牌。這就是我為什么后面總說,一定要把功夫劇和武打片分開,跟武俠劇分開,有一種使命感。
新民周刊:你覺得武俠劇的問題出在哪里?
都曉:功夫劇在香港發展有三條線,一條是成龍、洪金寶、元彪這條線,本身是京劇武生出來的。他們身手很好,但是沒套路。所以成龍是真動作,但不是真功夫,雖然后來雜糅了一些套路,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但跟武術還是有距離的。
李小龍是有真功夫的,跟葉問學的詠春拳,發展出截拳道。劉家良、袁和平是以從前做拳師,或者家里開武館的,也是打起來有套路。
但后來有一批人,花架子越來越多,就把功夫片拍濫了。現在國外一看中國的武俠劇,就認為中國功夫都是假的,慢慢把中國功夫劇當做動作片來看,這樣就毀掉了中國武術的名聲,變成了純娛樂。
我們從小想練的是功夫,不是武俠。我覺得中國功夫劇已經到了要自立門戶的時候,把它從武俠劇里搶救出來,要不然就把功夫給毀了。而且既然武術是比較好的手段,我們為什么不利用它,向國外宣傳。我當時就非常肯定,這部劇出來以后,肯定在國際上會有影響。
不會武功,怎么指導真功夫?
新民周刊:你在三部《少林寺傳奇》上一共投了一個億,其中花錢最多的是哪一塊?
都曉:四分之一都投在了打戲上。武俠可以拍10秒,做1分鐘。我既然打著少林寺真功夫的牌子,要恢復武術作為功夫劇的核心基礎,必須真勢、真拳,各方面比他們下的功夫都要大,用的人也多。一般一部武俠劇,投2000萬,打戲成本不超過100萬,我至少要拿出600萬。不這樣做,效果就說不過去。
新民周刊:你的這個思路,作為武術指導的程小東是不是能接受?以往他拍的都是《英雄》、《十面埋伏》這種典型的武俠片,以飛來飛去見長。
都曉:當時定的基調是一定要用一線有名的武術指導。最初定的是袁和平,劉家良,都是打得比較實的。但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年紀比較大了,拍電影還行,拍電視劇做不動了,而且我的劇打的量都很大。當時程小東正好在北京拍《滿城盡帶黃金甲》。在亮馬河邊的茶餐廳,他問我:“導演,你要什么?”我說:“要少林寺,不要武俠。”他說:“少林寺也可以浪漫的。”我說那是兩回事。少林寺的浪漫,肯定不是《英雄》的浪漫。他就講:“我明白了,你就是要真的。但演員都不能打啊。”我說我給你的是十六個全國武術冠軍。
其實程小東早就想拍少林寺了,拍真的少林功夫,只是一直沒有機會。他問我還有什么要求,我直言以告:最擔心的就是你是武俠劇的導演。我要的一定有武術套路,說得清為什么進攻,為什么失敗。而且要給往死里打,拳拳到肉,讓觀眾像看一場拳擊,不能飄來飄去。
我的第二個問題:不能接活給弟子干。
他說我自己干可以,但是我是很貴的。我說行,但這三個月,你必須按照我們要求打。
新民周刊:程小東不會武功,怎么指導真功夫?
都曉:為什么我們倆合作這么愉快?在這之前有一件事情讓我對他很放心。我們第二次見面的時候,我把整體構思都講了。他當時讓助手把我的演員集中到一起,把他們最拿手的功夫都拍下來,在家認認真真都看了一遍,琢磨每個演員的招式有什么特點。他也是第一次認識,這是虎拳,這是少林小洪拳,到現場之后成了半個專家。
他又找了兩個練少林拳的助手,比如虎拳,就讓兩個人就照著打一套。他非常聰明,一看就知道了,這個可以去掉,那個可以擴展。
新民周刊:你們鬧過矛盾嗎?
都曉:矛盾很多。他和徒弟拍完黃秋生的戲之后,我拿出了3頁稿紙18條意見。這個套路沒交代清楚;這個是動作,而不是功夫……一條一條全分析完之后,程小東半天沒說話。
第二天早上,出門的時候他在門口等著我,說:“導演,我理解你的意圖了,你今天看吧。”這句話讓我很感動,他像小孩一樣單純。并沒有憋著氣不理你了。打完收工,過去一看,我要的就是這個!只是打得還不夠實。他說:“還怎么實,再打就把人打死了。導演你好殘忍。”我跟他說:“以不打死人、不打殘人為底線。我給你找的不是演員,都是學功夫的,他們會挨打,你怕什么!”
人們的精神需要出路
新民周刊:第一部出來之后反響如何?
都曉:第一部出來以后面臨兩個問題。一是武俠劇的市場不景氣,大家拼命從高科技上去找亮點,沒人往回走從中國武術上去找出路。覺得科技都發展到今天了,你還用這種打,都覺得擔心。第二,我里面打的場面很多,很多人覺得打得太長了、太講究了。打有什么好看的?看樣片的時候,4家電視臺有3家否了。
但當時我想,我從小喜歡的這種武術,絕對不是飛來飛去的。大家都會說,你有真功夫拿出來亮亮,絕對不會說,你表演一下看看。這種帶有挑戰性的東西,我就不信老百姓不喜歡。真看電腦特技,還不如去電影院看美國大片,我們的電腦科技那么臭。
后來我就擴大了30家來看片,當時有8家簽了合同。
出后效果那么好,把大家都震驚了。福建臺第一家播,收視率達到5年來最高。廣東臺最高達到56%的收視份額。北京臺三頻道播出的時候,也達到了兩年來的收視最高峰。
這就說明了小眾和大眾的審美趣味差異。新事物出來有一個接受過程。電視劇市場當時處于一個迷茫,武俠片沒人看了,怎么做?都在找出路,每個人的判斷不一樣。所以我們的片子普遍存在一個問題,審片的時候打分不高,播出的時候打分高。包括第三部出來還是面臨這個問題。播出是山東臺收視率排名第一,應該是至少打90分的片子。但審片的時候只打了70分。
新民周刊:你覺得收視率為什么會那么高?契合了怎樣的時代需要和民眾心理?
都曉:這說明功夫文化有非常好的群眾基礎。只是我們沒有重視它。放著這么好的不做,去做武俠片。而且它的文化鋪墊也非常到位,大家看武術不是只看打。
雖然有些主流文化不承認,但功夫劇在當下對人精神上的鼓勵,遠遠大于我們現存的任何文化形式。人們的精神需要出路。就像美國人都希望城市里出現一個蜘蛛俠,把國家機器無法作為的不公平消滅掉。
在功夫劇里,永遠是弱者戰勝強者、善良戰勝丑惡、正義戰勝邪惡。這種概念正是好萊塢成功的模式。而且功夫劇滿足了在和平年代很多人的英雄主義思想。承其童年的夢想,加上比較輕松的形式,娛樂性也很強。
其實老百姓在任何時候,都希望有些更真實的東西,對那些糊糊弄弄的反感是發自內心的。就這個概念本身,足以讓老百姓心理上得到一種親近感。我這一次感觸最深的就是,電視劇一定要有誠意在里面。你只要真誠去做了,而且能從中看出真智慧,而不是偽智慧,老百姓就會支持。
這也是一種對技術包裝的文化的批判。大家并不是排斥技術包裝,而是排斥被技術包裝的良心。美國大片,可以而把一只狗拍得特有人情味,把一個機器人拍得讓人想哭,但中國能把人拍得跟機器似的。
新民周刊:為什么一開始就盯著國外市場?
都曉:我們既要賺錢,還要有一些文化的目的。現在做動作劇、功夫劇,沒人想做一種文化,都是當娛樂做。但我們一定要打出以我們為代表的影視劇里的真功夫的氣質。表面娛樂、勵志,內里一定要將功夫文化在國內打造成一種文化態勢。但不往國際上走,功夫劇在國內就不會被認可。必須墻外開花了,內部才承認。我的立意就是要借娛樂的手段,把一種文化往外推。拍完之后,所有的電視節我都去,徹底考察它在國際社會上的價值何在,做了很多交流。現在因為我們的努力,大家越來越重視到功夫劇的重要性,否則給外國大使館送禮不會送《少林寺傳奇》。馬上他們有一個領導要到古巴去訪問,送的中國作品,一部是《長征》,另一部還是《少林寺傳奇》。你不得不承認功夫文化正在從臺下走向臺上,從后臺走向前臺。
這面旗幟只有舉起來了,才有更大的影響力。我們已經確立了以《紅蜘蛛》為代表的一種類型劇。還可以立出以真功夫為代表的類型劇,這個根扎在中國文化的深處。我們前段時間還專門建立了中國功夫劇研究會,就是要把功夫劇和武俠劇徹底分開,它背后文化的東西,還遠沒有被發掘。
做什么事,都要真功夫!
新民周刊:你自己兒時的武學夢是怎樣的?
都曉:功夫始終是每一個男孩子心目中的一個夢,吸引人的是里邊的英雄主義、建功立業的豪氣。我是洛陽人,一說功夫興奮得不得了。看完電影《少林寺》,往那里跑了好幾趟,結果沒看到一個練功的,大失所望。后來當了體育記者,就把重心放在武術報道上。現在少林寺開武校的,很多都是當初我的朋友。當導演之后終于有了這么一個機會,在創作上暢快一把,盡量促成功夫文化更成形、更成熟。
新民周刊:聽說你在練太極。你覺得《少林寺傳奇》能像《大長今》帶動學醫熱、韓餐熱一樣,帶起學武熱嗎?
都曉:我是因為拍《少林寺傳奇》,才調動起來了練武的熱情。少林功夫沒法練了,老胳膊老腿的,還是練太極比較適合。我原來當體育記者的時候,那么好的條件,陳氏太極掌門人陳小旺讓我跟他學,我都沒學。他兩個弟子,當時經常一起玩,現在已經成了全國大師。我跟他們原本該是師兄弟的,現在變成師徒輩。
我估計這部劇能帶起來很大的學武熱情。第一部熱播的時候,本來少林寺那邊的武校,招生已經往下落了,結果那年很多小孩看完《少林寺傳奇》,覺得還可以練功,激起了好多孩子的夢想。
其實每個人的夢想不一定都是練武。它傳達的就是一種精神,做什么事,都要真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