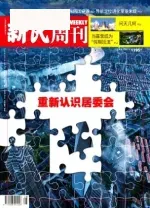以“白宮書記案”丈量國家的法治
劉洪波
一般的腐敗案只是貪賄而已,“白宮書記案”還調用司法機器對公民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予以直接的、體系性的損害。國家法律和法律機關以此而成為實現官員個人意志的工具。
安徽阜陽市潁泉區“白宮書記案”曾經轟動一時,近傳已經結案,舉報人李國福家屬獲賠88萬元。
2007年,因舉報潁泉區委書記張治安修建豪華辦公大樓“白宮”,李國福、其妻袁愛平、女婿張俊豪均被拘捕。2008年,李國福死在監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2010年2月,張治安以受賄罪、報復陷害罪被判死緩。2010年10月,潁泉區反貪局局長鄭濤、副局長徐光因參與打擊報復被處黨內嚴重警告,調離檢察院。
這個案件可以丈量現實社會與“法治社會”的距離。李國福因舉報一個區委書記,身死冤獄,舉家受難,損失無以彌補。再大的賠償,無法使死者復生;遭受非法拘捕的經驗,也不是錢可以換算。舉報者被權力報復,系獄而死;舉報者家屬也遭到權力的報復,復活了“連坐”。還有羅織罪名,榜掠求證,加上舉報者“放過家人”的哀告和屈服,以及雖屈服而不得免的苦難。張治安的治理,若以黑暗來形容,難道有什么夸張?
前不久,曾任河北省委書記的程維高去世。這名2003年被開除黨籍的高官,曾使舉報人郭光允遭受8年迫害。相比于郭光允,李國福的舉報,事實更加明顯(白宮人人眼目可見),官員層級更低,而付出的代價更大。
我當然不以為,這樣兩件事情的比較,可以判斷法治的退步,但至少可以表明,在真實的社會生活之中,法治進步的水平到底如何。
摒棄人治,實行法治,在當代中國成為歷史性的選擇,已有30多年。早在十年動亂結束未幾,“權力過分集中”,“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家長式的人物”“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系”,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乃至“君臣父子關系或幫派關系”,以及一個人隨意破壞法律,“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等等思考,就已展開。至上世紀90年代,建設法治國家已經載諸憲法。
像張治安這樣的區委書記,在權力序列里不可謂高,但其“違法能量”已是足夠強大。行賄受賄,鋪張靡費,無視治域貧困現實,窮奢極欲建豪華官衙,這已是權力對民眾的背叛,而張治安更進一步,對舉報者大治其罪,一意之立,法律失陷,黑獄頓成,號哭一片。如此權力,難道不可以稱之為勢焰熏天?
其實,說張治安對舉報者“大治其罪”,并不確切。按照法律,張治安并不執掌司法權力;而給李國福治罪者,則是潁泉區司法機關。作為區委書記,張治安合乎制度地擁有領導權力,這權力經張治安的使用,可以說類同于口出法隨的君主之權。在其治域內,國家法律隨其意志而解釋,司法機器隨其旨意而行止。
盡管任何腐敗案件中,我們都能夠看到權力制約的缺乏,看到“尤其一把手權力缺乏約束”,但“白宮書記案”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不受約束的權力顯示出的“全面專制”樣式。一般的腐敗案只是貪賄而已,“白宮書記案”還調用司法機器對公民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予以直接的、體系性的損害。國家法律和法律機關以此而成為實現官員個人意志的工具。
在“白宮書記案”中,賠償單位還有當地司法機關。然而,這些賠償單位,未聞將受到何種究責;參與制造冤獄的,不過警告和調離。違法所付的成本,是如此低廉。這種處理,與其說是樹立起對法律的信仰,不如說是堅固一些人違法枉法以承權力之意的信念。
張治安無疑是李國福死亡事件的首惡,但相關的機構、萬民之視聽、人心之指向,都不足以使首惡受到阻礙,不足以使協從者退卻,這足以表明在真正的法治國家“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這里仍然有著不斷發生的制度基礎。從權力運行的程序來說,張治安以區委書記之職,全面領導潁泉地方事務,“組織”、“法律”、“人民”等等符號,因區委書記這一職務而具體化,再具體到擔當職務的張治安個人。個人專斷,個人擅權、權力集中、家長制等等,在張治安身上體現無遺。這不是張治安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他掌握的權力從制度上具有發展為“小皇帝”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