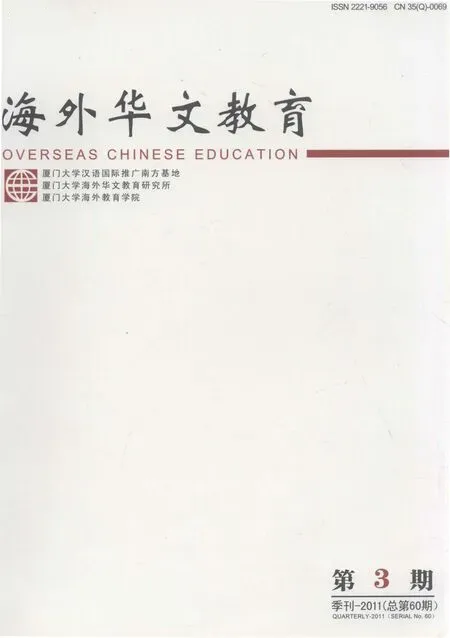教師話語中的文化:新加坡漢語課堂語篇分析
楊延寧
(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新加坡)
一、前 言
新加坡的漢語教學一直被賦予文化傳承的重任,該國各時期的漢語教學大綱都明確地將文化傳承作為教學的重要目的之一。隨著漢語教學改革的呼聲日高,逐漸出現了要刪減甚至剝離漢語教學中文化內容的聲音。由此引發的爭論也開始見諸于當地的各大媒體。這些爭論往往參雜太多的感情因素,反倒忽略了實際的教學情況。本文的寫作目的在于依據新加坡漢語教學的實際情況對這一問題進行澄清。
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是課堂語篇分析,研究的對象是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所形成的教師話語。語篇分析的方法應用范圍極其廣泛,依據的理論也各有不同。為了實現有關的研究目的,本文提出了三維雙階的分析模式,所依據的理論是由韓禮德(Halliday 1994)所創立的功能語法。本文認為在教學過程中形成的語篇可以從三個維度進行描述,即語篇范圍、語篇基調和語篇模式。這三個維度的描述分別體現了課堂活動的的主題、課堂上的師生互動關系和課堂對話的語體色彩。但是這三個維度的描述揭示的是課堂語篇比較宏觀的特征,尚需微觀層面的分析與之相配合。由此,本文也提出三個緯度在小句層的分析對象,搭建出完整的課堂語篇三維雙階分析模式。
以上述分析模式為基礎,本文對八節新加坡中、小學漢語課上形成的教師話語進行了量化分析。分析的結果表明,目前新加坡的漢語教師已較少辟出專門的時間講解文化知識。但是,文化對當地漢語教學的影響力依舊強大,主要表現在教學過程中背景知識的選擇、課堂上中華交際文化的傳承和傳統教學方法的延續。綜合這些特點,本文認為新加坡漢語課堂上的文化因素多以隱性方式存在,并嘗試對這一存在形式產生的內在原因進行分析。
二、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漢語課堂語篇中的教師話語
本研究所使用的所有語篇均來自于實際課堂觀察,分為中學和小學兩個部分。小學部分的語篇取自于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的一個大型研究項目。為了解新加坡小學漢語教學的真實情況,該項目在新加坡的五大學區內各選了兩所小學,每所小學任意選取兩節漢語課進行課堂觀察和錄像。本研究選用其中的四節漢語課,分別涉及四所小學。中學部分的語篇來自于作者在兩所中學中進行的課堂觀察和記錄,同樣包括四節漢語課。有關的中小學漢語課都進行了全程錄音,并依據錄音資料整理出完整的課堂記錄。
在獲取了相關的聲音及文字資料后,如何有效地對其整理和分析以獲得研究所需的課堂語篇就顯得尤為重要。本研究并沒有按傳統方式將一節課中所有的師生對話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描述,而是依據不同的課堂活動類型將所有師生表述切分為更小的語篇單位。舉例而言,如果一節課中有15個不同類型的課堂活動,就會相應地生成15個課堂語篇。另一方面,本文關注的是課堂語篇中的教師話語,學生的表達則不在研究范圍之內。原因在于本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文化內容如何在教師的教學過程中得以體現。本文切分一節漢語課的依據是實際教學活動的目的。基于已有的研究(楊延寧2010),作者共設定18類具有不同目的的教學活動,如表1所示:依據表1中的劃分方法,作者對八節漢語課進行了切分,共得到109個課堂語篇(小學52個,中學57個),作為本文的分析對象。所涉及語篇的長短不一,字數從205到373不等,通常由7到15個回合的師生對話構成。

表1 新加坡漢語課堂活動類型
(二)研究方法:教師話語的三維雙階分析模式
以語篇分析為基礎的研究方法在語言教學研究中應用得相當廣泛。但是已有的針對語言教學的語篇分析往往具有以下兩個突出的問題:1.分析的角度過于單一;2.分析的對象不夠具體。考慮到這兩個問題,本文提出了一個針對課堂教學實際情況的三維雙階語篇分析模式。
首先,任何一個課堂語篇都會圍繞特定的內容展開,可以稱之為語篇范圍。通過對語篇范圍的描述和界定,我們可以判斷一個語篇是否圍繞特定的主題展開。具體到本研究中,語篇范圍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特定漢語課堂語篇是否涉及文化主題。但是僅僅確定整個語篇的話語范圍是不夠的,有必要在語篇更微觀的層面進行細致分析。本文認為這種分析應該以語篇的基本構成單位,即小句為目標。一方面要確定每一個小句的主題,另一方面確定小句中新舊信息的出現順序。具體分析如例(1)所示:
(1)這些舞獅是什么顏色的?
舊信息 新信息(主題)
通過對小句(1)的分析,我們可以確定該句的主題是關于“顏色”的。同時也可以看到“舞獅”作為句子的舊信息出現,為小句的主題提供了文化背景。如果我們將大量小句分析的結果進行統計,就可以判斷整個語篇在多大程度上同文化內容相關,以及該語篇中進行了怎樣的文化背景處理。
課堂語篇由師生對話構成,自然涉及到師生之間的互動,本文稱之為語篇基調。師生之間的互動方式和互動中語言要素的選擇可以反映出一種語言特有的交際文化是否得到體現。就教師話語而言,有兩方面的選擇特別重要。首先是小句中語氣的選擇,包括陳述、疑問、祈使和感嘆四個主要類型。其次是小句中情態詞的選擇,比如“應該”、“可能”、“也許”等等。如例(2)所示:
(2)他們可能是另外的顏色,對不對?
情態詞 疑問語氣
傳統中華文化強調交際中的禮讓和謙和。了解漢語課堂語篇中語氣的選擇傾向和情態詞出現的多寡,有助于判斷傳統交際文化是否在新加坡漢語課堂得以體現。
除了課堂語篇的范圍和基調,我們還應該關注其語篇模式,即小句層面過程類型的選擇和小句的語體色彩。過程類型是系統功能語言學中的核心概念,用于描述小句中的核心動詞的及物性特征。漢語中的過程可以分為物質過程、心理過程、關系過程、存在過程、言語過程和行為過程六類。(Yang 2007)比如例句(3)和(4)分別是物質過程和關系過程。
(3)你們有沒有去過其他的國家?(物質過程)
(4)我們華人的眼睛是什么顏色?(關系過程)
不同類型的語篇中占優勢的過程類型也有所不同,比如說明性語篇中的關系過程總量會比較多,而描述性語篇中的物質過程會更占優勢。統計分析漢語課堂語篇中各類過程類型的數量分布可以揭示漢語教師的教學特征,進而了解傳統教學方式對新加坡漢語教學的影響。基于同樣目的,語篇中小句的語體色彩,主要是書面語和口語的選擇,也是本文分析的重點。綜合以上討論,本文所使用的三維雙階語篇分析法和其解釋的文化特征概括為表2。

表2 三維雙階語篇分析模式
三、新加坡漢語教學中的文化主題和文化背景
依據表2中的分析模式,作者首先對109個課堂語篇中包括的所有小句的主題和新舊信息進行了標注。統計結果表明主題屬于文化內容的小句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如表3所示。

表3 小句中的文化主題
但是,所有語篇中將文化內容作為舊信息的小句數量就要大得多。其中,小學部分達到了總量的25.3%,中學部分39.1%。對課堂錄音資料的分析也表明,新加坡的漢語教師實際上很少單獨講解文化內容,更普遍的做法是將有關內容同具體的詞、句講解相結合。比如課本中出現當地小學生比較容易混淆的親屬稱謂時,多數教師只對涉及的詞匯進行講解,不會帶入更多相關內容。講解到“節日”一詞時,教師一般都會先提到一些最為學生所熟知的傳統節日,作為進一步講解的背景知識。當有程度較好的學生提到“端午節”、“清明節”這類詞語時,教師才會給與進一步的講解。同時,大部分教師對文化內容的講解表現得相當克制。某位教師在上《過生日》一課時,偶然提到了“孝順”一詞。當她意識到學生還無法準確理解該詞的含義時,就告訴學生以后還會學到,然后迅速回到預設的教學內容。這些都表明,漢語教師并沒有將講解文化內容作為教學的主體內容之一。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接近總量三分之一的漢語課堂語篇中教師話語是以文化內容為背景展開的。比如一位教師問學生:

教師要講解的顯然是“節”的寫法,但是她將“春節”作為舊信息以便帶出“節”字。這一講解就是以文化內容為背景展開的。如果學生對“春節”毫無印象,該講解注定會失敗。重要的是這類具文化背景的講解在有關語篇中頻繁出現,而且集中在語言知識講解和漢字識讀兩類課堂活動中。由此可見,文化知識在新加坡的漢語課堂上還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只是不再成為教學的主體內容。
四、新加坡漢語教學中的交際文化
中華文化把人際關系的和諧作為理想目標。孟子講:“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也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華文化對和諧人際關系的重視對漢語教學自然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本文首先按表2所列的分析模式對教師話語中的語氣選擇進行標注,統計數據如表格4所示:

表4 教師話語中的語氣選擇
從表格4中我們可以看出,新加坡漢語教師的課堂話語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疑問語氣。陳述語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例,而祈使和感嘆語氣出現的比例就要低得多。分析結果也表明,漢語教師在進行課堂表達時往往刻意的選擇疑問語氣。比如很多通常以陳述語氣表達的意思都被轉換為疑問語氣,如例(6)所示:
(6)這個字曾經出現過,對不對?
教師在提出該問題時,其實非常確定提到的字在同一篇課文中是出現過的。但是使用疑問句后,可以增加師生之間的交流,也給學生提供了表達的機會。由此引發的師生問答可以改善實際交流環境,舒緩課堂壓力。從這一點看,漢語教師有意或無意地選擇疑問句式實際上起到了增加交流,調節師生關系的作用。如果說語氣的選擇還是漢語教師話語中比較大的特征,那么情態動詞的選擇則更能反映出教師在進行課堂互動時的微觀特征。本文對109個課堂語篇中出現的所有情態動詞和副詞進行了標注,并依據其不同功能進行了分類(Zhu 1996),數據如表格5所示:表格5中的數據首先說明,新加坡漢語教師使用最多的情態動詞和副詞同可能性和意愿性表達相關,其中可能性表達所占的比重更高。其次,我們還注意到表達必要性的情態動詞的使用頻率是最低的。我們還可以看到上述特征在小學部分的語篇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表5 教師話語中的情態選擇
課堂語篇一直是語言教學研究的重點,有關課堂上師生對話的分析相當細致全面。(McHoul 1978,Hustler and Payne 1982)有關研究發現,在課堂上教師和學生之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教師是知識的提供者,掌握對話的主動權。這些特點都決定了教師話語中的必要性陳述,即向學生發出指令的表達出現的頻率會比其它情態表達更高。但表格5中的數據卻表明,新加坡漢語教師話語中關于必要性的表達反而是最低的。對相關課堂語篇的進一步分析證明,很多帶有必要性的表達被漢語教師刻意地調整為可能性或意愿性表達,如例子(7)和(8)所示:
(7)同學們能在十分鐘內完成這個練習。
(8)大家愿不愿意來做一個小測試?
在課堂教學的大環境下,例子(7)和(8)的表達實際上是要求學生完成練習和測試,并沒有商量的余地。但是這類表達在漢語課堂上經常被教師弱化為意愿性和可能性陳述,命令的意味大大降低。
作者認為上述教師話語中的語氣及情態特征同中華文化中處理人際交往時強調委婉表達的特性密切相關。在課堂上進行相關表達時,教師并沒有對語氣和情態詞進行刻意的調整和選擇。多數強制性表達被下意識地以更加委婉的方式呈現。這些現象實際上是當地漢語教師長期形成的課堂交流習慣的一種體現。而這種交流習慣形成的根本原因則是幾代漢語教師對中華文化中人際交流原則的一貫堅持。新加坡的華文教師同其他科目教師相比,身上總是帶有一絲古樸守舊之風,為人行事更加謙和。這一特征對新加坡漢語教師的課堂表達有很大的影響。
五、新加坡漢語課堂上的教學傳統
本文對新加坡教師話語分析的最后一個方面是語篇模式,包括小句過程類型和語體特征兩個方面。對相關語篇的分析表明漢語教師話語的書面語特征非常明顯。書面語和口語可以通過計算語篇中的詞匯密度加以區分。Stubbs(1986)將詞匯密度定義為實義詞數量與總詞數之比。由于缺乏針對新加坡華語的詞匯密度的研究,作者任意選取了五千字的書面語和口語材料進行了計算,作為本研究的參考數據。針對課堂語篇中教師話語的詞匯密度計算表明,其數值更接近書面語,如表格6所示:

表6 教師話語中的詞匯密度
如表格6中的數據所示,新加坡漢語教師話語中的詞匯密度接近于當地使用的華文書面語,距口語的距離則較遠。這一特征同新加坡漢語教學使用的教材和教學方法都有關系。就教材而言,當地漢語教材是比較典型的選文式閱讀教材,比較適合書面語教學和讀寫技能的訓練。教師的教學方法也比較傾向于閱讀和寫作,對聽說的訓練則相對較少(楊延寧2011)。這些都表明,傳統的源于中國的語文教學對新加坡的漢語教學影響非常大。教師話語的書面語特征其實也是傳統教學文化影響力的一種體現。
小句過程類型的統計從另外一個角度印證了教學傳統對教師話語的影響。本研究對有關語篇的標注和分析表明,在漢語教師話語中占主導地位的是關系過程和物質過程,分別達到了總量的37.5%和25.1%,兩項相加更是超過了總量的六成。教師話語中最頻繁出現的句式是“A是B”和“A+及物動詞+B”。這其實和傳統教學法中重詞語解釋和實物描述的特征是一致的。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新加坡的漢語教學有很強的文化特性,但是該特性更多地以隱性的方式存在。漢語教師已經不再把文化內容作為教學的獨立內容,而是將其融入到具體的詞匯、句式講解中。與此類似,漢語教師不會將傳統文化中的人際關系處理作為教學內容,但是卻在教學過程中身體力行。身教勝于言傳,修讀漢語科目的學生一定會深受影響,形成類似的漢語表達習慣。至于教師話語的書面語特征和重解釋的特性同傳統教學法有密切關系。簡言之,新加坡的漢語教師不但將文化作為教學的背景知識,還在教學中傳承了中華交際文化和傳統教學文化。
六、文化特征隱性存在的內在原因
前文表明,新加坡漢語教師話語中的文化特征以隱性方式存在。我們自然要問,這一存在方式由何而起?作者認為其根本原因是新加坡漢語教學中傳統教學理念和最新教學方法的并存。
新加坡的漢語教學傳承有序,很多教學理念,百多年來一脈相承。其強大的影響力延伸到教學的每一個方面,潛移默化地制約著教師的教學行為,在教師話語中自然有所反映。比如教師話語分析所揭示的傳統教學文化的延續實際上就是長期存在的教學理念的一種體現。在本研究所涉及的八節漢語課中,可以觀察到很多實際上源于中國私塾教育的傳統教學法。其中包括:(一)學生隨教師有感情朗讀課文;(二)讀出漢字筆畫并用手指隔空比劃漢字的書寫順序;(三)教師按字詞在課文中的出現順序逐個解釋,較少顧及字詞之間的邏輯關系和學生的先備知識;(四)反復背誦課文(李國鈞,王炳照,2000)。這些傳統方法的主要特征是以教師為中心,機械重復,不注重實際教學效果的檢驗。但這并不妨礙其在課堂上的存在,傳統教學理念的強大影響力可見一斑。
本研究所揭示的教師話語中的交際文化特征同傳統教學理念一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傳統語文教學一直都將教書育人合二為一,漢語教師從來都是身兼二職。時至今日,新加坡的所有的漢語教師都要教授一門叫做“公民道德”的課程。這種教書育人的理念使得漢語教師非常重視自己和學生的言行舉止。比如,當地的學生在上漢語課前要向老師鞠躬問好,這在其他科目的課堂上是看不到的。由此可見,漢語教師對傳統交際文化的傳承同樣是傳統教學理念的體現。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教育體系在全世界居于領先地位。當地漢語教師在國立教育學院接受培訓時就已經開始接觸最新的教學理念。工作期間,也常常會受教育部委派到世界各國參觀學習,了解教育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同時,新加坡教育管理當局深感漢語教學任重道遠,一直刻意推廣最新的教學方法,以求事半功倍。其結果是,當地漢語教師在教學中不遺余力地使用最新教學方法。近二十年在語言教學領域風行的直接教學法、交際教學法、差異教學法、自主學習法等等,在八節漢語課中都有所體現。
在這種情況下,身兼雙重使命的新加坡漢語教師常常要左右兼顧。由于教育部的極力提倡,我們在漢語課上也觀察到很多最新的教學方法。與此同時,許多傳統的教學手段依舊大行其道。原因在于它們極具針對性,能夠有效地提高學生的考試成績。在有限的課堂時間里,教師要兼顧兩方面的需要,必然造成課堂節奏加快,課堂活動延續時間變短。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我們會觀察到,當地漢語教師將文化知識有節制地同具體教學內容相結合。這實際上是一種被動的、合理的選擇,是新加坡的特定教學環境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李國鈞,王炳照:《中國教育制度通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楊延寧:《從課堂實際情況看新加坡華文教學中英語的使用》,《華文教學與研究》2010年第2期。
楊延寧:《從課堂觀察結果看新加坡小學漢語教學的主要特征》,《國際漢語教學》2011年第4期。
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London:Edward Arnold,1994.
Hustler,D.and Payne,G Power in the classroom Research in Education,1982,(28):29-64.
McHoul,A.The organization of turns of formal talk in the classroom.Language in Society,1978,(7):183-213
Stubbs,M.Lexical density:A computational technique and some findings.In M.Coultard(ed.)Talking about Text.Studies Presented to David Brazil on His Retirement.Birmingham:English Language Research,University of Birmingham,1986.
Yang,Y.N.Grammatical Metaphor in Chinese.PhD Thesis.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2007.
Zhu,Y.Modality and Modulation in Chinese.In M.Berry(ed)Meaning and Form:Systemic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s.Norwood,N.J.:Ablex Pub.Corp,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