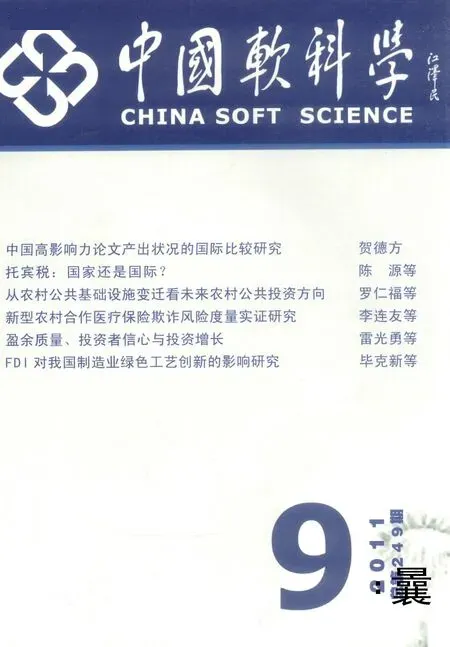我國西部生態脆弱性的評估:預控研究
尚虎平
(蘭州大學 管理學院,甘肅 蘭州730000)
一、問題的提出
2011年3月10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盈江縣發生5.8級地震,共造成25人死亡,全縣共有28.25萬人受災,此次地震又一次引起了社會對西部生態脆弱性的警覺[1]。
實際上,在剛過去的一年中,由西部生態脆弱性引致的自然災害已經愈加頻繁。青海省玉樹縣2010年4月14日晨發生兩次地震,使得2220人遇難,70 人失蹤[2]。同年 5、6 月間,重慶墊江、梁平、涪陵、彭水等12個區縣遭受大風、冰雹、暴雨災害,使89.78萬人受災。從2010年7月18日開始,長江上游地區普降暴雨,四川省廣安市渠江廣安城區段水位上漲達25.66米,這是自1847年以來廣安區發生的最大洪水災害[3]。此后,由此引發的災害逐漸擴大,按照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7月21日報告,在此次災害中全國25條河流發生了超歷史大洪水,27個省區市受災,受災人口1.13億,直接經濟損失約1422億元[4]。7月28日晚至29日,祁連山區普降大暴雨引發泥石流洪水災害,造成經濟損失3124.25萬元。時至8月,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縣突降強雨引發破壞性極強的泥石流,共造成1435人遇難,330人失蹤[5]。幾乎與此同時發生的四川震區新城特大山洪泥石流造成全省576萬人受災,因災直接經濟損失約68.9億元,汶川地震后重建即將交付的映秀新城被淹,面臨二次重建[6]。此后的時間里,西部的生態災害仍頻。上溯幾年,西部生態脆弱性引發的生態災難更觸目驚心:西南地區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使得11874.2千公頃農作物受災,因災直接經濟損失1516.5億元;汶川大地震使得四川、甘肅、陜西、重慶等省(市、區)417個縣受災,受災人口4625.6萬人,因災死亡69227人,失蹤17923人,直接經濟損失達8523.09億元;新疆大部分地區持續高溫使1867.6萬公頃天然草場嚴重受旱,糧食產區大面積受災,一些地方幾乎絕收;攀枝花——會理地震導致川滇兩省126.9萬人受災,直接經濟損失36.2億元;寧夏嚴重干旱致98.7萬人受災,多處甚至絕收;西藏發生強降雪,10萬余人受災[7],等等。
目前來看,由西部生態脆弱性引發的各種災害仍然有繼續蔓延,甚至向其它地區擴大的趨勢,而從過去幾年政府的應對措施來看,其效果仍然不甚理想。各地,甚至中央政府也以“救火為主”,有效的預防手段尚未出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人民網的“環境頻道”在2011年1月21日專門邀請了相關領域的專家進行探討,但仍然未找到行之有效的措施。從筆者2011年1月6日分別在SPRINGER和中國知網(CNKI)以“China’s(Chinese western ecology)vulnerability”和“西部生態脆”(由于國內將vulnerability翻譯成“脆弱”、“脆性”,這樣可以避免漏掉資料)檢索到的169篇國際文獻和124篇國內文獻的分析來看①之所以選SPRINGER數據庫是因為筆者考慮到SCI、SSCI、EI數據庫的學科傾向性過于明顯,對于跨學科研究涉及較少,而SPRINGER既包括理學、工學,也包括人文學科、社會科學;既包括期刊文章,也包含書本章節,更有利于從多學科、跨學科的角度來了解目前的研究現狀。,在國際范圍內,Wang et al.(2007)、Bennett(2008)等對我國西部生態脆性修復項目進行了梳理[8-9],Li et al.(2010)、Zhao(2002)等對生態破碎度做了考察[10-11],Fiona(2010)、Liu et al.(2009)等對生態植被完整性進行了研究[12-13],New和Xie(2008)、Jim與Yang(2006)等對三峽項目對生態脆弱性的影響進行了預測[14-15],Tilt(2008)、Squires et al.(2010)等對西部經濟社會發展對生態脆性的促動和生態脆性宏觀管理進行了探討[16-17];在國內文獻中,譚秀娟、鄭欽玉(2009)、張穎、王萬茂(2004)等對我國西部生態足跡進行了計量[18-19],張秀明(2009)、荀麗麗、包智明(2007)等對政府應對生態脆弱性的各種生態補償進行了探索[20-21],任保平、陳丹丹(2007)、董鎖成(2005)等對西部大開發中的生態脆弱性進行了研究[22-23],周永娟、王效科、歐陽志(2009)、高鴻雁(2010)等對西部生態環境總體現狀進行了初步探索[24-25]。總體而言,目前國際、國內對于以我國西部生態脆弱性評估來預防和控制生態危機、生態脆性的研究還是一個盲點,至少是一個很少被觸及的研究領域。然而,正如管理學家Magretta(1999)所指出的,“不能評估就無法管理”[26],由于對西部生態脆弱性評估,尤其及時評估的不足導致了以政府為主的公共管理主體不能有效應對愈來愈頻繁的西部生態災害問題。實際上,從評估學角度來看,所有評估都具有預防控制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很有必要以評估的方式來為預防和控制西部生態脆弱性的擴大、脆弱性誘發的生態危機擴大提供客觀的決策數據、決策信息。
二、我國西部生態脆弱性的發生與應對機理
盡管由加拿大統計學家Rapport、Friend、Costanza等(1979;1998)提出[27-28],因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而發揚光大的PSR(Pressure-State-Response)生態脆弱性發生、響應機理模型有著廣泛的影響力[29],但隨著生態脆性復雜性的提升,PSR模型逐漸不能應付越來越多由生態脆弱性引發的生態危機了。筆者收集了汶川大地震、祁連山泥石流、廣安市超級大暴雨、新疆創歷史記錄的干旱、西南低溫冰雪、攀枝花-會理地震、西藏強降雪等99例我國西部生態脆弱性從發生到應對(控制)結束的案例,通過統計分析開發出了一個生態脆弱性從壓力、狀態到響應的一般模式,如圖1,它是對PSR模型面向我國西部的本土化改進①案例收集、統計分析、模型構建過程筆者另文交代,此處限于篇幅所限略去詳細論證過程。。
筆者構建的生態脆性發生、響應模型中,由地下水的超采、樹木過度砍伐、人口密度激增、可耕地下降、森林覆蓋面積減少、泥石流頻發等“問題”逐漸積累形成了生態“壓力”。壓力集聚之后便誘發了生態“脆弱性狀態出現”,此時的“脆弱性狀態”對于政府為主的應對主體來說是一個黑箱,究竟如何應對此時的脆性狀態,所有應對主體都缺乏脆性的確切信息,如果此時應對,往往是盲人摸象,不能對癥下藥。為了了解脆性弱狀態的真實情況,使“黑箱”變為“白箱”,需要對脆性狀態進行評估,在評估過程中需要設計出科學的評估準則、篩選出科學的評估指標體系、選擇合適的證據數據(Evidence Data),進而實施評估。實際上,評估的過程只是使“黑箱”去黑化的過程,因此它更多地屬于“灰箱”,因為一些脆性狀態搞清楚了,還有一些脆性狀態并不清晰,在評估實施產生評估結果之后,整個脆性狀態才趨于明朗,出現了“白箱”——了解了脆性究竟由何種原因引起,脆性的嚴重程度如何,究竟如何有針對性地應對。在變成白箱之后,就需要采取警察應對警情式的應對,圖中用紅色表示,代表應對的迫切性與及時性,它包含了生態脆性危機應對的因素在里面。在以政府為主的應對主體按照脆性評估結果有針對性的響應之后,生態脆性便趨于緩和甚至解決,于是出現了人們期望的健康狀態,這就是模型中綠色的含義。

圖1 我國西部生態脆弱性發生、響應的機理
按照我們構建的模型來看,生態脆弱性的解決必須關注4方面問題:第一,把握好生態問題從積累、形成壓力到集聚的過程;第二,對脆弱性狀態出現的可能性的預判,預測脆性狀態可能的程度并力爭進行前饋式干預;第三,通過對脆弱性狀態評估標準設計、評估指標篩選、證據數據選擇,實施脆性狀態評估,了解目前脆性的種類、強度、誘因;第四,依據評估的結果由政府為主吸收其它主體參與對生態脆性進行危機管理、日常應對,從而將生態脆性消弭于無形。在這4者之中,最關鍵的是生態脆性評估環節,因為只有通過評估,社會、政府與其它干預主體才能了解脆性的具體狀態、強度、誘因,才能有的放矢的進行干預與危機管理,如圖1所示,所有針對性的干預環節都依賴于評估結果的指導,而評估之前的前饋式預防干預則屬于盲人摸象式的干預,盡管我們很歡迎此類干預,但它畢竟缺乏可靠性,充滿了盲動性,真正有效的干預還是在獲得評估結果之后有針對性的反饋式干預。
三、我國西部生態脆弱性評估預控的主要內容
與解決生態脆性的4個環節相適應,要解決我國西部生態脆性頻發問題,就需要針對這些方面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而從我們上文總結的國際、國內的研究現狀來看,目前對第一、第二、第四環節的研究較多,但對第三個環節,即通過對脆弱性狀態評估標準設計、評估指標篩選、證據數據選擇,實施脆性狀態評估,了解目前脆性的種類、強度、誘因的研究還非常缺乏,這使得幾乎所有研究不能觸碰到西部生態脆性的內核,不能提供生態脆性的強度數據、變化趨勢數據、類型學數據、誘因數據等等,使得脆性發生前的預防式應對、脆性發生過程中及時干預、脆性發生后反饋控制式干預均不能做到有的放矢。為了解決這些不足,筆者認為在進一步的研究中,應重點加強對于我國西部生態脆弱性評估的研究,通過提升評估研究的質量,我們最終可以實現用科學的評估結果來預防、控制西部生態脆性的目標,這實質上是一種評估預控的出路。
具體而言,評估預控的實現過程為:西部生態脆弱性評價的數據源確定與數據庫、數據集市、數據倉庫構建→西部生態脆弱性評估指標體系聚類挖掘與賦權→西部生態脆弱性評估實施→西部生態脆性與地方政府績效的協同度評估→將結果返回到西部生態脆性數據倉庫,構成“脆性結果集市”、“協同結果集市”→挖掘結果與影響因素的關系→政府應對策略探索,具體環節與流程如圖2所示。
(一)西部生態脆弱性評價的數據源確定與數據庫、數據集市、數據倉庫構建
首先,明確預控評估的操作性范圍的“西部”是采用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中確定的西南五省區市、西北五省區和內蒙古、廣西以及湖南的湘西、湖北的恩施兩個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組成,即“10+2+2”,也就是“泛西部”的范圍,這些地區幅員面積約約占全國總面積的71%,總人口約全國總人口的29%。
其次,梳理與這些地區相關的生態脆弱性數據庫、信息系統理論,尋求整合 GIS、EIS、GOOGLEEARTH等不同數據庫的合理方式。
第三,通過清理、清洗與西部生態脆性密切相關的遙感數據(RS)、地理信息系統(GIS)、全球定位數據(GPS)、GOOGLEEARTH、環境模擬系統(EIS),并收集各種統計年鑒、環境年鑒、氣候年鑒、地質數據庫、生態足跡等數據,結合實地調查獲得的人民對于生態的反響、政府對于生態的反應、社會對于生態的態度等數據,經過ETL(抽取、轉換、加載)處理,輸入MS SQL SERVER、ORACAL等數據庫、數據挖掘軟件,構建出西部生態脆性數據庫,并利用這些軟件的數據倉庫構建功能,構建出“指標數據集市”、“生態脆性數據集市”,然后利用自底向上模式,將數據集市鏈接為面向“脆弱性”主題的數據倉庫。另外,在我們評估獲得結果之后,還要在數據倉庫中增添“脆性結果集市”、“脆性與政府績效協同結果集市”。

圖2 西部生態脆弱性預控評估的內容與過程
(二)西部生態脆性評估指標體系聚類挖掘
本質上來說,政府績效評估指標設計是個逐層賦權聚類問題。研究者或者實踐者一般都需要在脆弱性現象與時間組成的坐標中選擇顯性、半顯性、隱性的生態脆弱性現象、伴生現象等并對其進行逐層聚類,并將聚類產生的代表(指標)用某種屬性名詞概括為指標名稱(圖3)。在生態脆性估指標的設計過程中,可以將脆弱性的整體情況依據顯性、半顯性、隱性的現象、伴生現象(圖3中的散點)聚類為某幾個一級指標來考察,如圖中的a1、b1、c1、d1、e1,然后對其賦權。所有一級指標的權重之和為1,意味著通過聚類,將生態脆弱性的所有需要考核的方面抽象、約簡為了5個方面,并以其代表脆弱性的所有方面,對它的評價大致等同于對整個生態脆弱性的總體評價。在一級聚類之后,根據脆弱性評估所需要的精確度,還會繼續在一級指標內繼續進行二級、三級,甚至有的評估需要聚類到四級、五級指標,所有級別的指標都需要在一級指標賦權作為總和的情況下,逐級分解賦權。可以說,分級聚類沒有盡頭,但現實一般只需要聚類到三級指標即可,圖3也只標示到二、三級指標,即 a2、b2……;a3、b3……。

圖2 生態脆弱性評估指標分層賦權聚類原理
在我國西部脆弱性評估指標的聚類中,首先需要聚類出指標草集,也就是指標的“草稿”,具體可以使用神經網絡、決策樹等聚類挖掘方式,這是一個比較粗放的聚類過程。由于“草集”過于粗放,還存在著“噪音”和“過擬合”問題,需要進一步的正則化,具體可以采取FP-TREE、APPRIOR等關聯規則方式,將毫無關聯的“噪音”指標消解掉。
消解掉“噪音”后的指標僅僅是聚類產生的指標集合,還不是規范的指標體系,因為它還缺乏權重,需要進一步賦權。筆者認為,在所有賦權方法中,熵值法不需要對數據的分布形態進行任何假定,這正好符合我國西部生態脆弱性評估指標賦權中在各類異質性數據中賦予生態脆弱性指標權重的需要,可以彌補數據挖掘賦權的不足。需要強調的是,利用信息熵賦權的只是三級指標,二級指標、一級指標的權值能夠按照“分層聚類”的結果自動加和出來。具體過程為:
其次,設有m個測度對象、n項測度指標,形成指標數據矩陣 I=(iαβ)m×n,對于某項指標 iα,指標iαβ的差距越大,該指標提供的信息量越大,其在綜合測度中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相應的信息熵越小,權重越大;反之,該指標的權重越小;如果該項指標的指標值全部相等,則該指標在綜合測度中不起作用。接著,將 iαβ轉化為比重形式的 ραβ,如式(1),

然后定義第β個指標的熵為式(2),

最后,定義第β個指標的熵權wδβ為式(3),

其中 wδβ∈[0,1],且經過這3 個階段,指標集中的三級指標就具有了權重。
(三)西部生態脆弱性評估實施
在指標體系篩選、賦權完成之后,便可以利用篩選出的指標體系依據脆弱性評估的一般模型進行評估。實際上,日常人們所談論的“生態脆弱性”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它具體包括單項生態脆弱性,比如水土流失、林木毀壞、干旱等;也包括總體生態脆弱性,也就是一定時期內由多種單向生態脆弱性綜合引發的生態脆弱性。在我國西部生態脆弱性評估中,必須包括這兩方面內容。當然,作為預控性質的評估,還有一個關鍵的環節,即評估生態脆弱性的變動趨勢。
1.單項生態脆弱性評估。也就是在應用開發出的指標進行評估的過程中,對每一個指標引發的脆性都進行判別,而非與其它類的評估一樣只著眼于總體評價。因為任何一項單項生態脆性都可能引發生態危機,如舟曲泥石流、云南大旱、玉樹地震等單項生態脆性都已經構成了生態危機,這時候生態脆弱性已經超過了警戒值,到了非介入不可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整體脆弱性評估暫時讓位于單項生態危機,此時的評價模型如式(4)所示。由于特定指標i的脆性值達到了危機標準值(危機標準值本研究按照國際生態脆性標準、我國西部脆性歷史數據確定),此時脆性值V便可以簡約等于此項指標的脆性值vi,它代表了單項生態危機的到來,需要政府及時介入,這也是進行生態危機管理的決策依據。

2.一定周期內的總體生態脆弱性評價。單項指標引發的生態危機畢竟不是生態脆弱性存在的常態,更普遍的情況是脆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卻未引發危機,對于這種情況的把握與應對需要每隔一段周期(一般為一年)進行一次綜合評估,這需要應用指標體系在每年度末進行綜合評價,其一般評價模型如式(5)所示,

其中,qi為各指標的初始化值,wi為各指標的權重。是生態良好度(非脆弱性)值,它是一個標準化比值且 0≤表示各指標綜合評價后獲得的脆弱性數據占極端脆弱性和的比例,最理想的生態情況是已評價出的脆弱性情況與所有極端脆弱性情況之和相等,即其值為1,代表所有的脆性都已發生,但卻未引發危機,這是最良好的生態環境。然而,這種理想情況一般難于發生,于是我們就需要評價脆弱性度,它是良好度與理想度1的差的絕對值,這就是一定周期內的生態總體脆弱度。
3.生態脆弱性變化趨勢評估。這是對一定時期內特定范圍內生態脆弱性變動趨勢的測評,其評估模型如式(6),

其中Vc為脆弱性變化度,vt0為特定地區評價初始期的生態脆弱性值,vtn為該地區評價截止期生態脆性值,T為變化的時間間隔。
所有以上的生態脆弱性評估都可以利用篩選出的指標體系,立足于整合出的數據庫中的數據,必要時實地調查的數據對西部12省區與兩個自治州進行生態脆弱性評價,評價的范圍包括所有這些省區市的地級區劃單位(按照2009年國家統計年鑒,共有153個)。
(四)西部生態脆弱性與地方政府績效的協同度評估
評估生態脆弱性的目的在于提高政府為主的其他管理主體及時應對生態脆弱性的能力,改善生態管理水平。然而政府應對生態脆弱性的一個基本價值前提在于其將生態作為其績效的有機組成部分,將消弭生態脆弱性與增加地區GDP一樣看待,從而在追求績效改善的同時帶來生態環境的改善,這是一種基于生態的績效觀(政績觀)[30]。生態改善與政府績效的同趨性就是生態脆弱性與地方政府績效的協同度問題,對其評估可以把握政府在推進工作的同時,將生態改善置于何種位置。筆者認為,預控評估的是政府綜合性績效(整體績效)與生態脆弱性的協同度問題,之所以不選擇評估生態對口管理職能部門績效與生態脆弱性的協同性進行評估,是因為在很大程度上,特定層級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在目前的政府預算體制、管理體制下,只是該級政府實現其關鍵績效目標的工具,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各地政府圍了GDP的提升,將招商引資的指標下放到每個職能部門,甚至婦聯、殘聯都有任務。鑒于此,我們認為生態歸口管理職能部門的生態治理績效完全取決于所屬的地方政府對改善生態所持的基本價值取向,如果它認為重要,可以在預算、人事、執行上提供支持,否則就可能使應對流于形式。地方政府應對生態脆弱性的基本價值觀可以從其績效與生態脆弱性的協同度評估中管窺一斑。政府績效與生態協同度評估可以采用協調度耦合模型,如式(7)、(8):
設正數i1,i2,…,im為評估生態脆弱性的m個指標;設正數p1,p2,…,pn為評價本地方政府績效評估的n個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則有式(7),

(7)為特定階段總體生態脆弱性評價函數和地方政府整體績效評估函數。式中,,αj、βj為相應于ij的上下限值,p'i按照類似方法定義。這樣便有了地方政府整體績效與生態脆弱性的耦合度(C)的評估模型,即式(8),

顯然,0≤C≤1,C=1時,耦合度最大,C=0 時耦合度最小。在用此模型評估時,耦合度越大,則說明政府獲得績效的過程中對于生態脆弱性的促進越大。由于生態脆弱性是生態的非良性狀態,耦合度大則說明政府獲得績效的過程中損壞了生態,加劇了生態惡化。
在評價地方政府績效時,可以開發一套指標體系,也可以采用已經開發出的各類較為科學的指標體系。我們建議,生態脆弱性與政府績效的協同評估按照每年評估一次的周期展開,評估對象也包括西部153個地級政府范圍。所有的脆弱性評估、協同評估既可以用已建好的數據庫、數據倉庫、數據集市在MS SQL、ORACAL等軟件中采用結構化語言的方式輸出結果,也可以用SPSS、STATA等統計軟件操作。
(五)政府及時預控西部生態脆弱性的策略
筆者認為,生態脆弱性應對本質上屬于公共管理問題,它需要以政府為主體,盡量吸納、引入其它主體參與生態治理,實現從政府生態管理到生態公共治理的轉變。在此過程中,政府仍然為主導,其應對策略、措施需要按照評價模型的式(4)、(5)、(6)、(8)的評價結果進行,如表1 的矩陣所示,政府在面對單項脆弱性、特定時段整體脆弱性、特定時期脆弱性變化趨勢以及脆弱性與本地政府績效協同度4種情況時,需要權變地做出合適的應對策略。此處僅列部分,具體策略需要根據特定地域、特定種類的脆弱性評價結果來確定,此處提出的策略矩陣是一個“工具箱”,可供西部地方政府來選擇使用。
應對矩陣提供的是一套類似于政府工具的策略集合[31],這些策略因脆弱性種類、評價結果的不同應該有所不同。
以單項生態脆弱性的評估與應對為例來說,比如針對由干旱引發的單項脆弱性,在評估的過程中,可以采用脆弱性評估模型(4)來對其評價,在應對的過程中,如果脆弱性評價結果顯示脆弱性程度僅為輕度狀態,“應對主體”可能只需要“本地職能”,也就是本地政府中主管生態保護的職能部門出面就行了;而如果評價結果顯示脆弱性為中度、重度,則應對主體就需要擴大,可能需要本地政府協調所有職能部門來進行應對,甚至還需要與上級政府聯動,動員社會組織如紅十字協會、青年志愿者協會、國際救援組織等共同應對。在應對融資上,做法與選擇應對主體類似,如果程度較輕,則可能只需要每年正常撥付到職能部門的公共財政預算經費就足夠應付,而如果評價結果顯示脆弱性達到了中度甚至更為嚴重,則可能需要向上級政府申請應急撥款,甚至還需要動員社會捐助,或者采用BOT、BTO、發行生態彩票等方式來進行融資。在具體應對策略、策略執行、應對績效評估、應對問責、應對及時性等選項上,也都與“應對主體”、“應對融資”的權變做法類似,根據脆弱性評估結果來相機選擇合適的工具。

表1 政府可能的應對策略矩陣(工具箱)
特定時段整體脆弱性、特定時期脆弱性變化趨勢以及脆弱性與本地政府績效協同度的應對操作,與單項生態脆弱性的應對沒有太大區別,都是依照評估結果顯示的脆弱性程度在工具箱中選取可行的工具。當然,表1的矩陣和工具箱,僅提供了最常見的參考性工具,在實際的應對中,我們還可以“制造”、“創造”、開發更多的工具,把工具箱做得更大。
四、結語與展望
我國西部生態脆弱性不是一個新話題,然而近年來因它而發生的生態危機日漸頻繁,且有向其它地域擴散的趨勢,值得社會各界的警醒。從筆者所梳理的國際、國內對于我國西部生態脆弱性研究的學術文獻來看,目前學界普遍忽視了以脆弱性評估來預防、控制我國西部生態脆弱性的研究。在筆者看來,由于學者是社會的眼睛和大腦,在學界對此不重視的情況下,社會實踐部門一般更難于提前洞悉以評估來達到生態脆弱性預控的策略。正是基于這種判斷,本研究在結合我國西部生態脆弱性實際發展了PSR模型的基礎上,探索性地提出了一套以西部生態脆弱性評估為工具的預防、控制我國西部生態脆弱性的研究設想。目前來看,盡管這些設想較為符合我國西部實際情況,但還有一些問題后續研究亟待開展:
(一)構建西部生態脆弱性評價數據庫。此類研究包括利用已有的涉及西部的GIS、GPS、GOOGLEEARTH、EIS、環境統計年鑒數據,以及調查所得的西部各地人民對于生態的情感、態度數據構建出“西部生態脆弱性”數據庫,并利用數據挖掘(DM)技術在其中挖掘生態脆弱性評估指標、利用指標評估目前生態現狀、利用關聯關系挖掘生態脆弱性與貧困、過度砍伐、過度放牧、二氧化硫排放等的關系,為進一步響應、干預打下基礎。
(二)開發科學的西部生態脆弱性評估準則。評估準則是評估的最終目標指向,有人認為是評估的價值追求[32],筆者也認可這種說法。這類研究需要廓清我們對西部生態評估采用人類功利性目的優先的準則,還是自然至上的法則;是要采用可持續發展觀點,還是采用“保障經濟增長勢頭”的準則。實際上,評估準則問題是為評估結果加“+”和“-”號的問題。
(三)設計、篩選出西部生態脆弱性評估的科學指標體系。從評估學的角度來說,指標體系是破解組織管理黑箱的鑰匙,在生態脆弱性評估中,評估指標體系也是開啟脆性狀態這個“黑屋子”的鑰匙。盡管目前我國在這方面有了一些很初級的探索,但這些探索還過于零散、應用領域過于狹窄,還沒有能夠設計、篩選出能夠真正評估西部生態脆弱性的指標體系,這需要在進一步的探索中加大力度去解決這個問題。
(四)選取科學的、有代表性的證據數據。有了評估指標體系才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究竟如何實施評估,根據評估學的一般流程來說,還需要選取脆性狀態的證據數據。一般而論,任何指標體系都有無數個證據數據,但究竟哪一個數據的信度、效度更高,則需要進行科學的選取,這也是任何一種評估都面臨的難題。從已有研究來看,目前還沒有解決此類問題的文獻,這是今后西部生態脆弱性評估研究中亟待加強的方面,否則開發出的脆性評估的指標就可能流于形式。
(五)探索有效實施評估的路徑。有效實施評估的路徑涉及評估周期的問題,也涉及評估地點的選擇問題(特別是典型評估),還涉及對生態脆弱性變動發展性的評估問題(時間序列性的評估),這些問題都需要今后加強探索。
(六)評估實施中的生態危機管理。生態脆弱性評估不同于其它領域的評估,其它類評估只要評價出總體狀況便很少去追究單個指標的極值和奇異值;生態脆弱性評估則不同,它需要特別留意單個指標比如土地沙化、地震預兆的極值和奇異值,因為它們可能預示著有突發生態脆弱性(生態危機)發生,一旦如此,則此時的整體生態脆弱性評估與應對要讓位于單項生態危機的及時應對,整體的評估可以暫時放在一邊,特定地區,甚至全國都開展單向生態危機管理。這方面的研究目前涉及的更少,甚至還沒見諸報端雜志,是今后重點突破的領域。
(七)評估結果的應用。除了單項危機應對外,生態脆弱性評估的整體結果應用是一個更為常態化的問題。生態危機畢竟不是生活的常態,我們面臨的實際情況是,西部生態脆弱性在無聲無息地加劇。但從人的角度來說,可能短期內的感觸并不深刻。這時候就需要整體生態脆弱性評估結果的幫助,指導人們如何應對常態化的脆性。比如可以根據評估結果顯示的數值,對土壤鹽堿化、空氣污濁化、過度放牧等進行應對。這是最容易被忽視,也是最應該重點研究的問題。
[1]2011年3月10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盈江縣5.8級地震震源機制[EB/OL].http://www.csi.ac.cn/manage/html/4028861611c5c2ba0111c5c558b00001/_ content/11_03/11/1299822319573.html.
[2]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EB/OL].http://www.banyuetan.org/czht/special/AnnualTheme/Aftertaste/zuileiben/101213/21646.shtml.
[3]葉卡斯.重慶強風挾雹奪29命[N].廣州日報,2010-05-07(A5).
[4]周靚.國家防總秘書長劉寧:仍然處在防汛抗洪的關鍵期[EB/OL].http://www.eeo.com.cn/Politics/by_region/2010/07/21/176152.shtml.
[5]舟曲泥石流已致 1435人遇難[EB/OL].http://news.163.com/10/0822/18/6ENBFQO3000146BD.html
[6]楊萬國.四川震區新城地質次生災害集中暴發[N].新京報,2010-08-23.
[7]民政部國家減災中心.2008年度中國十大自然災害事件[EB/OL].http://www.mlr.gov.cn/zt/dqr/40dqr/wcdz/200903/t20090330_117289.htm.
[8]Wang G H.The Western Ordos Plateau as A Biodiversity Center of Relic Shrubs in Arid Areas of China[J].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2005,(14):3187-3200.
[9]Bennett M T.China’s 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r Business as Usual?[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65):700-712.
[10]Li T A,et al.Fragmentation of China’s Landscape by Roads and Urban Areas[J].Landscape Ecology,2010,(25):839-853.
[11]Zhao G,Shao G.F.Logging Restrictions in China:A Turning Point for Forest Sustainability[J].Journal of Forestry,2006,(100):34-37.
[12]Fiona K.et al.Hypolithic Microbial Community of Quartz Pavement in the High-Altitude Tundra of Central Tibet[J].Microbiology Ecology,2010,(60):730-739.
[13]Liu Q,et al.Grass(Poaceae)Richness Patterns Across China’s Nature Reserves[J].Plant Ecology,2009,(201):531-551.
[14]New T,Xie Z Q.Impacts of Large Dams on Riparian Vegetation:Applying Global Experience to the Case of China’s Three Gorges Dam[J].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2008,(17):3149-3163.
[15]Xi J,Hwang W.Relocation Stress,Coping,and Sense of Control Among Resettlers Resulting from China’s Three Gorges Dam Project[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0,December 8(Online FirstTM),DOI 10.1007/s11205-010-9758-5.
[16]Tilt B.Smallholders and the“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Adapting to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ese Agriculture[J].Human Ecology,2008,(36):189-199.
[17]Dai L M,et al.China’s Classification-Based Forest Management:Procedures,Problems,and Prospects[J].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9,(43):1162-1173.
[18]譚秀娟,鄭欽玉.我國水資源生態足跡分析與預測[J].生態學報,2009,29(7):3559-3567
[19]張穎,王萬茂.中國省(市)區生態足跡差異實證分析[J].中國土地科學,2004,(4):19-24.
[20]張秀明,姜志德.2009生態農業與循環農業的比較[J].農機化研究,2009,(6):231-235.
[21]荀麗麗,包智明.政府動員型環境政策及其地方實踐[J].中國社會科學,2007,(5):114-129.
[22]任保平,陳丹丹.西部經濟和生態環境互動模式:產業互動視角的分析[J].財經科學,2007,(1):119-124.
[23]董鎖成,張小軍,王傳勝.“中國西部生態——經濟區的主要特征與癥結”[J].資源科學,2005,(6):103-111.
[24]周永娟,王效科,歐陽志云.生態系統脆弱性研究[J].生態經濟,2009,(11):165-168.
[25]高鴻雁.內蒙古西部生態脆弱區生態綜合治理模式探析——以阿拉善盟為典型案例的分析[J].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2010,(5):39-41.
[26]Magretta J.Managing in the New Economy(ed.)[M].Boston Cambridge:Harvard Business Press,1999:IntroductionⅧ.
[27]Rapport D J,Friend A.M,Toward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A Stress-Response Approach[Z].Statistics Canada 11-510,Ottawa,87.
[28]Rapport D J,Costanza R,McMichael A J.Assessing Ecosystem Health[J].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1998,13(10):397-402.
[29]Wolfslehner B,Vacik H.Evaluating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Strategies with the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in a Pressure-State-Response framework[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8,88(1):1-10.
[30]尚虎平.我國地方政府績效評估悖論:高績效下的政治安全隱患[J].管理世界,2008,(4):69-79.
[31]陳振明,薛瀾.中國公共管理研究的重點領域與主題[J].中國社會科學,2007,(3):140-152.
[32]卓越.政府績效管理導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