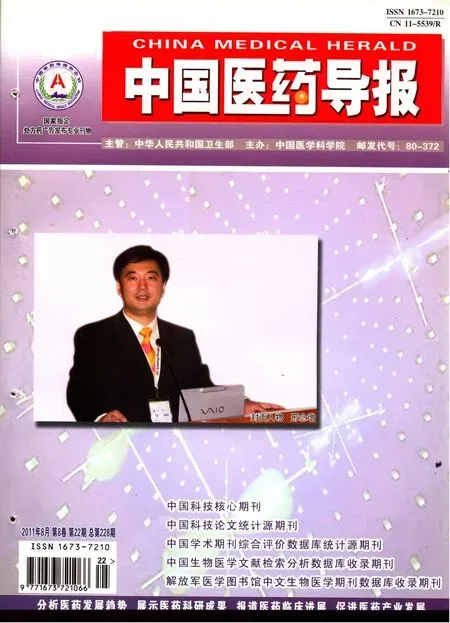胸腰椎爆裂骨折并截癱治療的臨床觀察
胡凱
湖南省株洲市一醫院脊椎外科,湖南 株洲 412000
胸腰椎爆裂骨折是臨床常見的嚴重創傷,屬高能量損傷,常見于高處墜傷、車禍傷,塌方、地震亦是重要原因,往往伴隨不同程度的神經功能損傷。其治療目的是糾正畸形,解除脊髓壓迫并恢復脊柱穩定性[1]。
我科自1999年成功開展胸腰椎爆裂骨折并截癱的手術治療,已系統認識到胸腰椎爆裂骨折并截癱的機制及治療特點。選取2002年1月~2008年12月我科收治的胸腰椎爆裂骨折并截癱的患者,并且成功施行手術治療,進行隨訪統計共計132例,做回顧性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132例患者中,男 97例,女35例;年齡18~59歲,平均(35.0±5.8)歲。根據術前常規拍攝X線、CT和MRI等,損傷部位:T1121例、T1238例、L135例、L229例、L39例。傷后至手術時間 4~15 d,平均(6.5±3.6)d。根據 Denis 分類[2],骨折類型均為爆裂骨折。術前神經功能Frankel分級[3],A型43例(32.58%),B 型 57例(43.18%),C 型 16 例(12.12%),D 型10例(7.58%),E 型 6例(4.55%)。109例(82.58%)為單一椎體的骨折,23例(17.42%)為多節段相鄰椎體骨折脫位。骨折椎體高度平均丟失61.4%,椎管占位平均達40.7%,傷椎上下終板夾角平均38.2°。依據不同的臨床特點,63例選擇前路手術(A 組),男 50 例,女 13 例,年齡 19~57 歲,平均(34.7±5.7)歲,傷后至手術時間平均(6.7±3.3)d;69例選擇后路手術,男47例,女12例,年齡18~59歲,平均(35.1±5.2)歲,傷后至手術時間平均(6.1±3.9)d。經統計學處理,兩組年齡、性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術前所有患者或家屬簽署手術知情同意書,知曉手術的必要性及危險性,同意進行手術治療,并對術后的恢復治療及康復鍛煉可以配合。
1.2 手術方法
術前均根據CT及MRI檢查制訂手術方案,決定減壓范圍,采用不同方法對脊髓進行充分減壓。術中具體情況利用切除的松質骨、同種異體骨或鈦網進行充分植骨。
前路手術前路內固定組 (A組),根據患者情況選擇Armstrong鋼板、Kaneta裝置;一般采用右側臥位,應用腰橋將季肋部與髂骨分開。切口從T10棘突旁5 cm起沿11肋斜形向下至腹直肌旁,逐層切開,切除11肋,鈍性剝離胸膜反折處,向上推開。將腹膜連同內臟推向中線,切開膈肌腳和膈肌,翻開腰大肌,在椎體腰部找到節段血管并結扎,顯露所需椎體,一般要顯露病椎及上下各一椎。充分切除傷椎上下椎間盤纖維環,同時保留終板,準備植骨床。在病椎上下椎按要求正確置入固定螺釘,迅速對病椎進行次全切除,對椎管充分減壓,去除腰橋撐開復位,在離硬膜囊5 mm處植入合適長度的髂骨或鈦網,安裝完成內固定系統,C形臂X線機透視了解復位、植骨、內固定正常后,徹底清理術野,安放引流,縫合傷口。
后路內固定手術組(B組),主要選用椎管減壓及骨折復位Dick釘或AF系統內固定術式。取俯臥位,胸部及側髂部墊枕、腹部懸空。C形臂 X線機定位,正中切口,顯露傷椎及上下兩個正常椎板、小關節及橫突基底部。遵照Weinstein解剖定位法[4]選擇椎根釘入點,稍咬平骨嵴后,將向后突進椎管的骨塊清除或復位,解除脊髓和神經根壓迫。C形臂X線機引導下確定骨隧道在椎弓根內后使用Dick釘或AF系統內固定,椎弓根螺釘至3/4深度,C形臂X線機透視檢查后,將螺釘擰緊至合適深度,安放左右螺紋桿并旋緊自鎖螺帽。調節螺桿及螺栓,使骨折復位達到椎體正常生理曲度或解剖復位,完成內固定操作。最后在橫突、椎板及小關節突處植骨。安裝完成內固定系統,C形臂X線機透視了解復位、植骨、內固定正常后,徹底清理術野,安放引流,縫合傷口。
一般1周左右鼓勵患者做腰背肌功能鍛煉,3周后帶腰圍等支具保護下起床活動。3個月后可漸撤去腰圍,并進行腰背肌功能鍛煉,若有脊髓損傷可給予高壓氧等治療措施以利脊髓功能恢復。
1.3 觀察指標
脊柱骨折手術的評價主要包括椎體和脊髓神經功能的情況。常規拍攝脊柱X線正側位片,根據手術前后的相關測量指標,計算出椎體前緣高度恢復率、后凸Cobb角糾正率;脊髓神經功能評價采用Frankel脊髓損傷分級[3],分為五級,A:運動、感覺功能完全喪失;B:不完全喪失,僅保留感覺;C:不完全喪失,僅保留運動 (無功能);D:不完全喪失,保留運動(有功能);E:所有運動、感覺功能完全恢復,但可能有異常反射。所有病例均采用末次隨訪情況評價其脊髓神經功能恢復情況。
1.4 統計學方法
所有資料均采用SPSS 16.0統計學軟件處理,計量資料數據以均數±標準差()表示。計量資料同組治療前后比較屬于自身前后配對設計,本組為隨機資料配對設計不成功、治療前后差值不服從正態分布,采用配對計量資料比較的秩和檢驗。組間比較屬于完全隨機設計,隨機設計多樣本比較的秩和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132例患者建立隨訪檔案,均獲得平均31.2個月(5~47個月)隨訪,未發生嚴重發癥及死亡。主要統計常規攝脊柱X線正側位片的情況及末次脊髓神經功能恢復情況。
2.1 手術時間、出血量及臥床時間的比較
A 組平均手術時間 (193±23)(157~246)min, 平均失血(860±123)(390~1 440)ml。B 組平均手術時間 (167±31)(125~233)min,失血(770±180)(410~1 730)ml。平均臥床時間 A 組(37±6)d,B 組(33±4)d,均帶胸腰支具下床。見表 1。
表1 兩組手術時間、出血量、臥床時間比較()

表1 兩組手術時間、出血量、臥床時間比較()
注:與 A 組比較,▲P=0.007<001,▼P=0.008<0.01,●P=0.048<005
組別 例數63 69 A組B組手術時間(min)193±23 167±31▲出血量(ml)860±123 770±118▼平均臥床時間(d)37±6 33±4●
2.2 兩組不同時間段的恢復指標比較
主要比較手術前后、拆除內固定時、末次隨訪時Cobb's角椎體高度占正常椎體高度比、椎管占位率。兩組術前各項比較因素指標平均值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隨訪,三個時間段兩組三個因素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末次隨訪時植骨融合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4<0.05)。見表 2。
表2 不同時間段各項指標的比較()

表2 不同時間段各項指標的比較()
注:與 A 組比較,*P=0.034<0.05
組別 術前 術后 拆除內固定時 末次隨訪A 組(n=63)Cobb's角(°)椎體高度(%)椎管占位率(%)植骨融合率(%)B 組(n=69)Cobb's角(°)椎體高度(%)椎管占位率(%)植骨融合率(%)22±2 40±8 60±13 5±2 90.±12 10±3 8±3 85±21 8±2 8±2 84±17 8±2 21.4±9.1 22±3 40±7 59±14 4±1 86±9 9±2 7±1 79±17 7±1 6±1 81±12 6±1 61.6±21.1*
其中,A組有3例、B組有1例在椎管減壓時撕破硬膜囊修補失敗,安置引流7 d后拔管,術后常規治療、檢測、補充電解質,最終傷口甲級愈合。B組有1例患者手術短節段固定,治療依從性較差,下地過早,Cobb's角基本回到術前水平約為30°,并造成L1椎弓根2枚螺釘斷裂,經2次手術植骨6個月左右融合,無明顯后遺癥。
2.3 兩組術前及末次隨訪時神經功能Frankel分級比較
末次隨訪時脊髓神經功能絕大部分較術前提高1~3級,原有神經癥狀未加重,未增加新的神經癥狀。其中,A組有57例較術前神經功能提高1~3級,占90.5%;B組有59例較術前神經功能提高1~3級,占85.5%。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7<0.05)。見表 3。

表3 兩組神經功能Frankel分級變化情況比較(例)
其中B組有1例患者術后一直有腰背部鈍痛,經理療等治療方法,患者腰背部鈍痛癥狀稍改善。
3 討論
3.1 統計結果分析
在手術時間及出血量的比較、不同時間段的恢復指標等因素,兩組比較,后路內固定手術B組均優于前路手術前路內固定A組。其中在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的比較方面,B組與A組的比較有顯著差異,表明在這兩方面的比較上,B組的優勢較A組明顯,可以更好地減少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由此可以減少患者麻醉的并發癥,以及患者的輸血的費用,可以更好地減少因為輸血而產生的一些反應。Cobb's角、椎體高度占正常椎體高度比、椎管占位率,兩組比較無明顯差異。神經功能Frankel分級的比較,A組略微優于B組,表明前路手術內固定可以較好的恢復神經的功能。
3.2 手術時機的選擇
目前對于胸腰椎骨折并截癱患者手術時機的選擇尚存有爭議[5-6]。本組手術均于傷后數日施行(平均7.5 d),術后神經功能障礙未見惡化,且不全截癱患者術后均有不同程度神經功能的改善,筆者認為手術時機在傷后按照不同患者的情況具體確定,手術最佳時機宜在傷后4~8 d內。術前時間過長則加重骨折復位的困難,術后椎體畸形的糾正與椎管占位的改善不能達到預期,不利于受損神經的功能恢復;術前時間過短則脊髓水腫尚未消退,且患者機體未得到充分準備,術前準備尚未完備,手術會加重脊髓的損傷,手術的應激導致術中及術后并發癥的增多[7-8]。
3.3 手術方式的選擇
對于胸腰椎骨折,目前手術方式主要分為前路與后路兩大類,兩種手術途徑各有優缺點。
Schnee等[9]認為對于前路手術的適應證為椎體壓縮和椎管受壓>40%、Cobb's角>15°,并且后柱穩定的患者,無論伴或不伴脊髓損傷;后路手術的適應證為椎體壓縮和椎管受壓<40%;且其認為前路手術比后路手術可以較好地恢復脊髓的損傷及矯正壓縮變形的椎體。
脊髓不完全損傷患者且CT或MRI證實脊髓前方受壓時宜施行前路手術;當患者脊柱前、中柱完全破壞或傷后時間較長,預期后路減壓不徹底時也宜積極采用前路手術行前方減壓[10]。前路手術可在直視下切除致壓物,可以充分減壓,前路減壓后,合理植骨,恢復椎體高度及脊柱生物力學平衡,提供了神經恢復的生理環境,促進受傷脊髓的恢復。
后路手術解剖較簡單,創傷小,固定節段少,固定牢固,出血不多,脊柱功能保持良好,通過體位復位和利用器械復位可達到一定程度的間接減壓并恢復椎體生理曲度;切除病椎椎板及棘突結合使用特殊器械將前方致壓物間接去除,使脊髓和神經根減壓充分;操作相對簡單,利于基層醫院開展。
前、后路手術的選擇不依賴于椎體后凸角的大小和椎管受壓的程度,而主要取決于脊髓損傷受壓的部位以及脊柱生物力學破壞的程度。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雖然行前路固定時耗時較長,出血較多,但其在平均住院日以及術后并發癥方面未見增多,且由于減壓徹底,椎管恢復完全,術后神經功能的恢復明顯優于后路手術。
[1]周志康.AF系統治療胸腰椎骨折伴脊髓損傷[J].中國骨傷,2009,22(7):497.
[2]Denis F.The three-column spine and its signification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acute thoracolumbar spinal injuries[J].Spine,1983,8(4):817-818.
[3]Frankel HL,Hancock DO,Hyslop G,et al.The value of postural reduction in the initial management of closed injuries of the spine with paraplegia and tetraplegia[J].Paraplegia,1969,7(6):179-180.
[4]朱崧.后路減壓植骨內固定治療胸腰椎骨折合并脊髓損傷[J].實用臨床醫學,2007,8(7):52.
[5]Schnce CS,Ansell LV.Selection criteria and outcome of operation with and without neurological deficit[J].J Neurofugery,2007,86(6):48-55.
[6]呂實川,蘇偉,劉思榮,等.脊髓內外減壓治療胸腰段脊髓損傷[J].中華骨科雜志,2005,16(4):210-212.
[7]崔明輝.中西醫結合治療胸腰椎骨折伴脊髓神經損傷[J].中國當代醫藥,2009,16(18):152-154.
[8]李忠澤,楊惠光,張云慶,等.胸腰椎骨折合并截癱側前路Kaneda及Z-plate內固定的臨床研究[J].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2009,18(1):26-29.
[9]Schnce CS,Ansell LV.Selection criteria and outcome of operation with and without neurological deficit[J].J Neurofugery,2007,86(6):48-55.
[10]霍洪軍,溫樹正,郭文通,等.前路減壓Kaneta裝置內固定治療胸腰段爆散性骨折[J].中國脊柱脊髓雜志,2008,7(3):123-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