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shuí)更適合發(fā)展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
——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與非國(guó)有企業(yè)研發(fā)行為的比較
肖興志,王建林
(東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產(chǎn)業(yè)組織與企業(yè)組織研究中心,遼寧 大連 116025)
一、引 言
與最近推出的發(fā)展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類(lèi)似,2006年2月中國(guó)曾推出《國(guó)家中長(zhǎng)期科學(xué)和技術(shù)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 (2006—2020)》,其中提到重點(diǎn)發(fā)展大型飛機(jī)項(xiàng)目,當(dāng)年一批飛機(jī)專(zhuān)家在廣東創(chuàng)建了一家民營(yíng)性質(zhì)的飛機(jī)設(shè)計(jì)公司——昌盛公司,隨后3年中昌盛公司自籌數(shù)千萬(wàn)元投入大型飛機(jī)的研究。2008年5月國(guó)家國(guó)資委、上海市政府等部門(mén)共同出資組建中國(guó)商用飛機(jī)有限責(zé)任公司,從事大型飛機(jī)的設(shè)計(jì)與制造,昌盛公司由于無(wú)法獲得政策和資金支持,遂申請(qǐng)加盟中國(guó)商用飛機(jī)有限責(zé)任公司,最終未果,目前昌盛公司的研發(fā)團(tuán)隊(duì)正面臨解散。這一案例曾激起熱烈討論,這里我們不想分析昌盛公司是否應(yīng)該獲得政府支持,畢竟在大飛機(jī)項(xiàng)目上,政府事先并未公開(kāi)招標(biāo),而中國(guó)商用飛機(jī)有限責(zé)任公司拒絕昌盛公司加盟也被看作是普通的企業(yè)行為,但它仍給我們提出這樣一個(gè)問(wèn)題,中國(guó)在未來(lái)振興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時(shí),是否一定要采用國(guó)有企業(yè)為載體,或者政府是否應(yīng)優(yōu)先扶持國(guó)有企業(yè)。
回答上述問(wèn)題的關(guān)鍵是:國(guó)有企業(yè)是否比非國(guó)有企業(yè)具有更高的創(chuàng)新動(dòng)力和創(chuàng)新效率。一種流行的觀(guān)點(diǎn)是,國(guó)有企業(yè)由于存在效率、決策等問(wèn)題會(huì)在創(chuàng)新方面劣于非國(guó)有企業(yè)。但也有不同的聲音,國(guó)務(wù)院國(guó)資委研究中心的彭建國(guó)認(rèn)為,央企擁有先進(jìn)的創(chuàng)新科技和雄厚的資金優(yōu)勢(shì),在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這場(chǎng)競(jìng)賽中,中央企業(yè)責(zé)無(wú)旁貸。2010年5月出臺(tái)的《國(guó)務(wù)院關(guān)于鼓勵(lì)和引導(dǎo)民間投資健康發(fā)展的若干意見(jiàn)》(“新非公36條”)的26條提到“鼓勵(lì)和引導(dǎo)民營(yíng)企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可見(jiàn)在政策層面政府并非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情有獨(dú)鐘”。
較少文獻(xiàn)直接分析中國(guó)國(guó)有企業(yè)和非國(guó)有企業(yè)研發(fā)行為和特征,部分采用行業(yè)面板數(shù)據(jù)的文獻(xiàn)涉及到國(guó)有產(chǎn)權(quán)比重對(duì)研發(fā)效率的影響,得出的結(jié)論大部分為國(guó)有企業(yè)比重增加會(huì)降低研發(fā)效率。但是我們認(rèn)為當(dāng)前國(guó)有企業(yè)并沒(méi)有在各個(gè)行業(yè)隨機(jī)分布,伴隨著國(guó)有企業(yè)改革,國(guó)有企業(yè)行業(yè)布局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段文斌調(diào)查了1993—2007年間的國(guó)有資本的行業(yè)分布,發(fā)現(xiàn)國(guó)有經(jīng)濟(jì)集中在煙草加工業(yè)、石油和天然氣開(kāi)采業(yè)等11個(gè)行業(yè)[1]。各個(gè)行業(yè)對(duì)于研發(fā)的需求,Jefferson等認(rèn)為一些同質(zhì)品行業(yè)如采掘業(yè)、煙草加工業(yè)本身的研發(fā)需求較少,因此已有文獻(xiàn)認(rèn)為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效率低,其實(shí)可能反映了該行業(yè)本身的研發(fā)效率低,而與所有制性質(zhì)無(wú)關(guān)[2]。
本文將研究范圍限定在高技術(shù)行業(yè),不僅是為了避免樣本選擇性偏差所帶來(lái)的影響,更主要的是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與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同屬于研發(fā)密集型產(chǎn)業(yè),實(shí)證結(jié)論更富有政策含義。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的“新興”二字決定這些產(chǎn)業(yè)大部分還在萌芽期,但是其中某些子產(chǎn)業(yè)的確為當(dāng)前的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如新興信息產(chǎn)業(yè)中的通信網(wǎng)絡(luò)和集成電路、生物產(chǎn)業(yè)中的生物醫(yī)藥、高端裝備制造業(yè)中的航空航天等,因此由目前的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推斷未來(lái)的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既是可行也是可取的。本文對(duì)同處于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中的國(guó)有企業(yè)樣本和非國(guó)有企業(yè)樣本進(jìn)行分析和比較,力圖回答以下問(wèn)題:國(guó)有企業(yè)和非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投入有何差異?研發(fā)產(chǎn)出有何差異?研發(fā)效率有何差異?對(duì)政府資助的反應(yīng)有何不同,除此之外還受何種因素影響?這些能給中國(guó)未來(lái)發(fā)展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帶來(lái)什么啟示?
二、文獻(xiàn)綜述
國(guó)外對(duì)企業(yè)創(chuàng)新行為的研究重點(diǎn)關(guān)注企業(yè)規(guī)模和市場(chǎng)結(jié)構(gòu)的影響,Schumpeter在《資本主義、社會(huì)主義和民主主義》一書(shū)中提到大規(guī)模企業(yè)憑借資金優(yōu)勢(shì),有能力進(jìn)行創(chuàng)新活動(dòng),這種活動(dòng)會(huì)鞏固企業(yè)的壟斷地位,這又將進(jìn)一步刺激其未來(lái)創(chuàng)新[3]。Arrow認(rèn)為相對(duì)于壟斷性市場(chǎng)來(lái)講,競(jìng)爭(zhēng)性市場(chǎng)更有利于通過(guò)創(chuàng)新產(chǎn)生利潤(rùn)流,因此競(jìng)爭(zhēng)性環(huán)境下的企業(yè)其創(chuàng)新動(dòng)力更大,圍繞這兩種觀(guān)點(diǎn),出現(xiàn)了大量經(jīng)驗(yàn)性研究[4]。部分學(xué)者對(duì)中國(guó)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行為進(jìn)行了考察,并根據(jù)國(guó)情加入了所有制的影響,Jefferson等分析了中國(guó)1997—1999年的大型制造業(yè)企業(yè),發(fā)現(xiàn)企業(yè)規(guī)模對(duì)研發(fā)投入沒(méi)有顯著影響,國(guó)有資產(chǎn)比重會(huì)降低研發(fā)效率[2]。聶輝華等使用2001—2005年中國(guó)企業(yè)層面數(shù)據(jù)分析,發(fā)現(xiàn)企業(yè)的研發(fā)投入與規(guī)模、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是倒U型關(guān)系,同時(shí)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投入更多[5]。吳延兵分析了1994—2002年中國(guó)34個(gè)工業(yè)行業(yè)的面板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企業(yè)規(guī)模對(duì)研發(fā)投入有顯著的促進(jìn)作用,而國(guó)有產(chǎn)權(quán)比重對(duì)研發(fā)投入并沒(méi)有顯著影響[6]。
企業(yè)研發(fā)投入最終需要形成研發(fā)產(chǎn)出,有些學(xué)者以研發(fā)產(chǎn)出作為衡量創(chuàng)新的變量,周黎安和羅凱考察了1985—1997年中國(guó)分省面板數(shù)據(jù),采用地區(qū)人均專(zhuān)利數(shù)衡量研發(fā)產(chǎn)出,發(fā)現(xiàn)企業(yè)規(guī)模對(duì)創(chuàng)新有顯著正面影響,但這一關(guān)系來(lái)源于非國(guó)有企業(yè)[7]。朱有為和徐康寧分析了中國(guó)1995—2004年13個(gè)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面板數(shù)據(jù),采用新產(chǎn)品銷(xiāo)售收入作為研發(fā)產(chǎn)出并測(cè)算研發(fā)的技術(shù)效率,發(fā)現(xiàn)企業(yè)規(guī)模、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都與研發(fā)效率呈正相關(guān),外資企業(yè)比重、國(guó)有企業(yè)比重都與研發(fā)效率呈正相關(guān)[8]。馮根福等分析了中國(guó)1996—2004年的35個(gè)行業(yè)的面板數(shù)據(jù),采用新產(chǎn)品開(kāi)發(fā)數(shù)目作為研發(fā)的產(chǎn)出變量并測(cè)算了研發(fā)效率,發(fā)現(xiàn)企業(yè)規(guī)模、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程度都與企業(yè)研發(fā)效率呈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國(guó)有企業(yè)比重與企業(yè)研發(fā)效率呈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9]。
與已有的關(guān)注中國(guó)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文獻(xiàn)相比,本文的貢獻(xiàn)有以下幾點(diǎn):第一,使用兩組分開(kāi)的樣本——國(guó)有企業(yè)和非國(guó)有企業(yè)——研究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中企業(yè)的研發(fā)行為,避免使用全行業(yè)數(shù)據(jù)帶來(lái)的估計(jì)偏誤問(wèn)題。第二,使用聯(lián)立方程進(jìn)行研究,已有文獻(xiàn)將研發(fā)投入和研發(fā)產(chǎn)出都視為創(chuàng)新活動(dòng),兩者之間肯定不能劃等號(hào),本文同時(shí)考慮研發(fā)投入和產(chǎn)出的情況,設(shè)定一個(gè)包含研發(fā)投入方程與研發(fā)產(chǎn)出方程的聯(lián)立方程系統(tǒng),研究方法更為科學(xué)和嚴(yán)謹(jǐn)。第三,考慮了政府資助對(duì)企業(yè)創(chuàng)新活動(dòng)的影響。目前大量研究顯示政府資助會(huì)影響企業(yè)研發(fā)投入,如Wallsten分析美國(guó)公司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政府資助會(huì)擠出公司自身的研發(fā)投入[10],Lach分析了以色列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政府資助刺激了小公司研發(fā)投入[11]。
三、數(shù)據(jù)和指標(biāo)描述
本文使用的數(shù)據(jù)來(lái)自《中國(guó)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統(tǒng)計(jì)年鑒》(2004年、2005年和2009年),以及《中國(guó)統(tǒng)計(jì)年鑒》(2009年)。《中國(guó)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統(tǒng)計(jì)年鑒》不僅提供了各個(gè)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的總體數(shù)據(jù),還提供了細(xì)分所有制成分的數(shù)據(jù),據(jù)此可以獲得完整的國(guó)有企業(yè)樣本和非國(guó)有企業(yè)樣本,航天器制造業(yè)和雷達(dá)及配套設(shè)備制造業(yè)的企業(yè)數(shù)量過(guò)少,且涉及領(lǐng)域特殊,這里將其剔除。最終選定了以下15個(gè)行業(yè):化學(xué)藥品制造、中成藥制造、生物生化制品的制造、飛機(jī)制造及修理、通信設(shè)備制造、廣播電視設(shè)備制造、電子器件制造、電子元件制造、家用視聽(tīng)設(shè)備制造、其他電子設(shè)備制造、電子計(jì)算機(jī)整機(jī)制造、電子計(jì)算機(jī)外部設(shè)備制造、辦公設(shè)備制造、醫(yī)療設(shè)備及器械制造、儀器儀表制造,這些行業(yè)最早可查到較完整資料的年份為1998年,這樣本文選取樣本時(shí)間區(qū)間為1998—2008年。表1詳細(xì)說(shuō)明研發(fā)投入、政府資助和研發(fā)產(chǎn)出這三個(gè)指標(biāo)的數(shù)據(jù)。

表1 各指標(biāo)的描述性統(tǒng)計(jì)
(一)研發(fā)投入
本文中我們使用研發(fā)密度這一相對(duì)量指標(biāo)表示研發(fā)投入,這便于我們識(shí)別研發(fā)投入的真正來(lái)源。可以利用的反映企業(yè)研發(fā)投入的指標(biāo)有兩個(gè),一個(gè)是科技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支出占銷(xiāo)售收入的比重,另一個(gè)是R&D經(jīng)費(fèi)支出占銷(xiāo)售收入的比重,科技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支出指的是本單位開(kāi)展科技活動(dòng)所實(shí)際支出的全部費(fèi)用,R&D經(jīng)費(fèi)支出則指的是科技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支出中用于基礎(chǔ)研究、應(yīng)用研究和試驗(yàn)發(fā)展三類(lèi)項(xiàng)目(課題)以及這三類(lèi)項(xiàng)目 (課題)的管理和服務(wù)的費(fèi)用支出,因此科技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支出是更廣泛意義上的研發(fā)投入。根據(jù)所選擇的15個(gè)行業(yè)1998—2008年數(shù)據(jù),我們分別計(jì)算了國(guó)有企業(yè)和非國(guó)有的研發(fā)投入情況,可以發(fā)現(xiàn)無(wú)論以科技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支出衡量,還是以R&D經(jīng)費(fèi)支出衡量,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投入都不低于非國(guó)有企業(yè),平均來(lái)講國(guó)有企業(yè)的科技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支出占銷(xiāo)售收入的比重為3.14%,而非國(guó)有企業(yè)這一指標(biāo)為2.78%,國(guó)有企業(yè)R&D經(jīng)費(fèi)支出占銷(xiāo)售收入比重為1.77%,而非國(guó)有企業(yè)這一指標(biāo)為1.75%。
(二)政府資助
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是研發(fā)密集型產(chǎn)業(yè),也是國(guó)家財(cái)政資金重點(diǎn)扶持的產(chǎn)業(yè),企業(yè)的科技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籌集途徑有政府資金、企業(yè)資金和金融機(jī)構(gòu)貸款,政府資金占企業(yè)科技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籌集的比重可以衡量政府對(duì)企業(yè)研發(fā)的資助力度。該指標(biāo)存在數(shù)據(jù)缺失情況:辦公設(shè)備制造業(yè)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6年無(wú)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電子計(jì)算機(jī)外部設(shè)備制造業(yè)1999年和2000年無(wú)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醫(yī)療設(shè)備及器械制造業(yè)2003年無(wú)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最終我們放棄了這些樣本點(diǎn)。從表1中可以看出國(guó)有企業(yè)科技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中的政府資金比例顯著高于非國(guó)有企業(yè),平均來(lái)講國(guó)有企業(yè)的科技經(jīng)費(fèi)中11.38%來(lái)自政府,而非國(guó)有企業(yè)僅有4.2%,考慮到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投入較大,所以實(shí)際上國(guó)有企業(yè)所分享的政府撥款總額要遠(yuǎn)遠(yuǎn)大于非國(guó)有企業(yè)。非國(guó)有企業(yè)的這一指標(biāo)最小值為0,說(shuō)明某些非國(guó)有企業(yè)在特定年份沒(méi)有得到政府任何科技經(jīng)費(fèi)資助。為了反映國(guó)家科技撥款的投向,我們還進(jìn)一步計(jì)算了國(guó)有企業(yè)分享政府科技撥款的比例,計(jì)算方式為國(guó)有企業(yè)科技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籌集中的政府資金占全部企業(yè)科技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籌集中的政府資金的比重。可以看到國(guó)有企業(yè)分享到的政府財(cái)政科技撥款平均為52.6%,要高于非國(guó)有企業(yè),這一指標(biāo)的最大值為1,說(shuō)明政府撥款在某些年份某些行業(yè)全部投向國(guó)有企業(yè),核查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共有8個(gè)這樣的樣本點(diǎn),而8個(gè)樣本點(diǎn)中的3個(gè)為研發(fā)總支出最多的飛機(jī)制造及修理行業(yè),這些統(tǒng)計(jì)結(jié)果說(shuō)明政府科技撥款投向具有很強(qiáng)的傾向性,國(guó)有企業(yè)分享了大部分政府科技資金。對(duì)這一現(xiàn)象,我們?cè)僖?008年的總體數(shù)據(jù)為例補(bǔ)充說(shuō)明,2008年政府為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投入的科技經(jīng)費(fèi)為87.88億元,國(guó)有企業(yè)獲得了其中的67.39億元,大約占76.68%,而國(guó)有企業(yè)數(shù)量?jī)H占6.75%。
(三)研發(fā)產(chǎn)出
對(duì)于研發(fā)產(chǎn)出變量,我們使用新產(chǎn)品銷(xiāo)售收入占銷(xiāo)售收入的比重表示。剔除了四個(gè)數(shù)據(jù)可靠性值得懷疑的樣本,一個(gè)是2006年的通信設(shè)備制造制造業(yè),該年該行業(yè)的國(guó)有企業(yè)新產(chǎn)品銷(xiāo)售收入為460.97億元,而銷(xiāo)售收入僅有400.40億元;一個(gè)為1998年的家用視聽(tīng)設(shè)備制造業(yè),該年該行業(yè)的國(guó)有企業(yè)新產(chǎn)品銷(xiāo)售收入為206.19億元,而銷(xiāo)售收入僅有141.39億元;另外兩個(gè)為2002年和2003年飛機(jī)制造及修理業(yè),該行業(yè)2002年和2003年的非國(guó)有企業(yè)新產(chǎn)品銷(xiāo)售收入分別為58.4億元和134.80億元,但銷(xiāo)售收入僅分別為9.38億元和11.69億元。我們發(fā)現(xiàn)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產(chǎn)出平均高于非國(guó)有企業(yè),同時(shí)國(guó)有企業(yè)研發(fā)產(chǎn)出方差也稍大,因此單就研發(fā)產(chǎn)出而言,國(guó)有企業(yè)要領(lǐng)先于非國(guó)有企業(yè),但是兩類(lèi)企業(yè)的研發(fā)投入是不同的,僅通過(guò)描述性結(jié)果無(wú)法判斷誰(shuí)的研發(fā)效率更高。
四、實(shí)證分析
(一)模型估計(jì)
本文將要估計(jì)的模型為以下聯(lián)立方程:

其中,(1)為研發(fā)投入方程,RDexp為研發(fā)投入變量,這里使用科技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支出這一廣義的研發(fā)投入,計(jì)算方法為單位銷(xiāo)售收入的研發(fā)投入,在隨后的穩(wěn)健性檢驗(yàn)中我們也使用了R&D經(jīng)費(fèi)支出;GOfund為政府資助力度,計(jì)算方法為政府資金占企業(yè)科技活動(dòng)經(jīng)費(fèi)籌集的比重,SIZE為企業(yè)平均規(guī)模,計(jì)算方法為行業(yè)總產(chǎn)值除以企業(yè)個(gè)數(shù),其中行業(yè)總產(chǎn)值使用工業(yè)品出廠(chǎng)價(jià)格,按1998年不變價(jià)格計(jì)算;PROF為盈利情況,計(jì)算方法為行業(yè)利潤(rùn)總額占行業(yè)銷(xiāo)售收入比重;COMP為行業(yè)競(jìng)爭(zhēng)狀況,用行業(yè)內(nèi)企業(yè)個(gè)數(shù)表示;u為研發(fā)投入方程的行業(yè)個(gè)體效應(yīng),ε為研發(fā)產(chǎn)出方程的隨機(jī)干擾項(xiàng)。(2)為研發(fā)產(chǎn)出方程,NPsales為研發(fā)產(chǎn)出變量,計(jì)算方法為新產(chǎn)品銷(xiāo)售收入占全部銷(xiāo)售收入比重,也有研究使用企業(yè)利潤(rùn)作為研發(fā)產(chǎn)出變量,不過(guò)我們認(rèn)為盡管研發(fā)最終效果需要反映在企業(yè)盈利上,但這是一個(gè)間接的過(guò)程,可能需要一個(gè)較長(zhǎng)的滯后期,而使用新產(chǎn)品銷(xiāo)售收入/全部銷(xiāo)售收入則更為直接;FORE為外資的知識(shí)外溢,計(jì)算方法為行業(yè)內(nèi)三資企業(yè)總產(chǎn)值占全行業(yè)企業(yè)總產(chǎn)值比重;v為研發(fā)產(chǎn)出方程的行業(yè)個(gè)體效應(yīng),η為研發(fā)產(chǎn)出方程的隨機(jī)干擾項(xiàng)。所有變量都取自然對(duì)數(shù),由于PROF存在負(fù)值情況,將這一指標(biāo)全部加1后再取自然對(duì)數(shù),此外考慮到投入產(chǎn)出之間的時(shí)滯,同時(shí)也為了減少內(nèi)生性問(wèn)題,將所有解釋變量都滯后一期。
本文分國(guó)有企業(yè)和非國(guó)有企業(yè)兩類(lèi)樣本進(jìn)行估計(jì)。估計(jì)之前需要解決識(shí)別問(wèn)題,對(duì)于遞歸聯(lián)立方程而言,如果假定方程之間隨機(jī)擾動(dòng)項(xiàng)是無(wú)關(guān)的,那么相當(dāng)于給協(xié)方差矩陣施加了一個(gè)約束,這一約束足以識(shí)別模型,接下來(lái)的估計(jì)也很簡(jiǎn)單可以,可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逐個(gè)估計(jì)模型,而不會(huì)產(chǎn)生聯(lián)立方程中的非一致問(wèn)題[12]。本文主要集中分析這一種情況,模型中內(nèi)生性解釋變量滯后了一期,可以大致認(rèn)為兩個(gè)方程之間的隨機(jī)擾動(dòng)項(xiàng)是無(wú)關(guān)的,同時(shí)作為穩(wěn)健性檢驗(yàn)的一部分,我們也報(bào)告了隨機(jī)擾動(dòng)項(xiàng)相關(guān)時(shí)的估計(jì)結(jié)果。
表2為研發(fā)投入方程 (1)的估計(jì)結(jié)果,兩類(lèi)企業(yè)樣本的Hausman檢驗(yàn)都支持選擇固定效應(yīng)模型。估計(jì)結(jié)果表明政府支持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研發(fā)投入的影響不顯著,但政府支持對(duì)非國(guó)有企業(yè)研發(fā)投入的影響顯著為正,非國(guó)有企業(yè)科技經(jīng)費(fèi)中的政府資金比例每增加1%大約會(huì)帶來(lái)企業(yè)研發(fā)投入增加0.36%。企業(yè)規(guī)模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研發(fā)投入的影響顯著為正,說(shuō)明熊彼特的大企業(yè)有利于研發(fā)假說(shuō)適用于國(guó)有企業(yè),企業(yè)規(guī)模每增長(zhǎng)1%,大約帶來(lái)研發(fā)投入增長(zhǎng)0.65%;對(duì)于非國(guó)有企業(yè),企業(yè)規(guī)模的影響顯著為負(fù),熊彼特的假說(shuō)不再成立:小規(guī)模企業(yè)的研發(fā)投入反而更多,企業(yè)規(guī)模下降1%大約帶來(lái)研發(fā)投入增加0.5%。盈利狀況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研發(fā)投入的影響為負(fù)但不顯著,對(duì)于非國(guó)有企業(yè)的影響顯著為負(fù),高盈利企業(yè)無(wú)動(dòng)力研發(fā)說(shuō)明非國(guó)有企業(yè)短視問(wèn)題較為突出,存在“吃老本”現(xiàn)象[13]。競(jìng)爭(zhēng)程度僅僅影響國(guó)有企業(yè),行業(yè)中的企業(yè)數(shù)量越多,國(guó)有企業(yè)越傾向于增加研發(fā)投入,說(shuō)明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投入符合Arrow假說(shuō),非國(guó)有企業(yè)研發(fā)支對(duì)企業(yè)數(shù)量的反應(yīng)不敏感。
表3為擾動(dòng)項(xiàng)無(wú)關(guān)假設(shè)下研發(fā)產(chǎn)出方程 (2)的估計(jì)結(jié)果,兩類(lèi)企業(yè)樣本的Hausman檢驗(yàn)都支持選擇固定效應(yīng)模型。估計(jì)發(fā)現(xiàn)無(wú)論是國(guó)有樣本還是非國(guó)有企業(yè),在控制了諸如規(guī)模、盈利性、競(jìng)爭(zhēng)狀況、知識(shí)外溢等指標(biāo)后研發(fā)投入都是研發(fā)產(chǎn)出重要解釋變量,這說(shuō)明忽略研發(fā)投入單純分析研發(fā)產(chǎn)出是不合適的。比較兩類(lèi)企業(yè)研發(fā)投入的產(chǎn)出彈性系數(shù)大小,可見(jiàn)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效率稍微領(lǐng)先,兩類(lèi)企業(yè)的研發(fā)投入各增長(zhǎng)1%,國(guó)有企業(yè)研發(fā)產(chǎn)出大約增長(zhǎng)0.45%,而非國(guó)有企業(yè)研發(fā)產(chǎn)出大約增長(zhǎng)0.4%。企業(yè)規(guī)模顯著影響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產(chǎn)出,企業(yè)規(guī)模增長(zhǎng)1%大約會(huì)帶來(lái)研發(fā)產(chǎn)出增長(zhǎng)0.55%,而企業(yè)規(guī)模對(duì)非國(guó)有企業(yè)的影響盡管為正但不顯著。盈利性對(duì)兩類(lèi)企業(yè)的研發(fā)產(chǎn)出影響都為負(fù),但僅在非國(guó)有企業(yè)樣本估計(jì)中勉強(qiáng)通過(guò)顯著性檢驗(yàn),說(shuō)明企業(yè)的高盈利可能會(huì)降低其推出新產(chǎn)品的速度。競(jìng)爭(zhēng)程度會(huì)顯著正面影響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產(chǎn)出,這說(shuō)明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產(chǎn)出符合Arrow假說(shuō),但競(jìng)爭(zhēng)程度對(duì)非國(guó)有企業(yè)研發(fā)產(chǎn)出的影響不顯著。外資企業(yè)產(chǎn)值比重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產(chǎn)出影響不顯著,說(shuō)明國(guó)有企業(yè)沒(méi)有從外資企業(yè)那里得到太多技術(shù)轉(zhuǎn)移,對(duì)非國(guó)有企業(yè)的影響顯著為負(fù),一個(gè)可能的解釋是非國(guó)有企業(yè)樣本包含大量外資企業(yè),外資比重高使得行業(yè)內(nèi)外資企業(yè)研發(fā)的邊際產(chǎn)出下降,同時(shí)對(duì)本土非國(guó)有企業(yè)的溢出不足,最終外資比重對(duì)非國(guó)有企業(yè)整體的研發(fā)產(chǎn)出影響表現(xiàn)為負(fù)。

表2 研發(fā)投入方程估計(jì)

表3 研發(fā)產(chǎn)出方程估計(jì)
(二)穩(wěn)健性檢驗(yàn)
穩(wěn)健性檢驗(yàn)的目是考察結(jié)論是否對(duì)于估計(jì)方法或變量選擇敏感,如果改變估計(jì)方法或變換變量后,回歸結(jié)果沒(méi)有發(fā)生實(shí)質(zhì)變化,那么我們的結(jié)論便是穩(wěn)健的。這里使用兩種途徑進(jìn)行穩(wěn)健性檢驗(yàn),第一種途徑是假定隨機(jī)擾動(dòng)項(xiàng)之間是相關(guān)的,使用三階段最小二乘進(jìn)行重新估計(jì),第二種途徑是使用R&D經(jīng)費(fèi)支作為研發(fā)投入變量進(jìn)行重新估計(jì)。
如果兩個(gè)方程的隨機(jī)擾動(dòng)項(xiàng)之間是相關(guān)的,需要首先檢查聯(lián)立方程的可識(shí)別性,方程 (1)右邊全部為外生變量,所以方程 (1)可以識(shí)別,方程 (2)右邊含有內(nèi)生解釋變量,也含有一個(gè)本方程特有的外生變量FORE,因此方程 (2)也可以識(shí)別,此時(shí)使用最小二乘法逐個(gè)估計(jì)方程將是有偏和非一致的,需要改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鑒于之前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的Hausman檢驗(yàn)全部支持固定效應(yīng),這里直接采用固定效應(yīng)估計(jì),①我們首先使用STATA中的xtdata命令將數(shù)據(jù)“去均值化”,然后再使用針對(duì)截面數(shù)據(jù)的reg3命令得到三階段最小二乘結(jié)果。表4給出了相應(yīng)的估計(jì)結(jié)果,首先關(guān)注研發(fā)投入方程,政府資助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研發(fā)投入的影響仍然不顯著,對(duì)非國(guó)有企業(yè)影響為正且顯著,這些與逐一方程估計(jì)一致,只是彈性數(shù)值變小。企業(yè)規(guī)模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的影響仍然顯著為正,對(duì)非國(guó)有企業(yè)的影響仍然顯著為負(fù),與逐一方程估計(jì)一致,僅彈性絕對(duì)值變大。企業(yè)利潤(rùn)水平對(duì)于兩類(lèi)企業(yè)的研發(fā)投入影響都為負(fù),與逐一方程估計(jì)稍微不同的是僅國(guó)有企業(yè)的影響通過(guò)顯著性檢驗(yàn),說(shuō)明國(guó)有企業(yè)的短視效應(yīng)可能更大。競(jìng)爭(zhēng)狀況仍然顯著正向影響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投入,系數(shù)估計(jì)值變化不大,同時(shí)對(duì)非國(guó)有企業(yè)的影響由不顯著變?yōu)轱@著。再次觀(guān)察研發(fā)產(chǎn)出方程,兩類(lèi)企業(yè)研發(fā)投入的產(chǎn)出彈性估計(jì)仍然都顯著為正,盡管與逐一方程估計(jì)相比彈性值大大下降,但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產(chǎn)出彈性仍領(lǐng)先于非國(guó)有企業(yè)。與逐一方程估計(jì)一致,企業(yè)規(guī)模和行業(yè)競(jìng)爭(zhēng)狀況仍然都顯著正向影響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產(chǎn)出,而對(duì)非國(guó)有企業(yè)影響不顯著。與逐一方程估計(jì)稍微不同,盈利狀況開(kāi)始顯著負(fù)向影響兩類(lèi)企業(yè)的研發(fā)產(chǎn)出,說(shuō)明高技術(shù)行業(yè)的高額利潤(rùn)確實(shí)會(huì)降低企業(yè)研發(fā)產(chǎn)出,研發(fā)產(chǎn)出中存在“吃老本”現(xiàn)象。外資企業(yè)產(chǎn)值比重的影響與逐一方程估計(jì)類(lèi)似: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的影響不顯著,對(duì)非國(guó)有企業(yè)的影響顯著為負(fù),仍然顯示出高技術(shù)領(lǐng)域外資企業(yè)存在對(duì)內(nèi)資企業(yè)的技術(shù)封鎖。三階段最小二乘的估計(jì)結(jié)果顯示結(jié)論是穩(wěn)健的。
我們將R&D經(jīng)費(fèi)支作為研發(fā)投入變量重新估計(jì)方程 (1)和 (2),所有解釋變量都滯后一期,假定方程之間隨機(jī)擾動(dòng)項(xiàng)是無(wú)關(guān)的,估計(jì)結(jié)果見(jiàn)表5(所有Hausman檢驗(yàn)都支持選擇固定效應(yīng),這里僅報(bào)告了這一估計(jì)結(jié)果)。可見(jiàn)政府資助、企業(yè)規(guī)模、研發(fā)投入、競(jìng)爭(zhēng)程度、外溢效果等變量的顯著性水平及符號(hào)方向基本沒(méi)有發(fā)生實(shí)質(zhì)性變化,這說(shuō)明本文的分析結(jié)論具有較好的穩(wěn)健性。

表4 穩(wěn)健性檢驗(yàn)之一:三階段最小二乘估計(jì)

表5 穩(wěn)健性檢驗(yàn)之二:使用新變量估計(jì) (固定)
五、結(jié)論和政策含義
我們的分析顯示盡管?chē)?guó)有企業(yè)取得了大部分政府資助的研發(fā)資金,但是國(guó)有企業(yè)研發(fā)投入對(duì)政府資助不敏感,表明政府科技經(jīng)費(fèi)的資助沒(méi)有調(diào)動(dòng)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積極性,一個(gè)可能原因是國(guó)有企業(yè)更容易編造各種“項(xiàng)目”套取政府的研發(fā)資助,研發(fā)資助并非真正所需,企業(yè)與政府之間存在“跑部錢(qián)進(jìn)”現(xiàn)象。與此相反政府資助能夠顯著正向影響非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投入,科技經(jīng)費(fèi)資助程度的彈性大約為0.15。它給我們帶來(lái)的啟示是,在扶持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發(fā)展時(shí),政府對(duì)下?lián)艿目萍冀?jīng)費(fèi)資金應(yīng)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地物盡其用,并適當(dāng)向非國(guó)有資本和民營(yíng)資本傾斜,更多注意發(fā)揮非國(guó)有資本和民營(yíng)資本作用。
國(guó)有企業(yè)的研發(fā)投入和研發(fā)產(chǎn)出都符合熊彼特的假說(shuō),非國(guó)有企業(yè)則出現(xiàn)了相反的情況——規(guī)模越小研發(fā)投入越大,這表明大規(guī)模國(guó)有企業(yè)由于“不差錢(qián)”從而研發(fā)投入較大,而較小的非國(guó)有企業(yè)由于經(jīng)營(yíng)靈活也有較大的創(chuàng)新動(dòng)力。當(dāng)然這不足以質(zhì)疑或支持熊彼特的理論,僅是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狀的一個(gè)經(jīng)驗(yàn)觀(guān)察,但我們?nèi)钥蓳?jù)此判斷,如果要在短時(shí)間內(nèi)實(shí)現(xiàn)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快速發(fā)展,大型國(guó)有企業(yè)仍然是最重要的主體和主導(dǎo)力量,現(xiàn)階段大型國(guó)有企業(yè)擁有資金、政策、技術(shù)、人才等全面優(yōu)勢(shì),能夠?qū)崿F(xiàn)集中力量辦大事,在若干領(lǐng)域?qū)崿F(xiàn)快速突破。此外由于小規(guī)模的非國(guó)有企業(yè)也很熱衷于創(chuàng)新,在特定領(lǐng)域重視和引導(dǎo)小型非國(guó)有企業(yè)非常必要。
國(guó)有企業(yè)在研發(fā)效率上并不低于非國(guó)有企業(yè),一般認(rèn)為國(guó)有企業(yè)存在產(chǎn)權(quán)不清、委托代理等問(wèn)題,研發(fā)投入可能沒(méi)有得到最有效率的使用,但我們的實(shí)證結(jié)果顯示這并不是事實(shí),非國(guó)有企業(yè)在市場(chǎng)的驅(qū)動(dòng)下能夠?qū)崿F(xiàn)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chǎn)出,國(guó)有企業(yè)似乎也能做到這一點(diǎn)。研發(fā)效率的高低是一個(gè)值得深入探討的問(wèn)題,以上述政府科技資金投向?yàn)槔梢钥闯觯袊?guó)的經(jīng)濟(jì)政策對(duì)兩類(lèi)所有制企業(yè)并不是平等的,國(guó)有企業(yè)通常會(huì)得到更多的支持,這可能會(huì)有助于其提高研發(fā)效率。無(wú)論如何,研發(fā)的高效率并不意味著治理的高效率,中國(guó)的國(guó)有企業(yè)改革遠(yuǎn)未完成,在未來(lái)發(fā)展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時(shí),國(guó)有企業(yè)仍然需要完善經(jīng)營(yíng)機(jī)制,建立更規(guī)范的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
國(guó)有高技術(shù)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活動(dòng)與行業(yè)競(jìng)爭(zhēng)程度關(guān)系密切,行業(yè)內(nèi)企業(yè)加入會(huì)促進(jìn)國(guó)有企業(yè)增加研發(fā)投入并加快新產(chǎn)品推出。這給我們帶來(lái)的啟示是,在鼓勵(lì)大型國(guó)有企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時(shí),行業(yè)準(zhǔn)入一定要放開(kāi),決不能變鼓勵(lì)國(guó)有企業(yè)進(jìn)入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為國(guó)有企業(yè)壟斷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新非公36條”允許民間資本進(jìn)入國(guó)防科技工業(yè)等六大領(lǐng)域,并明確提出可以進(jìn)入法律法規(guī)未明確禁止準(zhǔn)入任何行業(yè)和領(lǐng)域,在發(fā)展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時(shí),能否有效落實(shí)“新非公36條”非常重要。
盈利水平負(fù)向影響兩類(lèi)企業(yè)的研發(fā)投入和研發(fā)產(chǎn)出,這可能和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本身特征有關(guān),“創(chuàng)造性毀滅”的領(lǐng)先者會(huì)獲得高額回報(bào),從而降低了其研發(fā)動(dòng)力和推出新產(chǎn)品的速度。這也從另一角度說(shuō)明行業(yè)內(nèi)競(jìng)爭(zhēng)的重要性,因?yàn)槠髽I(yè)數(shù)目的增加會(huì)提高泊松到達(dá)率,縮短技術(shù)領(lǐng)先者的利潤(rùn)流持續(xù)時(shí)間,因此在未來(lái)發(fā)展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時(shí),必須營(yíng)造一個(gè)充分競(jìng)爭(zhēng)的市場(chǎng)環(huán)境。此外,我們還發(fā)現(xiàn)高技術(shù)領(lǐng)域中外資的知識(shí)溢出效果不明顯,這說(shuō)明國(guó)外公司存在對(duì)國(guó)內(nèi)企業(yè)技術(shù)封鎖和壟斷,在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的振興中,這一點(diǎn)恐怕也不會(huì)改變。這就需要國(guó)內(nèi)企業(yè)重視自主研發(fā),以自主創(chuàng)新為主,國(guó)際合作為輔,不斷研發(fā)具有自主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高端產(chǎn)品。
[1]段文斌.治理機(jī)制、行業(yè)集聚與國(guó)有工業(yè)部門(mén)績(jī)效變動(dòng)模式——國(guó)有企業(yè)改革30年反思和前瞻 [R].“反壟斷與政府規(guī)制:理論與實(shí)踐”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會(huì)議論文,2010.
[2]Jefferson,G.H.,Bai,H.,Guan,X.,Yu,X.R&D Performance in Chinese Industry[J].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2006,15(4):345-366.
[3]Schumpeter,J.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M].London:George Allen& Unwin,1942.
[4]Arrow,K.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A].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C].NBER,Princeton,1962.
[5]聶輝華,譚松濤,王宇鋒.創(chuàng)新、企業(yè)規(guī)模和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基于中國(guó)企業(yè)層面的面板數(shù)據(jù)分析[J].世界經(jīng)濟(jì),2008,(7):57-66.
[6]吳延兵.中國(guó)工業(yè)R&D投入的影響因素[J].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研究,2009,(6):13-21.
[7]周黎安,羅凱.企業(yè)規(guī)模與創(chuàng)新:來(lái)自中國(guó)省級(jí)水平的經(jīng)驗(yàn)證據(jù)[J].經(jīng)濟(jì)學(xué) (季刊),2005,(2):623-638.
[8]朱有為,徐康寧.中國(guó)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研發(fā)效率的實(shí)證研究[J].中國(guó)工業(yè)經(jīng)濟(jì),2006,(11):38-45.
[9]馮根福,劉軍虎,徐志霖.中國(guó)工業(yè)部門(mén)研發(fā)效率及其影響因素實(shí)證分析[J].中國(guó)工業(yè)經(jīng)濟(jì),2006,(11):46-51.
[10]Wallsten,S.The Effect of Government-Industry R&D Programs on Private R&D:The Case of the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J].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31(1):82-100.
[11]Lach,S.Do R&D Subsidies Stimulate or Displace Private R&D?Evidence From Israel[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2002,50(4):369-390.
[12]Greene,W.H.Econometric Analysis(6th Edition)[M].New Jersey:Prentice Hall,2008.354-397.
[13]Tirole,J.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M].Cambridge:MIT Press,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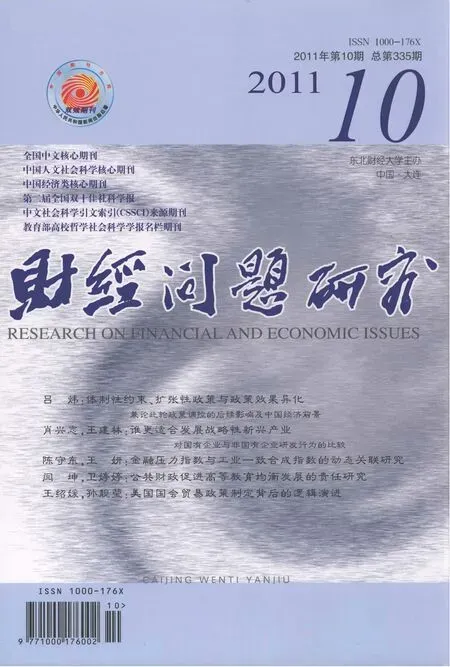 財(cái)經(jīng)問(wèn)題研究2011年10期
財(cái)經(jīng)問(wèn)題研究2011年10期
- 財(cái)經(jīng)問(wèn)題研究的其它文章
- 煤化工業(yè) “十二五”時(shí)期的產(chǎn)能過(guò)剩防范問(wèn)題研究
——基于山西、陜西和內(nèi)蒙古煤化工行業(yè)的調(diào)研 - 農(nóng)地資本化流轉(zhuǎn)與農(nóng)業(yè)投入研究
- 外資企業(yè)生產(chǎn)率與東道國(guó)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可持續(xù)性研究
- 跨國(guó)技術(shù)聯(lián)盟中文化差異與知識(shí)轉(zhuǎn)移績(jī)效研究
- 美國(guó)國(guó)會(huì)貿(mào)易政策制定背后的邏輯演進(jìn)
- 我國(guó)外商投資企業(yè)轉(zhuǎn)移定價(jià)避稅應(yīng)對(duì)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