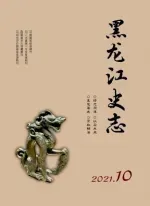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分析
王瀟冬
(魯東大學歷史與文化學院 山東 煙臺 264025)
中華民族凝聚力是中華民族賴以統一、獨立和生存、發展的內在動力。它包括三個有機組成部分,即“民族整體對民族成員(或民族個體)的吸引力,民族成員對民族整體的向心力,民族成員之間的親和力。”[1]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發展的歷史分析:
一、長期性
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多民族國家。這五千年歷史是各民族間遷徙、戰爭、融合的歷史。各民族間的遷徙、戰爭、融合,改變了特定地域民族的單一性,促成了不同民族的重新組合。這不僅促進了中華民族在血緣上的融合和形成,也促進了中華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形成,這樣的融合成為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一個重要途徑。這個過程十分漫長,我們稱之為長期性。
早在遙遠的上古時代,便出現了遷徙融合,比較著名的是三苗等部。原居住在兩湖一帶的三苗人,在戰敗后,被迫遷移至今甘肅、青海等地,也有的遷入江淮、洞庭等平原地區附近的山林谷地,發展為今天的苗、瑤、畬等民族[2]。在周朝,先秦的西戎由于戰敗,加入華夏行列。東夷,被西周兼并,遂逐漸融入華夏族。春秋戰國時期,原主要分布在今山西省境內的狄人通過一系列的侵擾戰爭逐漸漢化,融入華夏族。公元206年,曹操擊敗烏桓,并“悉徙其族居中國,”[3]內遷的烏桓人融入漢族,留居故地的烏桓人則鮮卑化,以后絕大多數又因鮮卑的漢化而加入漢族。至三國時期,五嶺以南地區的百越部分漢化,部分演變為今天的壯、瑤、黎等族的先人。南北朝以后,匈奴柔然這樣的民族實體也分化、瓦解。
隋時,鮮卑作為獨立的民族實體不復存在,融入漢等民族[4]。大部分氏人加入漢族,部分加入了南蠻、羌、吐谷渾等族[5]。唐時,6-8世紀稱雄于我國北方的少數民族突厥融為漢族成員。高句驪也在唐代消失,大部融入漢族,一部分成為新羅人,少數加入突厥,部分成為女真人,加入女真族的,在金亡之后又成為漢族成員[6]。到五代十國吐谷渾也是在此時期消失于歷史,大部分融入了漢等民族中,一支吐谷渾人則仍活躍于青海極其附近地區,成為今土族等族的先人[7]。公元1125年,契丹族所建立的遼王朝被女真族推翻,契丹族由此開始解體,逐漸融入了蒙古族、漢族、高麗族,有些則成為今青海省土族的成員[8]。公元1227年,西夏滅亡,黨項族也在歷史上消失,其民大多融入漢族,部分加入蒙古、藏等民族。公元1234年,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被滅,女真融入漢族、蒙古族,還有一部分保持女真稱號,成為后來滿族的先人[9]。元朝,蒙古人執掌政權,中華大地上到處散居著蒙古人,而元朝的迅速覆滅使得散居在各地的蒙古人未能北返,被迫留居當地,明朝的同化政策使絕大多數蒙古人融入漢族和其他民族。[10]明清時期,中國不管是在民族還是在版圖上,都已基本成型,與當代幾乎無異。
長期的民族融合強化了各民族的認同和依存關系,縮小了彼此之間的差異,客觀上增強了凝聚力。
二、承繼性
民族凝聚力形成是一個長期性的過程。在長期性的過程中,它又具有承繼性的特征,新興王朝吸收前王朝的精髓,摒棄前王朝糟粕,客觀上推動著民族凝聚力的不斷前進。作者認為,民族凝聚力作為意識流概念,體現在中國就是大一統思想的發展。
夏啟廢“禪讓”變“家天下”,建立了出具文明的國家。商在夏的基礎上,將周圍各國納入自己的統治,“一統天下”的思想在這時已處于萌芽狀態。周王朝繼承商的“余一人”[11]“唯我獨尊”的觀念,使“天下王有”“天下一統”的思想開始明朗豐富,而此時天下一統的觀念反映在民族問題上便是華夷一流。春秋大國爭霸,華夏諸侯認識到“攘夷”不可能,只有把華夷放在同一矛盾體中才能解決問題。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也主張國家一統。秦漢實現一統,經過多年的融合,發展了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漢族。以漢族為主體的秦漢帝國的許多政治體制和統治政策,促進了多民族國家內部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倫理等各方面的一統,“華夷一統”得到充分發展。經過兩漢四百多年的統治,大一統思想在魏晉南北朝的封建體制中已根深蒂固[12]。東漢末戰亂,少數民族乘機內遷,利用先進漢文化建立政權,實行漢化政策,促進各民族間的政治、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交流、發展,進一步加強了中華各民族間的內在聯系與密不可分的整體性。無論現實政治如何對立,在當時人們的心中已形成祖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樣的觀念。
隋唐初期的君主大都生長于少數民族和漢人雜居的關隴集團,因此他們在大一統思想的支配下,不區別對待少數民族,采取華夷同重的民族懷柔政策,“華夷一體”得到充分發展。宋是中國歷史上的又一次分裂時期,宋朝偏安,無力一統,因此宋的思想家們只能以“正統”取代“一統”,“正統”恰恰體現了無力“一統”的無奈,“一統”思想無可取代。與宋并存的遼、夏、金等北族王朝則仍在大一統思想的影響下進一步漢化。元朝統治者追求現實政權和思想文化的全面一統。元王朝擴大了中國的版圖,結束了民族間的對立,突破民族間的政治界限,將各民族置于大熔爐,促進了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也促進了思想上的共同認知。明代第一位君主朱元璋宣稱:“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間。”[12]這充分說明,中華整體觀念深入人心。清朝的統治者認定“無華夷之別、內外之分”,所謂的華夷,只是地域不同而已,無論何種民族以何種形式建立的“大一統”政權,都被視為“大一統”“正統”。經過漢、唐、元、明以來的民族融合和思想交流,中華民族在清朝升華成為一個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大一統思想和中華整體觀念深入人心,成為凝聚各族人民重要的精神力量。
各個王朝對于“大一統”的態度呈現出了上下承襲、連綿不斷、不斷豐富、不斷完善的發展趨勢,這種“大一統”思想的深入人心越深,人們心中的凝聚力越重。
三、時代性
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發展漫長、承繼,但這并不阻礙民族凝聚力在各個時期表現出不同的特性。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發展,在各個王朝都表現出了它獨有的時代特征。
夏商周時期,幾個部落聯合在一起,共同抗擊另一個部落的統治。這體現了當時社會背景下的一種簡單的民族聚合。春秋戰國時期,民族戰爭是民族聚合的特殊形式,春秋時,各國仍打著“一匡天下”的旗號進行爭霸戰爭,戰國,“王”已成為各國附庸,兼并、融合成為主流。經過長期的兼并、分化、吸收、統一,戰國七雄產生,七雄之間的戰爭是為了爭奪天下統一者的地位,這都從客觀上說明中原民族凝聚、民族一統的觀念深入人心。到了秦漢時期,時代性可概括為:和親中的凝聚。秦漢時期,中原國家一統之后,于少數民族的關系成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問題,與少數民族的和親在客觀上促進了民族凝聚力的發展。王朝較弱時,被動和親,息兵養民;實力足夠強大時,變主動和親,保持友好關系,促進民族在經濟、文化上的發展。魏晉南北朝的的時代性則可概括為:空前規模的民族融合。自東漢以來,匈奴、鮮卑、羯、氏、羌等邊疆民族大規模內遷,在北方地區形成各族錯處雜居的局面,內遷各族利用先進的漢文化建立政權,實行漢化政策,在北方地區出現了空前規模的以漢化為特點的民族大融合。
隋之后的王朝在承繼性中顯示了時代性。隋唐時期:開明的民族政策。宋朝:并存中的漢化。元:民族大熔爐。明清:注重文字效應的民族凝聚。清王朝的康雍乾三位圣主,不斷的以自己的理論,推崇大一統、中華整體的觀念,并以實際行動完成邊疆統一,建立起空前鞏固、空前統一的大帝國。
民族凝聚力的發展存在于各個王朝之中,每個王朝又對于凝聚力的發展起到了它獨有的促進作用,幫助民族凝聚力不斷向前、縱深發展,促使凝聚力在國家生存發展的關鍵時刻發揮其特殊的作用。
[1]孔慶榕等編.《中華民族凝聚力論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第11頁.
[2]參照王鐘翰主編.《中國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61—562頁.
[3]《三國志》卷30.《烏丸鮮卑東夷傳》.
[4]《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民族出版社,第279頁.
[5]《新唐書》卷222下.《南蠻下》;《資治通鑒》卷292.《后周記》三;《魏書》卷101,《吐谷渾傳》
[6]《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民族出版社,第313頁
[7]《新唐書》卷221上,《吐谷渾傳》;周偉洲《吐谷渾史入門》第28頁;王鐘翰主編《中國民族史》第211頁.
[8]后說據陳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65也上所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王鐘翰主編.《中國民族史》.第497頁.
[10]注:如忽必烈征云南,統10萬大軍前往,后留駐其地有2萬人左右。據杜玉婷、陳呂范兩位先生在《云南蒙古族簡史》中說,他們絕大多數在明初落籍云南后,為適應歷史環境,大多融入漢族,也有一些加入了其他少數民族.
[11]《尚書·盤庚》.
[12]《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民族出版社,第584頁.
[13]《明太祖實錄》卷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