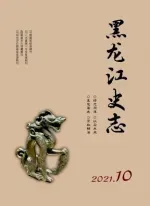新方志中的文體要求
鄒琳琳
(黑龍江省地方志辦公室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
在寫(xiě)這篇文章之前,借閱了許多資料,很多都談到了地方志中對(duì)文體和文風(fēng)的要求。下面就我個(gè)人所閱讀過(guò)的志稿,來(lái)加以理解新方志中對(duì)于文體的要求。
從資料上,我們可以了解到新方志的文體要求,是使用語(yǔ)體文和記述體。
語(yǔ)體文就是白話文,也是白話文的書(shū)面語(yǔ)言,它是現(xiàn)代漢語(yǔ)。歷代的志書(shū)都是用當(dāng)時(shí)的通用語(yǔ)體的,新方志當(dāng)不例外,也要用現(xiàn)代漢語(yǔ)的這種語(yǔ)體文。下面我就兩個(gè)問(wèn)題說(shuō)一下新方志中問(wèn)題的要求,一是方志文體的要求,一是與其他文體的區(qū)別。
一、方志文體的要求
方志是資料性著述,由于這一根本屬性,決定了它在行文表述上,有以下幾個(gè)突出的要求:
第一,記事要以時(shí)為序。
一般記敘文的述事比較自由,有多種方法,可正敘,可倒敘,可插敘,可補(bǔ)敘,但新方志中不能隨意使用這些方法,只能以時(shí)為序來(lái)進(jìn)行正敘,記事必須按時(shí)間先后,由古到近,由遠(yuǎn)到近,從發(fā)生、發(fā)展寫(xiě)到它的現(xiàn)狀。但是在很多志稿里就以插敘或者補(bǔ)敘的手法來(lái)記敘。
例如:《黑龍江省志·航運(yùn)志》(試寫(xiě)稿)中,第六章航道整治工程的一節(jié)里有這樣一段描述:“據(jù)1990年5月測(cè)量,航道水深不足4.0米,嚴(yán)重影響船舶滿載航行,江海兩用輪更是不能通過(guò)。這也是整治此段航道的主要原因之一。1989年,黑龍江省政府就此問(wèn)題向外交部申請(qǐng)治理航道。1990年2月,給予批復(fù)。”這里除了時(shí)間倒敘外,還有一個(gè)語(yǔ)病的問(wèn)題,我們暫且先不說(shuō)。
第二,述事要述而不論。
地方志是用資料說(shuō)話,只要把資料理順好了,道理也就說(shuō)清楚了。只要把實(shí)事講清楚了,觀點(diǎn)也就體現(xiàn)出來(lái)了。觀點(diǎn)體現(xiàn)出來(lái),對(duì)事物的褒貶也就清楚了。地方志記述的客觀歷史,不需要畫(huà)蛇添足地加以評(píng)頭論足,所以胡喬木說(shuō):“地方志不是評(píng)論歷史的書(shū),不是史論,多余的評(píng)論,不但不為地方志增光,反而為地方志減色。”
例一:民國(guó)時(shí)期,縣內(nèi)自耕農(nóng)僅占農(nóng)民總戶數(shù)的14.3%,少地或無(wú)地的農(nóng)民卻占85.7%。由此可見(jiàn),民國(guó)時(shí)期土地兼并之激烈。
上述例子中對(duì)事件敘述完后,加上了一句斷語(yǔ),便是畫(huà)蛇添足了。
當(dāng)然,述而不論也不是絕對(duì)不允許有一點(diǎn)評(píng)論的語(yǔ)言,這也不可能,必要時(shí)畫(huà)龍點(diǎn)睛地加一兩句評(píng)語(yǔ)還是必要的。既是畫(huà)龍點(diǎn)睛,就不能把龍身上全都點(diǎn)上眼睛。
第三,記述中要寓理于事。
什么叫寓理于事?就是通過(guò)對(duì)資料的記述,來(lái)說(shuō)明事物的興衰起伏、發(fā)展變化、因果關(guān)系、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和客觀規(guī)律,而不是通過(guò)說(shuō)教來(lái)表達(dá)這些內(nèi)容。不發(fā)議論,不搞虛構(gòu),不搞旁征博引,不搞合理想象,不進(jìn)行邏輯演繹,一切結(jié)論都是志書(shū)的讀者從資料的記述去取得,而不是靠我們直言相告。
例一:該年7月,全縣各鄉(xiāng)鎮(zhèn)有一萬(wàn)多人參加大煉鋼鐵運(yùn)動(dòng),采用土法冶煉,加之礦石低劣和原料不足,僅煉出質(zhì)量低下的生鐵500多噸,虧損2萬(wàn)多元,不得不于年底停產(chǎn)。
例二:通過(guò)土地改革,解放了生產(chǎn)力,提高了廣大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積極性,促進(jìn)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由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需要和農(nóng)民生活的提高,又促進(jìn)了縣屬工業(yè)的發(fā)展。
例一和例二截然不同,前者是寓理于事,后者是說(shuō)教。
二、達(dá)到這些要求的操作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用資料進(jìn)行困果排比。
例:20年代前,借山坡挖洞筑窯,以柴草燒制,每窯約三五百公斤。30年代,引入煤炭燒窯,產(chǎn)量大增,較大的窯戶年產(chǎn)可達(dá)3000余噸。1954年,石灰生產(chǎn)合作化。1958年改為國(guó)營(yíng)廠,建窯13座,年產(chǎn)石灰1.2萬(wàn)余噸。60年代石灰生產(chǎn)進(jìn)入低谷,社辦企業(yè)僅有二三處,各村子石灰窯停產(chǎn)。1971年后重點(diǎn)辦起7處石灰廠。1985年起發(fā)展迅速,1987年,全縣有石灰廠108處,年產(chǎn)石灰18萬(wàn)噸。
這一段志稿,就是資料充實(shí),數(shù)據(jù)具體,記事準(zhǔn)確,使事物的因果關(guān)系很自然地展現(xiàn)出來(lái),這是用資料進(jìn)行因果排比的結(jié)果。
第二種方法是用資料進(jìn)行對(duì)比的方法。
資料的對(duì)比,有事物本身的縱向?qū)Ρ龋灿信c其他事物的橫向?qū)Ρ取?/p>
例一:1952年,縣內(nèi)養(yǎng)豬由解放前的2萬(wàn)頭增至13.6萬(wàn)頭,形成第一個(gè)養(yǎng)豬高峰。1963年實(shí)行劃給飼料田的辦法,全縣生豬存養(yǎng)量達(dá)到14.8萬(wàn)頭,形成第二個(gè)養(yǎng)豬高峰。再后,為了發(fā)展養(yǎng)豬,又實(shí)行了一些優(yōu)惠政策,如給予工分補(bǔ)貼和現(xiàn)金獎(jiǎng)勵(lì)等辦法。1967年達(dá)30.6萬(wàn)頭,1973年上升到34.5萬(wàn)頭,1975年為42.2萬(wàn)頭,1980年為46.23萬(wàn)頭,形成第三個(gè)養(yǎng)豬高峰。此后,隨著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體制的變更,養(yǎng)豬補(bǔ)貼取消,每年生豬存養(yǎng)量保持在20萬(wàn)頭左右。
例二:地瓜歷來(lái)為膠南的主要糧食作物。建國(guó)前,全縣栽種40萬(wàn)畝,占糧播總面積的20%多。1955年增至50萬(wàn)畝,占糧播總面積的30%多。1966年后,地瓜種植面積擴(kuò)大,達(dá)到66萬(wàn)畝,占糧播總面積的39.65%。此后,小麥、玉米的種植面積不斷擴(kuò)大,地瓜面積逐步減少。1978年下降至39.51萬(wàn)畝,占糧播總面積的20%。1987年栽植25.7萬(wàn)畝,僅占糧播總面積的15.4%。
例三:1951年,全縣共審結(jié)離婚案件240件,占民事案件總數(shù)的78.43%。自1952年至1955年,共審結(jié)離婚案件1385件,年均277件,比1951年增長(zhǎng)15%。1961和1962年,因生活困難等因素引起案件增多,兩年共審結(jié)849件,占民事案件總數(shù)的93%。××年,共審結(jié)離婚案件1132件,占民事案件總數(shù)的31%。
上述例一為縱向?qū)Ρ龋⒗秊闄M向?qū)Ρ取?梢钥闯觯眠@種方法說(shuō)明事物發(fā)展變化和興衰起伏,確能達(dá)到彰明因果、體現(xiàn)規(guī)律的目的。
第三種方法是用點(diǎn)面結(jié)合的方法。
所謂面就是一般概況,點(diǎn)就是典型材料。點(diǎn)面結(jié)合是兼顧廣度與深度的方法,也是兼顧一般與個(gè)別的方法。記述事物,如果能用上好的典型材料,就會(huì)更加寓理于事。如有部縣志在記述該縣戰(zhàn)時(shí)支援前線的一般概況和各種數(shù)字后,又記述該縣在1947年粉碎國(guó)民黨軍隊(duì)重點(diǎn)進(jìn)攻山東時(shí),某村在青壯年全部在外支前的情況下,10多名老人組成運(yùn)糧隊(duì),推著小車(chē),隨部隊(duì)轉(zhuǎn)戰(zhàn)三天三夜,運(yùn)糧4800多斤。這些老人都在60歲以上,其中年齡最大的74歲。這幾位支前運(yùn)糧老人的故事,從側(cè)面說(shuō)明黨和群眾的魚(yú)水之情,也說(shuō)明我們的解放戰(zhàn)爭(zhēng)是一場(chǎng)人民戰(zhàn)爭(zhēng),其寓意是很深刻的。
三、志書(shū)文體與其他文體的區(qū)別
志體與其他文體的區(qū)別,只有通過(guò)具體事例的辨析,方可心領(lǐng)神會(huì)。
第一,志體與史論的區(qū)別。
方志是存史,史論是述史,二者的功能不同,寫(xiě)法也必然不同。志書(shū)是資料性的著述,它是通過(guò)記述資料而達(dá)到存史的目的,它不能象史論那樣,用大段文字直接來(lái)議論得失、分析因果、闡明規(guī)律、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乃至上升到理論。
例:經(jīng)過(guò)土地改革,廣大農(nóng)民分得了土地,農(nóng)村生產(chǎn)力有了提高,但終因工具不足,資本短缺,而無(wú)法進(jìn)行深耕細(xì)作,遇上自然災(zāi)害更無(wú)法抵御。為了迅速發(fā)展生產(chǎn),黨和政府引導(dǎo)農(nóng)民組織起來(lái),走互助合作道路,鼓勵(lì)農(nóng)民按自愿原則,開(kāi)展多種形式的互助合作。
這段分析不是不準(zhǔn)確,但只用議論和概念,而不記具體事實(shí)和數(shù)據(jù),就不是志書(shū)內(nèi)容,而是志書(shū)里的贅文。
說(shuō)到志書(shū)與史書(shū)的關(guān)系,附帶說(shuō)一下。古人論“史、志同源而不同體”,歸納起來(lái)有四點(diǎn)不同:第一點(diǎn)史縱志橫,史以時(shí)系事,志以類(lèi)系事;第二點(diǎn)史約志博,史縱述社會(huì),志橫列百科;第三點(diǎn)史遠(yuǎn)志近,通常說(shuō)隔代修史,當(dāng)代修志;第四點(diǎn)史論志敘,史重于探索規(guī)律,志重在記敘事實(shí)。
第二,志書(shū)文體與議論文體的區(qū)別。
議論文的顯著特點(diǎn)是論,運(yùn)用概念、判斷和推理,來(lái)表明作者的觀點(diǎn)和主張,它以說(shuō)理取勝,是以理服人的。議論文有三要素,即論點(diǎn)、論據(jù)、論證。論點(diǎn)提出要證明什么,論據(jù)回答用什么來(lái)證明,論證解決怎么去證明。
方志與之相反,它雖然要表明觀點(diǎn),但不是直接說(shuō)出來(lái),更不允許靠旁征博引,或引用權(quán)威的著作來(lái)論證自己的觀點(diǎn)。
例:計(jì)劃生育是我國(guó)的一項(xiàng)基本國(guó)策,有計(jì)劃地控制人口增長(zhǎng)速度,使之同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發(fā)展相適應(yīng),是直接關(guān)系到現(xiàn)代化建設(shè)速度和民族興旺的大問(wèn)題。
上例就是某部縣志關(guān)于人口的記述,這就不是志體,而是議論文體。
第三,志書(shū)文體與行政工作總結(jié)的區(qū)別。
總結(jié)一般是敘述經(jīng)過(guò),羅列成績(jī),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研究分析,然后提出改進(jìn)工作的措施。這種寫(xiě)法,也不符合志體的要求。
例:該廠的特點(diǎn)是:堅(jiān)持質(zhì)量第一,信譽(yù)第一,以贏得客戶的信任;堅(jiān)持全進(jìn)全出,進(jìn)多少料,出多少產(chǎn)品;堅(jiān)持科學(xué)管理,分工明確,工作有條不紊;自覺(jué)遵守各項(xiàng)政策,不走私,不套匯。
第四,志書(shū)文體與教科書(shū)的區(qū)別。
教科書(shū)、辭典、百科全書(shū)等,大多采用說(shuō)明文體,在文字中解釋定義、定理、公式、辭條等。
例:土地改革,是廣大農(nóng)村在建國(guó)初期,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土地改革法》和《國(guó)務(wù)院關(guān)于劃分階級(jí)的決定》,在黨的領(lǐng)導(dǎo)下,開(kāi)展規(guī)模宏大、斗爭(zhēng)激烈的土地改革運(yùn)動(dòng),用革命的方法,對(duì)土地等生產(chǎn)資料進(jìn)行重新再分配,取消地主土地私有制,實(shí)現(xiàn)農(nóng)民的土地私有制。
地方志不承擔(dān)概括全國(guó)性的一般政策的論述,而且地方志的知識(shí)性,也不是去解釋名詞或?qū)n}說(shuō)明。它的知識(shí)性,是表現(xiàn)在對(duì)本地資料的記述。
第五,志書(shū)文體與新聞報(bào)道的區(qū)別。
新聞報(bào)道包括消息、通訊、調(diào)查報(bào)告、新聞特寫(xiě)等,它的特點(diǎn)是時(shí)效性和政治傾向,而志書(shū)則要求思想性、科學(xué)性、資料性。
以記述會(huì)議為例,它的要素是時(shí)間、地點(diǎn)、人員、內(nèi)容、過(guò)程、結(jié)果等。新聞報(bào)道就要寫(xiě)得有氣氛,有色彩,有事例,洋洋灑灑,娓娓道來(lái),但志書(shū)卻寫(xiě)得非常簡(jiǎn)潔。
例:××縣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huì)第一次會(huì)議,于1967年7月26至30日召開(kāi),出席會(huì)議代表400名,缺席39名,列席代表14名。會(huì)議聽(tīng)取縣委政治報(bào)告、縣政府工作報(bào)告、財(cái)政預(yù)決算報(bào)告、縣人民法院工作報(bào)告,并通過(guò)以上報(bào)告的決議。會(huì)議選舉產(chǎn)生縣長(zhǎng)××,副縣長(zhǎng)××。
第六,志書(shū)文體與文藝作品的區(qū)別。
文藝作品是形象思維,運(yùn)用渲染和情感的文筆,進(jìn)行想象和構(gòu)思,塑造人物和事件。志書(shū)則是“其文直,其事賅,不隱惡,不溢美,謂之實(shí)錄”。
如有部志書(shū)記瞿秋白犧牲時(shí)對(duì)劊子手說(shuō):“共產(chǎn)黨人是殺不盡的!沒(méi)有共產(chǎn)黨人,革命不會(huì)成功!”據(jù)有關(guān)回憶錄記載,瞿秋白在犧牲時(shí)沒(méi)有慷慨陳詞,這些話是他平時(shí)對(duì)其妻說(shuō)過(guò)的,但志書(shū)作者憑想象力,把它們嫁接在一起,以顯示英雄本色。志書(shū)的記述是不允許這樣進(jìn)行藝術(shù)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