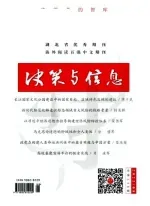世界網絡戰硝煙四起
文/滿凱艷 狄鑫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在《權力的轉移》一書中提到,世界已經離開了依靠暴力與金錢控制的時代,未來世界政治的魔方,將控制在擁有信息強權的人手里,他們會使用手中掌握的網絡控制權、信息發布權,達到暴力與金錢無法征服的目的。
走在世界政治經濟前沿的中國,自然無法避開這場新戰役,且不僅要攘外,更要安內。商戰在互聯網商業化20年之后,進入了轟轟烈烈的戰國時代。曾經為人類提供前所未有創業機會的互聯網,成為巨大的新戰場。
網絡戰爭將帶來什么
如果說工業時代的“戰略戰”是核戰爭,那么,信息時代的“戰略戰”就是網絡戰。
網絡戰爭會是什么樣?負責反恐和網絡安全的白宮前幕僚理查德·克拉克在他的新書中設想了十五分鐘之內造成的災難性破壞:計算機病毒讓軍方的郵件系統癱瘓;造成煉油廠和輸油管道爆炸;空中交通管制系統癱瘓;貨運和城市鐵路列車出軌;金融數據被涂改;美東電網斷電;軌道衛星運轉失控。隨著食物緊缺,資金鏈斷裂,整個社會很快分崩離析。最糟糕的是,攻擊者的身份一直成謎。
IT行業的安全專家布魯斯·施奈爾則表示,在未來戰爭中,網絡空間肯定是戰場之一,但除非是在真正的戰爭環境中,否則要對美國施行毀滅性攻擊從技術上來說困難重重,也不符合常理,而如果真正的戰爭爆發的話,攻擊者可能是顯而易見的。
對高層領導來說,計算機技術是一柄雙刃劍。炸彈可以由GPS衛星導航;飛機可以通過遠程遙控飛行全世界;當今的戰斗機和軍艦本身就是巨大的數據處理中心,即使是普通的步兵也在上網。但是不斷增加的互聯互通和不安全的互聯網,讓電子攻擊的手段不斷翻新;對計算機的日益依賴也增加了它們可能造成的損失。
網絡武器的神秘面紗
網絡武器和核炸彈一樣,存在并不代表要使用。而且,攻擊者不能確定攻擊行為會對另一個國家造成怎樣的影響,這就使得他們的攻擊部署存在很高風險。對先進的軍事力量(如美軍)而言,這樣的不確定性是網絡攻擊的一個缺陷,但恐怖分子和流氓國家的軍隊對此就無所謂了。網絡攻擊也帶來了網上犯罪和間諜活動的危險。
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危險的不穩定趨勢。網絡武器正被秘密研發,誰都絕口不談將在何時,怎樣使用它們。沒人知道它們真正的力量,所以國家必須為最壞情況作打算。網絡的匿名屬性也增加了錯誤、錯認和失算導致軍事力量在常規武器或太空武器上升級的風險。網絡戰發動很快,且偏好先發制人的攻擊方式,幾乎沒有時間留給你冷靜應對。即使計算機輔助武器系統和信息化步兵已經吹散了一些戰場上的迷霧,網絡武器依然給網絡空間罩上了一層厚厚的危險的不確定性毯子。
網絡武器在大國手中使用起來最為有效。但是它們因為價廉物美,對相對弱勢的一方來說更有用,同時它們也很適合恐怖分子使用。幸運的是,類似于基地組織這樣的恐怖團體看起來主要是用互聯網進行宣傳和通訊,可能是缺乏讓煉油廠自爆的技術能力,或許他們更喜歡用自殺性炸彈制造血腥場面,而不喜歡電腦破壞這樣的匿名行動——至少現在還是如此。
各國正組建網絡戰機構
奧巴馬已經宣布,美國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屬于“國家戰略資產”,并任命國家安全局局長基思·亞歷山大將軍擔任新成立的網絡司令部的領導。英國也建立起了一整套網絡安全政策體系,和總部設在英國國家通訊總部(GCHQ)的“行動中心”,GCHQ相當于美國國家安全局。中國在討論“如何到21世紀中期打贏信息化戰爭”。許多國家也在組建各自的網絡戰機構,包括俄羅斯、以色列和朝鮮。伊朗自稱已擁有了全世界第二大的網軍。
與傳統軍隊相比,網軍有什么不一樣?全部由黑客組成嗎?雖然中國國防部前不久剛剛公開確認,為提高部隊的網絡安全防護水平,解放軍廣州軍區組建了專業的“網絡藍軍”,但是關于網絡部隊的詳情,并未有確鑿詳盡的信息。在這一方面,喜歡大張旗鼓鼓吹網絡戰的美國或許倒可以成為我們的參考。
1995年,美軍就有16名“第一代網絡戰士”。到目前為止,美國已擁有最大的網絡戰力量,三軍都有網絡部隊。據防務專家喬爾·哈丁評估,美軍共有3000-5000名信息戰專家,5萬~7萬名官兵涉足網絡戰,規模相當于7個101空降師。
美軍大張旗鼓地組建網絡戰司令部,實際上是承認美國已擁有越來越多的網絡戰武器,并為未來使用這些武器制造輿論。在軟殺傷網絡戰武器方面,美國已經研制出2000多種計算機病毒武器,如“蠕蟲”程序、“特洛伊木馬”程序、“邏輯炸彈”、“陷阱門”等。在硬殺傷網絡戰武器方面,已研制成或正在發展電磁脈沖彈、次聲波武器、激光反衛星武器、動能攔截彈和高功率微波武器,可對別國網絡的物理載體進行攻擊。
網絡竊密是最大的情報災難
傳統的間諜人員冒著被捕或死刑的風險想方設法將文件副本偷運出境。但是那些網絡空間中的間諜就沒有這樣的風險。“一名間諜一次可能拿走相當于幾本書的材料,”一名高級美國軍方人士說,“現在他們可以把整個圖書館偷走。而且如果你把書又重新上架了的話,他們還會再來偷一遍。”
“自從1940年代后期丟失過核機密以來,網絡竊密是最大的情報災難。”總部在華盛頓的智庫戰略與情報研究中心(CSIS)的吉米·路易斯說。間諜可能是西方面臨的最直接的威脅:失去高科技技術可以讓西方逐漸喪失經濟領先優勢,如果真的置身于戰爭之中,竊密可以削弱其軍事優勢。
西方的間諜認為中國部署了最勤懇的和最無恥的網絡間諜。但是俄國間諜在技術上可能更熟練,也更狡詐。間諜們說,在這一軍團中,首當其沖的還是美國的國家安全局和英國的GCHQ,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西方國家直到最近都不愿意大聲譴責計算機竊密。
網絡犯罪就是網絡戰爭
互聯網的設計目標是方便和可靠,而不是安全。而通過全球網絡化,鮮花和野草良莠不齊地同時出現了。網絡空間無需護照。警察們被限于國界之內,罪犯卻可以逍遙自在地四處漫游。
奧巴馬稱,去年因網絡犯罪造成的損失接近1萬億美元,盡管這一數字存在爭議,但卻是一個比毒品交易的金額還要龐大的秘密世界。銀行和其他公司不愿意承認丟失了多少數據。2008年,在為客戶進行的調查中,區區一家電信公司Verizon就報告丟失2.85億條個人信息記錄,包括信用卡和銀行帳號等細節。
更令人擔憂的是,網絡犯罪和網絡戰爭間的界限現在是很模糊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些國家將網絡犯罪組織視為有用的聯盟。一些國家已經表現出他們愿意容忍,支持甚至引導犯罪組織和市民去攻擊敵對目標。
在格魯吉亞的網絡攻擊案例中,就有這樣的情況,市民在俄羅斯軍隊從陸地和空中入侵格魯吉亞的同時,發動了針對目標的網絡攻擊。專家認為,網絡攻擊事件與軍方行動如此協調,顯示出在市民網絡攻擊者中與俄羅斯軍方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
“許多網絡戰爭的挑戰都在網絡犯罪中體現出來,因為國家和網絡幫派都使用同樣的工具。”按照一名德國網絡犯罪研究人員的說法,“比如說,任何人都可以去向犯罪組織租用一個僵尸網絡,我們甚至可以做到,只要你有錢就可以產生破壞,而不需要知道如何做或者這其中有些什么需要被跟蹤。”
網絡軍備競賽已經開始
由網絡安全公司McAfee發表的“虛擬犯罪報告”稱,國際間軍備競賽已經移師互聯網。
據白宮前顧問保羅·庫爾茲(Paul Kurtz)稱,法國、以色列和中國都擁有網絡武器程序。他在采訪了20多位專家后得出的結論與上述報告相同。
McAfee公司總裁戴夫·戴爾特(Dave Dealt)說:“我們從兩年多以前就開始預警全球性的網絡軍備競賽,但現在我們找到很多證據表明,競賽已經開始。”
除了美國,俄羅斯、日本、法國、德國、印度等國家,甚至臺灣地區,都已經把網絡戰的部隊建制化、編制化。北約正討論網絡戰要達到何種程度才能被認定為是某種“武裝攻擊”的形式,從而責成其成員國提供作為盟友的幫助。
相比于二戰之后蘇聯和美國之間的武器軍備競賽來說,狀況有些不同,國家間正在進行著建立網絡武器方面沉默的軍備競賽。如果將前者視為決斗,那么網絡武器競賽相對來說可能更加像自由競賽。
戰略和國家關系研究中心的前技術領導人吉姆斯·里維斯不認為已經見到了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戰爭,但是他相信網絡戰爭風險正在加大。他說:“網絡戰爭現在不會爆發,但是國家間的競賽已經毫無疑問地在運行,網絡武器存在,而且我們可以預見到敵人也許會使用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