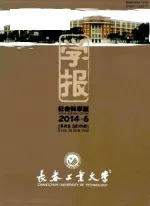建立假冒偽劣行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
蘭德旭
(1.吉林大學 經濟學院,吉林 長春130012;2.吉林省長春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吉林 長春130061)
建立假冒偽劣行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
蘭德旭1,2
(1.吉林大學 經濟學院,吉林 長春130012;2.吉林省長春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吉林 長春130061)
懲罰性賠償制度,是指由法庭判處的被告賠償數額超出原告實際損害的賠償。本文從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由來進行分析,指出了我國現階段假冒偽劣行為的特殊性,從對制假的威懾、保護市場交易功能、鼓勵提高產品質量及激勵消費者參與打假四個方面分析了建立我國假冒偽劣行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我國建立該制度應該與提高產品質量、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調動消費者積極性、打擊與引導相結合的四點建議。
懲罰性賠償制度;法經濟學
一、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由來
懲罰性賠償在英美法中通常被定義為,當被告的行為是輕率、惡意、欺詐時,判處的超過實際損害的損害賠償。從語源學的角度看,懲罰性賠償概念的本質在于超過實際損害賠償之外的“附加性”賠償,它是法官判決由被告給付原告數倍于其實際損害的損害賠償。一般地認為,懲罰性賠償是在被告人故意侵權或有逃脫責任機會情況下,為達致適度威懾的目的,在被告人承擔補償性賠償責任的前提下,根據其非法獲利或逃脫責任幾率而額外承擔一定金額的損害賠償。
懲罰性賠償的觀點與實踐淵源于古代法。早在公元前1894年,《漢謨拉比法典》就有關于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在中國古代,也有相當數量的懲罰性賠償的規定。例如,漢代的“加責入官”之制,《唐律》和《宋刑統》的“征贓”,直至《大明律》中對收受和使用假幣給予的懲罰性處理,都具有濃重的行政懲罰色彩,但其加倍征收的款額是收歸國庫,并非作為對受害方的賠償。
17世紀至18世紀,英美法中的懲罰性損害賠償主要適用于誹謗、誘奸、惡意攻擊、私通、誣告、不法侵占住宅、占有私人文件、非法拘禁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譽損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至19世紀中葉,懲罰性賠償已被法院普遍采納。自19世紀以來,懲罰性賠償不僅適用于侵權案件,也適用于合同案件。懲罰性損害賠償轉向制裁和威懾不法行為,而主要并不在于彌補受害人的精神痛苦。進入20世紀,隨著大企業的蓬勃興起,各種不合格商品導致對消費者損害的案件頻繁發生,但由于大公司財大氣粗,僅靠對消費者進行補償性賠償難以對其非法損害行為起到威懾作用,于是懲罰性損害賠償遂逐漸適用于產品質量責任,同時賠償的數額也不斷提高。
我國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首次提出了加倍賠償,2008年《食品安全法》第一次提出了假一賠十的規定,2009年底出臺的《侵權責任法》中在產品責任一章中明確規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這是我國第一次以立法的方式明確了懲罰性賠償制度。
在正常情況下,以產品責任為基礎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應產生在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發達的社會中,以產品缺陷為前提。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企業現狀,還不具有實行這種正常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經濟基礎。在我國最應該嚴厲打擊的,社會矛盾最突出的不是正常的產品缺陷,而是假冒產品,人們對此也深惡痛絕。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目前最需要的是建立對營利性故意侵權和假冒偽劣行為的懲罰性賠償制度,這也是國務院正在研究考慮的問題。
二、建立假冒偽劣行為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
我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假冒偽劣產品盛行,屢打不絕,屢禁不止,這與現行法律對產品責任損害賠償金的相關規定有很大關系。我國現行的有關產品責任制度的基礎都是基于產品缺陷,而產品缺陷一般產生于正規廠家。基于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條件,不可能讓普通生產商承擔更大的賠償責任,因為責任加大,意味著成本提高,產品價格上漲,而正是這種善意的立法平衡被假冒產品鉆了空子,導致制假售劣的泛濫,最終由整個社會承擔損失。建立假冒偽劣行為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堵塞法律漏洞的現實需要:
1.建立假冒偽劣行為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對制假售假行為的有力威懾。經濟學認為,人類行為具有一種理性模式,人總是很理性的從事行為,當被威懾的人在決定從事或不從事某一行為時,他會依據理性權衡該行為的利弊得失。因此,通過懲罰性賠償金就會對行為人產生威懾。建立假冒偽劣行為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可以實現法律制度的預防功能和教育功能,通過遠遠高于實際損害的懲罰性賠償這一懲罰制度,達到威懾的目的,使制假售假者不敢以身犯險,從而維護社會利益。而一般補償性損害賠償根本無法威懾和遏制生產者或銷售者從事制假售假不法行為。因為生產者制假獲利必然遠遠大于其損害賠償責任,而只有超過實際損害賠償的懲罰性賠償金,才能夠威懾產品生產者從事類似的不法行為。用法的經濟學分析的觀點來分析,就是懲罰性賠償將給不法行為人在經濟上增加負擔,而這種負擔就是不法行為人為其行為所付的代價。這種代價將遠遠高于其制假獲利的風險,這樣能過威懾達到制假者自動不敢制假的目的。
同時,通過對某個不法行為人負有懲罰性賠償而承擔責任的判決,還可以遏制其他人犯類似的錯誤。當懲罰性損害賠償加于某個不法行為人的時候,便同時向社會輸送了一種約束性信息,使廣大社會成員了解到不法行為的性質、危害和法律后果,從而使他們在以后的活動中注意避免類似的行為。在故意侵權和假冒偽劣行為情況下,補償性賠償不能抵消侵權人的非法獲利或不能完全補償受害人所受傷害,而適用懲罰性賠償可以達到最佳威懾狀態,因為對損害的不完全補償會使潛在的受害人對此類侵害行為采取消極預防。而由于并非所有的受害人都提起訴訟,法院適用懲罰性賠償,可以讓侵害人承受其行為的社會成本,即“社會成本的內在化”。從犯罪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一流的違法者就是用最小的違法犯罪成本獲得最大的違法犯罪收益,而政府所須采取的措施便是通過一系列社會公共政策(包括法律)使違法者的違法犯罪成本最大化。最后達到減少違法犯罪率的目標。英國經濟學家貝克爾在其名著《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中提出,對付違法犯罪行為的最好的公共政策就是提高違法犯罪成本,使違法犯罪“不合算”。
2.建立假冒偽劣行為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交易功能的保護。市場經濟是指生產各要素通過市場的自由交易來配置。對侵犯他人財產權的非自愿交易施之以懲罰性賠償的懲罰,可以營造自愿交易的市場環境。懲罰性賠償可以使潛在侵權人認識到交易比侵權合算,激勵潛在侵權人進行交易。根據科斯定理,在補償性賠償金低于侵權人非法獲利而又不能完全補償受害人損失情況下,一個潛在侵權人就會從事侵權行為,而潛在的受害人則會將盡可能防止侵權行為的發生,考慮通過購買使潛在侵權人放棄侵權行為。這顯然不符合社會利益的需要,事實上這種支付因為不存在交易機制也不可能發生。但如果賠償金太低,潛在侵權人會過分從事損害行為。
3.建立假冒偽劣行為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對提高產品質量的正面鼓勵。從法的經濟學角度來看,法律責任制度不過是定價制度而己。當侵權成本與侵權收益相當時,侵權人有可能無所顧忌地實施侵權行為。引入了懲罰性賠償制度,就提高了違法成本。現實生活中,一些假冒偽劣行為者為了追逐高額利潤,追求低成本,進而進行制假售假。建立懲罰性賠償機制,不僅是對被仿冒產品的保護,也督促假冒產品生產者提高產品質量,生產自己品牌的產品,從而消滅假冒偽劣產品的產生土壤。
4.建立假冒偽劣行為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對廣大消費者抵制制假售假行為的激勵。目前針對假冒偽劣行為的主要手段是行政處罰,其中主要是罰款,而罰款并非用于補償受害人,而是上交國庫,作為直接受害的消費者個人沒有直接從行政處罰中得到補償,削弱了與假冒偽劣行為作直接抗爭的受害人的積極地位。而懲罰性賠償金是賠給原告的,這就為廣大消費者實施法律提供了動力。至于訴訟成本的問題,如果按照傳統民法理論的觀點,賠償全部損失固然重要,但并不能消除廣大消費者打得起官司賠不起精力的顧慮。“損一賠一”雖然在理論上能夠使消費者的損失得到賠償,但是消費者出于上述種種顧慮,未必愿意與假冒偽劣產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論個清楚”、使自己的損失得到實際賠償。通過懲罰性賠償可以鼓勵受害人為獲得賠償金而提起訴訟,揭露不法行為并對不法行為予以遏制。雖然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并沒有降低訴訟成本,但在某種意義上說,因其增加了效益,而使成本相形之下降低。在立法上創造更大的消費者參與空間,調動廣大消費者與假冒偽劣行為作斗爭的積極性,可以提高法律的實效。政府獲取違法行為相關信息的能力及其用于監管的資源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建立假冒偽劣行為的懲罰性賠償制度這種方式來動員廣大的受害人來參與監控,利用民事賠償的方式來懲治違法行為。這樣可以形成一股巨大的社會監控力量,甚至可以起到限時監控的作用。這是政府執法所不具有的,至少也可以彌補行政執法的不足。
三、建立我國假冒偽劣行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幾點建議
一是與提高產品質量相結合。建立假冒偽劣行為的懲罰性制度的目的是消滅假冒偽劣產品。打假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最根本的是要提高產品質量。對假的懲罰本身也同時是對真的鼓勵,一方面為正品企業維護市場環境,讓正品能夠在市場存在并得利。為企業積極改進工藝、嚴格管理,生產正品提供動力。同時也是對制假企業頭上加懸的一把利劍,如果利令智昏,利欲熏心而敢于制假,則要付出巨大代價,這本身也是讓制假企業轉向正道。
二是與行政處罰刑事處罰相結合。懲罰性賠償制度是一種民事賠償制度,并且在實踐中是一種事后制度。作為一種遏制假冒偽劣行為的手段還應與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相結合。行政處罰是一種主動發現,可以有效避免后果的產生。而對于假冒偽劣行為造成嚴重后果,致人傷亡的,僅有民事賠償顯然是不夠的,這就需要刑罰來制約。這樣民事、行政、刑事相結合,有利于結成一張遏制假冒偽劣行為的網。
三是與調動消費者積極性相結合。在中國,實施法律的巨大的人力資源在民間。雖然各級政府機關特別是產品質量監督機關努力工作,但是他們畢竟人力、才力有限,不可能把所有事情辦好。與行政罰款和刑法上的罰金不同,懲罰性賠償金是賠給原告的,這就為廣大消費者實施法律提供了動力。懲罰性賠償制度是一種民事訴訟制度,也就是說是不告不理的,一個制度的建立要是沒有實際實施,那就等于一張紙,并有實際效果。所以,建立我國假冒偽劣行為的賠償制度時要考慮方便消費者訴訟,為消費者提供便利,在起訴要求、證據及賠償數額上都要向消費者傾斜。這樣才能調動消費者的積極性,打一場消滅假冒偽劣行為的專業戰變為人民戰爭,則無往而不勝。
四是打擊與引導相結合。有人主張對假冒偽劣行為實行懲罰性賠償就是要使造假者被罰個傾家蕩產,而不敢去造假。筆者不認同這種看法。每個人都是社會中的人,且不說造假者在社會中有某些官員庇護,使假冒偽劣行為屢打不止。在不排除造假者有企圖謀求暴利的同時,也應該看到,也要給一些制假售假者一些社會出路,要注重打擊與引導相結合。打擊是一個臨時手段,根本解決問題還在于引導,即堵與疏的關系。
[1]王利明.美國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J].比較法學,2003,(5).
[2]李珂,馮玉軍.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法經濟學分析——兼論中國《消法》第49條的法律適用[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4).
[3]劉孫麗.建立我國產品責任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研究[D].南寧:廣西大學,2007.
[4]〔美〕貝克爾.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M].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蘭德旭(1968-),男,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吉林省長春市質量技術監督局,主要從事法經濟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