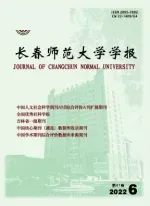從認知語用推理維度審視言語交際中的語境思維
李 爽
(江蘇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外國語言文學系,江蘇無錫 214153)
語境在認知語言學中主要指語用者通過經驗把具體的語境內在化和認知化后,存在于語用者自身的語用知識。語言除了字面意思外還包含交際意義,聽話人需要根據認知語境進行認知語用推理,即:語言傳出者在傳出語言交際意義前,已根據語言接受者可能的認知語境,進行了逆向的認知語用推理。下面我們對《紀念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這篇文學作品中的時空交錯進行分析,以此解讀語用推理對語言超載信息的理解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認知語用推理機制:用語用推理解讀語言接觸中的深層思維
語言是人類形成和表達思想的手段;思維是人腦對客觀事物能動的、間接的和概括的反映。思維與語言雖然是兩種機制,卻是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根據英國哲學家和邏輯學家格賴斯的語用推理模式,交際者傳遞某一思想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接受者明白他的意圖,語用學的中心任務就是解釋這些刻意的交際意圖是如何被推導出來的。語用推理是一個錯綜復雜的認知心理過程,它包括各種語境信息的搜尋和激活、一次或多次的推理過程以及結論的驗證等。其實,人們之所以能在信息不完備的前提下進行推理并獲得合理的認識,就是因為利用了已有的知識和經驗。這種以默認前提或常識為基礎的推理,一般是自動的、無意識的、無需刻意作出努力的思維過程,從而使人們在瞬間作出判斷和推理成為可能。人們交際的目的不是尋求最大關聯,而是尋求最佳關聯,即受話人以最小的信息處理努力獲得足夠的、最佳的語境效果。在這一明示——推理的認知過程中,關聯理論為語用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統一的理論框架。
本文重點分析關聯理論的語用推理特征,即關聯理論這一語用學理論主要研究信息交際的推理過程,尤其注重語言交際的話語解釋原則。從關聯理論的角度來探討篇章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語篇建構過程和語言信息處理行為,從而更好地指導閱讀理解實踐。本文在概述關聯理論核心內容的基礎上,以威廉·福克納的短篇小說《紀念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下文簡稱《玫瑰花》)為范本,從敘事學的角度,著重分析這篇小說在敘事中時間與空間刻意交錯與互補的特征,以及這一特征對于表現小說主題的特殊意義,并由此從時空維度來分析關聯理論與語篇分析的關系,論證語篇分析是一個讀者和作者交流的過程,語篇分析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獲取作者所表達的話外意圖 (交際意義);語篇分析的實質是推理,是一個讀者利用自己的百科知識、邏輯知識與詞匯知識對新信息進行加工處理的過程;語篇分析是一個讀者與作者尋求最佳關聯的過程,所依賴的語境是一個動態的并且是相互作用的心理構建,并以此來探討如何通過語境來尋找關聯、進行語用推理來正確理解語言,進而增強局部連貫和整體連貫的意識,深化將語篇連貫理論和方法滲透到閱讀與寫作教學中去的思想內涵。
二、背景知識的激活與連貫性的保持:用最佳關聯解讀敘事時空的交錯與互補
1.以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的交錯解讀語用推理是語言交際的核心
Sperber和Wilson的關聯理論把交際看作一種有目的、有意圖的人類活動,是一個明示—推理的認知過程。明示是對說話人而言的,指的是說話人明確地向聽話人表示意圖的一種行為;推理是對聽話人而言的,指的是聽話人通過明示手段所提供的信息推斷出說話人的意圖。語言交際活動涉及兩種意圖:信息意圖和交際意圖,也就是說,說話人說話時不僅表明他有某種傳遞信息的意圖,更要表明他有傳遞這種信息的意圖。
因此,交際過程不僅僅是單純的編碼—解碼過程,還是對話語和語境信息的動態推理過程。推理是獲取隱含意義的主要方式,它根據語言手段或非語言語境獲取有關話語內容的邏輯結論。在特定語境條件下,聽話人需要形成一定的假設才能理解說話人的意圖,一方面,形成假設的過程是人們推理的過程,也就是一個依賴語境因素的認知過程;另一方面,語境必須結合交際事件的社交因素。在任何一部敘事作品中必然會涉及兩種時間,即故事的時間與敘事的時間 (文本的時間)。傳統小說中,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基本呈重合狀態,事件的排列猶如串好的糖葫蘆,清晰而有序,即使偶有插敘和倒序也不影響直線而下的順利閱讀。想用和故事實際發生的時間來描述敘事文本的時間跨度是很難做到的,任何人都無法回避這一客觀限制,然而《玫瑰花》卻用短短的幾千字就展現了愛米麗小姐近半個世紀的生活。小說共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開頭采用了法國學者熱奈特提出的“時間倒錯”的手法,直接概述愛米麗小姐的葬禮,然后又將目光推回“1894年某日”鎮長沙多里斯上校豁免了愛米麗的一切稅款。但是后來“思想開放的”第二代鎮長和參議員因對這項安排不滿而打算登門訪問。從中不難看出作者在沙多里斯和第二代鎮長就任之間的時距上采用了省略的手法,其敘事時間為零。這中間究竟隔了多少年,愛米麗小姐發生了哪些事還無從得知。但當參議員們正式訪問愛米麗家時,卻插入了一句“自從八年或者十年前她停止開授瓷器繪畫課以來,誰也沒有從這大門出入過。”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參議員的拜訪應是在開授瓷器彩繪課之后,即“八年或十年前”這段本該在前的故事時間被穿插進了作品的敘事時間。與之相同的還有第二部分中當鎮上的人們處理完愛米麗家的“異昧”事件后,出現了一個“內倒序”,即以鎮上人們的視角轉入了對愛米麗父親生前與死時愛米麗境況的回憶。這種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相互交雜的情形不僅在每個單獨的部分中頻頻亮相,而且在每部分間的銜接上也被巧妙地加以利用了。如第二部分開頭就并未緊扣第一部分末尾展開敘述,而是猛然將鏡頭拉回了30年前。讀者所期待的敘事時間被中斷而又回到了往昔的故事時間。諸如此類的插入式回憶與正常的故事邏輯不斷沖擊碰撞,迫使我們以跳躍的眼光和非直線型的思維參與揉和到作品中。雖然小說里的時間“線條不是筆直的,而是依據一定的思路將看似不相關的東西串起來”的“一種主觀認知和感情的產物”,但人類需要意義,而意義取決于連貫性,并且時常產生于某種一連串同質成分組成的完整無缺的線條之中,所以無論先后以及出現的東西多么雜亂無章,人們都會試圖在其中找出某種秩序,在秩序中發現各自的意義。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認知腳本的激活不僅依賴于話語中的語詞,更為重要的是依賴于語境假設的確立,依賴于交際者的認知語境。
2.以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的互補解讀語境關聯是話語理解的理據
語言交際是一個認知過程,這個過程是靠明示推理來進行的,并受關聯原則的支配。在交際的過程中,每個交際行為都傳遞有最佳關聯的假設,即說話者總是通過話語提供具有最佳關聯的假設,話語理解則是一個通過處理話語找出最佳關聯解釋的推理過程。波蘭美學家羅曼·英伽登在談對文學作品的認識的時候曾提出“不定點”的概念。“不定點”正好符合Sperber和Wilson的關聯理論,即言語交際涉及說話者和聽話者雙方對話語信息的處理:說話者通過明示交際行為,為聽話者理解話語提供一定的相關信息和認知語境,讓聽話者獲取某種信息;而聽話者對話語的理解,是經對方的明示信息激活有關的認知語境,而努力尋找關聯,并進行推理以明白對方的交際意圖,從而獲得語境效果。而正如本文剛才的分析,因為敘事與故事時間的雜糅似乎造成了時間的中斷和情節的流失,但作家設置的若干個“不定點”并未成為懸而未決的無頭公案,而是在某一小節的敘述中再次展開,不著痕跡地互相補充說明,填補了空白。如第一部分中愛米麗開授瓷器繪畫課一事雖一語帶過,但到第四節中又出現了對同一事件的更為詳細的描述,使我們對女主人公有了更全面的了解。開授瓷器繪畫課是愛米麗孤寂封閉的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是關于愛米麗故事的重要一幕,雖然故事的帷幕在第四節中才正式拉開,但這也恰是對開頭部分零敘事時間的照應和補充。比較明顯的例子還有第二部分開頭略微點到愛米麗的心上人拋棄了她,但下文卻將這頗能引起讀者興趣的信息拋到了九霄云外,鋪開了對“異味”事件的敘述。而當我們尚沉浸在這一片“異味”的迷霧中時,作者在第三部分卻又回到了幾乎被人們忽略的“心上人”身上。至此,這一消息性聯結因素才向我們揭開神秘的面紗。于是,荷默·伯隆這個新的人物浮上水面,又牽連出新的關系和事件。由此,在福克納那里,“葫蘆串”的主軸已經斷裂,甚至還橫生出許多“枝節”。而這一個個滾落的“糖葫蘆”已成為散在的存在,需要我們的大腦重新賦予其秩序,這種看似混沌一片的布局卻更能引起讀者的注意和思索。所以小說中的一些事件以不同面貌較高頻率地重復出現不是沒有意義的。也就是說,在實際的言語交際過程中,為了準確理解話語標記語的制約性,我們就很有必要依據一些語言手段解碼話語信息,積極尋找關聯,以達到推斷語篇內容的目的。
3.以時間與空間的互補解讀認知語言學和關聯理論所共同關注的中心議題之一是語用推理
篇章分析是對語篇的理解,它是一個積極主動的建構過程,需要讀者通過從文字中獲取信息并進行加工而獲得有效信息。在這個過程中,讀者根據最佳關聯的原則把分散于篇章中的各種信息整合與聯系起來,經過必要的判斷、推理,尋求話語與語境的最佳關聯,在認知語境的作用下取得話語的交際意義。也就是說,通過語用推理建構一個篇章的意義是讀者與篇章不斷進行交際活動的結果。讀者把新知識和舊知識聯系起來,在對詞匯意義的解碼的過程中,實現對篇章的全面理解。可見語篇分析的實質是一個判斷、推理、歸納、總結的過程,是讀者根據最佳關聯的原則在認知語境的作用下通過推理取得話語的交際意義的過程。在交際時,雙方的認知語境要形成互明,說話者要根據他對聽話者認知語境作出的假設,選擇合適的語言形式。
《玫瑰花》中不乏對“濃縮在空間中的歷史時間”的出色運用。對于小鎮上的人來說,時間從其對愛米麗一家有記憶起直到她去世始終是自然地向前推進的。“我們”看到愛米麗小姐逐漸“發胖”,“頭發越變越灰”,唯一服侍她的黑人“頭發變白了”,“背也駝了”;然而與時間的洪流格格不入且頑強對抗的因素依舊“巋然獨存”。對于愛米麗小姐來說,時間已然凝固和凍結。70多年來,她幾乎完全封閉于那間“19世紀70年代風格”的房子里。在這“光線陰暗”,“空氣陰濕而又不透氣”,包著笨重家具的皮套子“已經坼裂”的空間里還有一個更為隱秘的小房間,荷默·伯隆的尸體在那兒躺了40余年。愛米麗用砒霜將他毒死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每晚都與這具尸體同床共眠。這幢大木屋就是一種特殊的時間形式,是“過去”插于“現在”之中的象征。愛米麗身上那似乎因停滯而失去了的時間正是在這一屋子中找到了存在的證據。
小說的五個部分中,時序來回顛倒,故事懸念迭出,時間被割裂又被重新拼貼得天衣無縫。福克納正是要通過這種敘事時間的跳躍性來迫使讀者注意敘述時間本身,而以“房子”意象為代表的空間也是與時間融合在一起的,它標識著愛米麗生前的時間與回憶。這些被割裂分散的信息單位巧妙地互相關聯,有機地構成一個藝術整體,每一個單位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它本身,而且也在于它與其它單位的聯系。由于本文掙脫了以往因受“西方主導傳統中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假定”而將敘事“視為因果相接的一串事件”的束縛,所以讀者必須在與整體的聯系中去理解每一個單位。
語境是保證交際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使交際靈活的重要手段。說話人可以利用語境因素成功表達思想,受話人可以結合語境因素對話語進行分析,推導出言外之意,在語境中學習語言是使學生獲得言語交際能力的重要要求。如果我們能夠在閱讀理解教學中較好地運用語用預設與認知語境,一定能夠幫助學生挖掘出話語的深層含義,從而有助于理解作者的寫作意圖。本文通過實例論證了語用推理、認知語境在閱讀理解推理中是一種主動的“猜測—證實”的過程,一種心理語言的揣摩過程,一種 (作者與讀者)“相互交流的過程”。這一認知過程體現在閱讀理解中即為對文章和段落要義的理解、具體信息的搜索、上下文中詞義的推測、作者態度或意圖的推斷。
[1]羅鋼.敘事學導論[M].3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32.
[2][美]H·R·斯通貝克選·序.[M]//《世界文學》編輯部.福克納中短篇小說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100.
[3]劉燦,賀薈中.西方心理語言學中回指推理的研究綜述[J].心理科學,2010(4).
[4]翟雯婷.關聯理論對語用推理機制的闡釋[J].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10(3).
[5]張斌峰,張毅龍.意思表示解釋的語用學透視——語用推理的維度[J].前沿,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