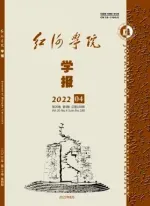媒介再現與社會現實建構
楊惠林
(紅河學院人文學院,云南 蒙自 661100)
媒介再現與社會現實建構
楊惠林
(紅河學院人文學院,云南 蒙自 661100)
媒介真實與社會現實存在著偏差,媒介再現現實的方法主要有對新聞事實的選擇、新聞語言的運用和轉換、報道對象的突出與淡化,媒介不能真實反映現實的原因除了意識形態方面的因素以外,還有強勢階層對話語權的掌控,弱勢群體的集體失聲以及媒介對經濟利益的追逐等方面的影響。可見,社會“現實”是由媒介建構的。
真實;再現;意識形態;建構;偏見
一 社會現實與媒介再現
沃爾特·李普曼在其代表作《公眾輿論》中指出,在信息化高度發達的社會里,主要存在以下三種現實:一是“客觀現實”,這種“現實”是客觀存在著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真實現實,就是事實本身;二是“擬態環境”,而這種“現實”是經過媒介選擇、加工、過濾后向公眾展示的“象征性現實”;三是“主觀現實”,這種“現實”存在于人們意識中的“關于外部世界的圖像”。“主觀現實”是在人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而且這種認識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媒體所提供的“象征性現實”。經過這種中介后形成的“主觀現實”,已經不可能是對客觀現實“鏡子式”的反映,而是產生了一定的偏移,成為了一種“擬態”的現實。對于大眾來說,媒介是信息發布渠道,是他們虛擬環境的來源,因此,媒介常常成為操縱、勸服和制造輿論的工具。[1]1-8
人們生活在一個信息的海洋中,由于實際活動的范圍、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對與他們有關的整個外部環境和眾多的事情都保持經驗性接觸,對超出自己親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們只能通過各種“新聞供給機構”去了解認知。李普曼在其著名的“擬態環境”理論中指出,正是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征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之后向人們提示的環境。然而,由于這種加工、選擇和結構化活動是在一般人看不見的地方(媒介內部)進行的,所以,通常人們意識不到這一點,而往往把“擬態環境”作為客觀環境本身來看待。[1]44
李普曼認為人們認為是“事實”的東西通常只是一種判斷。新聞媒體能提供“事實”和真正的“事實”還不是一回事。李普曼在強調一個重要的定義中寫道:“新聞的任務是報告一個事件的發生,事實所起的作用是把隱蔽的真相公布于眾。”[1]62
傳播媒介就是通過象征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于結構化以后向人們提供的環境就是擬態環境,它不是現實環境的再現,而是信息環境的環境化,人們往往把擬態環境作為客觀環境本身來看待,這種擬態環境不僅制約人的認知和行為,而且通過制約人的認知和行為來對客觀的現實環境產生影響。
再現(representation)一詞意指“再次呈現”,是“真實”世界里一些事物的一種映像、類似物或復制品。[2]139它可以是以一定方式被再現或改編成媒介代碼的物、人、集團或事件。對不同人或事物的再現體現了媒介對該類人或事物不同的看法、立場、態度。再現不是對社會現實的“鏡子式”的反映,而是通過選取一些片斷或忽略掉一些元素、通過角度的選擇、事實的取舍、畫面的剪輯、特效以及蒙太奇組合來體現媒介的好惡、傾向、意圖。
“再現”主要是將不同的符號組合起來,表達復雜而抽象的概念,是人們對傳播符號的選擇與建構,是所關注對象或觀念的意義與結果的過程。再現的動作需要將許多分散的元素,聚集成一個可明了的形式,因此再現是一種人為的話語實踐,具有意識形態的意義。
媒介在現實生活中起到無時無刻不在反復向受眾傳遞著各種信息及觀點,這些信息及觀點由淺入深、由點到面地影響著受眾的認知、態度、情感、價值觀和文化心理,為受眾構筑了一個強大的認知場。可以說,現代受眾的認知結構是在大眾傳媒所展示的“媒體現實”的基礎上形成的。作為主體的受眾所接觸到的信息絕大多數并非來自生活中的現實世界,而來自大眾電視媒介所創造或構建出來的一個新的世界,它不是原來的物理世界的翻版,而是一個思想性的世界。
德里達認為,我們很難區分正確的再現與錯誤的再現,區分真理與謬誤、區分現實與虛構,事實上,再現總是伴隨著不可避免的虛構與錯誤。[3]20所以,媒介對社會現實的再現影響到公眾對某一群體、團體、社會的認知與了解。媒介所塑造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公眾對這一群體的理解和態度,恰當的媒介形象能夠促進社會交往,形成好的社會互動,扭曲的媒介形象則會誤導公眾、形成歧視。
然而,由于受到種種原因的影響,媒介不可能對社會現實進行客觀如實的反映,媒介對現實的反映總是隱藏著種種意圖,盡管有時這種意圖顯得更加隱蔽。
二 媒介再現現實的手段或方法
(一)從新聞產生的過程來看
陸定一曾經把新聞定義: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但是,哪些事實可以成為新聞進入媒介的報道視野,哪些事實盡管有很大的新聞價值,但還是遭到了媒介舍棄?媒介依靠什么來對社會現實進行篩選和判斷,選擇什么, 如何報道, 都反映了媒介的傾向性。因為不是任何新近發生、正在發生的事實都能得到報道。
從微觀上來看,從事實加工到成為新聞成品的過程中,記者、編輯、總編和媒介管理者從自己的立場、態度、價值觀來對事實進行篩選,他們都懷著各自的目的對新聞事實進行稀釋,使之更符合自己的品味,而不管這種目的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
從宏觀上來看,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政治體制、政府部門以及由他們制定的相關的政策等都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對新聞生產進行嚴格的控制。
任何事實都無法完全被報道, 人類只能有選擇地報道。所以說, 任何報道, 本質上都是經過了報道者對事實的選擇, 任何報道其實都是選擇性的報道。
所以在現實生活中,媒介總是代表著某一階級、階層、政黨和國家的利益,在對社會現實的再現過程上,就是要通過對社會現實的取舍來權衡各種利弊得失,維護階級、階層和執政黨的利益,通過某一事件或片斷建構和塑造政府的光輝形象,通過這一光輝形象來體現政府的合法性、權威性和親民性。如媒介總是在時逢節日時報道某些領導深入基層、深入家庭慰問,以此來宣揚領導的親民、務實的崇高品格和為人民群眾服務的精神。
(二)從新聞語言的陳述方式來看
用什么樣的語言來表述或陳述新聞,這取決于媒介從員人員的觀念、態度和立場以及媒介背后的各種復雜的利益主體。性質不同、立場不同、語言不同,所傳遞出的意義也就截然相反。可以說,媒介及媒介的掌控者正是通過對新聞事實的選取、新聞語言的轉換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或目標的。同樣的一個新聞事實,為什么媒介之間的報道會大相徑庭呢?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新聞語言的置換使得新聞看起來更加符合某些團體的利益,如“報喜不報憂”、“反面新聞正面做”等都是運用不同的語言來反映意圖的。
如何客觀公正地報道事實,還事實以本來面目,是新聞媒介孜孜以求的目標,盡管人們認為絕對的客觀是不存在的,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只不過是神話,但捍衛新聞的客觀性卻是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操守之一。日本學者早川一榮推薦了新聞語言的三種陳述方式—報道、推論和判斷。
(1)報道:指的就是一種可以被證實的表述,排除了推論和判斷的原因。新聞報道中所涉及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經過以及所強調的事情的來龍去脈都是可以通過某些渠道能夠得到證實,或者直接在新聞報道中體現出來,如國外的一些記者在新聞報道中所采用的直接引語最多,報道多方說法,這樣所報道出來的新聞才更有說服力,這樣的新聞也才更接近事實的真相。報道是早川一榮推薦的一種最重要、最常用也是最可靠的新聞表達方式。
(2)推論:任何對將來的表述都是推論,因為將來是不可知、未能預見的,這種預測性新聞在媒介中并不少見。筆者認為在新聞報道中要盡量少用推論,即使要用也要基于已知而陳述未知,使對未來的推論具有現實的依據。對于記者來說,最為穩妥的辦法就是限于已知加于報道,即為推論加上現實的依據,這樣目的就是讓推論可以被證實。如可以加上“據某某透露”、“據某部門告訴記者”等,這樣的預測性新聞就可以被查證了。
(3)判斷:是對某一事件、人物或物體表示贊許與否的表達。判斷就是一種主觀認知,而這種主觀認知往往會受到個體情感、情緒所左右,很難做出正確的判斷。而這種判斷一旦經媒介擴散、放大以后,就會在社會大眾中產生一種很難消除的固定成見與偏見。如前些年對“河南人”的判斷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河南人”中只有極個別的人是不道德的,但就是這種個別現象放大、擴散以后就成了整個河南人的不是,就連小品也拿河南人說事。我們到底要問河南人到底招誰惹誰了?
有時,記者在報道新聞時會有意無意地表達一種自己的判斷,作為敏感的記者要認真對待此類判斷。一位合格的新聞記者、一個負責任的媒體可以通過盡量做到排除推論和判斷,盡可能地限于報道而做到語言表述的盡量客觀。
(三)從報道的對象來看
學者俞虹在《當代社會階層變遷與電視傳播價值取向》一文中,依據陸學藝等對中國社會現階段社會階層的劃分,從傳播資源和傳播權力的角度,將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結構劃分為三大塊:1、強勢集團:由擁有相當的或一定的組織資源的國家與社會高層管理者、擁有充分的文化資源或組織資源的大型企業管理人員、擁有充分的文化資源的高級專業人員、擁有充分的經濟資源的大私營企業主構成;2、中間階層:由擁有相當的或一定的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人員、產業人員、農業勞動者構成;3、弱勢群體:由僅僅擁有很少量的或基本沒有三種資源的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構成。[4]
由于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在政治、經濟、文化資源上都不占有優勢,他們處于社會的底層,沒有話語權,沒有再現的權力和能力,只能被任意言說,被人再現。他們在媒介報道時經常被刻板印象化,被卷標化,甚至被污名化,他們大部分在媒介的再現中無法發聲,也不擁有優勢的發言位置,因而處在一種被建構、被塑造、甚至被發明的劣勢處境。正如福柯所認為的那樣:從文化與權力關系的角度看,再現行為本身就是文化內部權力關系的一種體現,那些能夠再現自身和他人的人握有權力,而那些不能再現自身和他人的人則處于無權的地位,只能聽評他人來再現自己。于是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再現,“工人階級是粗陋的”、“婦女天生就是卑賤的”、“少數民族是愚昧無知的”、等等。[3]21
三 媒介不能真實反映社會現實的原因
(一)國家意識形態的控制
從媒介與政治權力和權威的關系來看,媒介的使命之一在于論證和維護政治權力的合法性,鼓吹政治權力的權威性,充當政治權力合法化的機器。著名傳播學者赫伯特·阿特休爾指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新聞媒介都沒有展現出獨立行動的圖景,而是為那些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利益提供服務。在他看來,媒介在任何領域都成為政治、經濟或社會權力的代言人。[5]336
媒介具有強大的政治功能,而在這個政治功能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宣傳或宣揚政府的合法性、權威性和支配性,所以媒介教育或教化就成了不可缺失的關鍵。媒介就好比是在給我們上課,教會我們應該持有怎樣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如何更好的遵循統治階級制定的各種規則、制度。
在中國,由于現行的新聞政策與新聞體制,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宣傳、輕傳播”的傾向。我國新聞體制實行完全國有的有限商業運行機制,新聞媒介具有雙重屬性,即形而上的上層建筑屬性和形而下的信息產業屬性,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劉建明先生指出,中國現行的新聞政策并不抽象地強調什么客觀公正,而是在政治報道上強調立場,強調為誰服務,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黨報體制產生的意識形態。[6]275
在這種新聞政策影響下,我國的新聞媒體長期存在著“重宣傳、輕傳播”的傾向,新聞媒介的宣傳功能倍受重視,而傳播新聞信息的功能則一直未得到應有的發揮。
(二)話語權的掌控或缺失
話語權實質是公民在社會上能否維護其合法權益, 能否獲得做人尊嚴的重要標志。思想家福柯曾說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社會地位, 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7]159
話語和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一種辯證的關系,一方面,話語被社會結構所構成,并受到社會結構的限制,受制于社會層次上的階級和其他關系。另一方面,話語在社會意義上是建構性的,它有助于社會結構的所有方面的建構。因此,話語不僅是表現世界的實踐,而且是在意義方面說明世界、組成世界、建構世界。
政府是通過媒介來建構和掌控話語權的,可以說媒介正是政府話語權的代言人,他們往往是和政府站在一起的,而民眾對政府的方針政策不是始終自明的,他們承擔著教化民眾的重任。底層民眾由于缺乏公開表達聲音的渠道,他們的聲音長期被忽略,這也正是中國媒介長期以來為什么一直以“傳者為中心”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話語實際上是一種資源話語、一種身份話語,更是一種權力話語,無論是商業信息的傳播還是政治情報的傳達,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媒介在社會階層中的“強勢地位”。因此,媒介是一種“部分存在”,它將自己首要地置放于社會的優勢階層之中。即便是媒介在進行大眾傳播的時期,由于媒介的強勢地位,形成的仍然是單向的傳播形態。信息和話語只有媒介單方面作為一個唯一的主體在進行傳播與表達,大眾更多只是作為受眾接受和理解。
(三)商業利益的追逐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一切商品必須以市場為導向,符合市場需求是媒介生存的法則。市場驅使著媒介放棄了文化建設和追求,只服從市場和資本的邏輯。在這種商業文化的刺激下,人們的精神追求呈退縮之勢,物質欲望不斷膨脹,媒介開始遵循商業規則,追求賣點。
商業利益要在交換中實現,大眾媒介也是如此,約瑟夫·斯特勞巴哈和羅伯特·拉羅斯在《今日媒介》:信息時代的傳播媒介》中總結了媒介機構贏得商業利益的方法:直銷、訂購、使用費、廣告、辛迪加、版面費和公共資助等八種。除了公共資助以外,媒介主要通過兩大類來實現自己的利益,①收費媒介(電影、雜志、報紙)通過向公眾出售信息,獲得收益;②另一類是通過其他機構支付的廣告費獲取利益,這一類主要是媒介機構將購買自己制作的媒介內容(附加廣告)傳遞給公眾,換得公眾的注意力,再向廣告主提供刊播廣告的機會 ,獲得刊播費,在這樣的交換中,媒介獲得高于購買或制作媒介內容的成本的利益。
廣告主在大眾傳播過程中,分享了公眾的注意力,這個注意力會同廣告的說服作用,轉為對其產品的購買意愿,正是在這種交換中實現其商業利益。[8]11
那么媒介怎么做才能獲得廣告主的青睞呢,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收視率或發行量,廣告主看重的就是收視率與發行量。所以媒介只能在新聞報道中突出娛樂性、追求刺激性,以此來吸引受眾的注意力,繼而獲得大量的廣告。
媒介正是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媒體正漸漸遠離新聞的公正與客觀,轉向滿足受眾的某些心理。在這種價值取向影響下的媒體關注的不再是新聞的真實性再現,而是媒介所描繪和塑造的“虛性世界”。
[1][美]李普曼.公眾輿論[M].閻克文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大衛·麥克奎恩.理解電視:電視節目類型的概念與變遷[M].苗棣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139.
[3]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20.
[4]俞虹.當代社會階層變遷與電視傳播價值取向[EB/OL].(2009-2-25)[2011-2-12]http://www.cctv.com/tvguide/tvcomment/dssk/swqk/xdcb/tjnr/9236_3.shtml.
[5][美]J·赫伯特·阿特休爾.權力的媒介[M].黃煜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336.
[6]劉建明.媒介批評通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275.
[7]王治河.福柯[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9.
[8]章浩.說服公眾:大眾傳播的商業功能[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Reality Construction
YANG Hui-Lin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ong he University, Mengzi 661100, China )
Media real and social reality exists deviation, media representation realistic methods are mainly on the news fact selection, news language use and conversion, reports the prominent and desalination object, the media cannot really reflect the real reasons besides ideology factors, besides the strong class to counterpoise, control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of collective cried as well as media on economic profit pursuing the influence of such. If yes, social "realistic" is constructed by media.
reality;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construction; prejudice
G20
A
1008-9128(2011)03-0056-04
2011-03-24
楊惠林(1976-),男,云南曲靖人,講師,陜西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聞理論與媒介文化。
[責任編輯 自正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