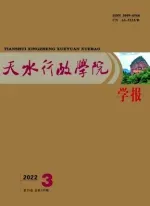意圖倫理抑或責任倫理
—— 法治的倫理基礎引論
蘇仲慶
(鹽城師范學院政法系,江蘇 鹽城 224002)
意圖倫理抑或責任倫理
—— 法治的倫理基礎引論
蘇仲慶
(鹽城師范學院政法系,江蘇 鹽城 224002)
法治的倫理基礎是以意圖倫理為基礎與目的、以責任倫理為中介與手段的混合倫理,它來源并決定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本性。法治的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結合,形成法治倫理的無形之手。我們需要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的結合,需要法治倫理的無形之手,來建設各盡其職、各盡其責、各享其利的正義的社會,即一個真正的長久的和諧社會。
法治;自由意志;意圖倫理;責任倫理
一、法治與倫理
道德與法律是人類社會規范世界的兩個維度。道德(倫理)與法律的關系問題是人類思想之永恒主題與難解之迷,人們通常認為: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是兩個不同的規范體系,道德維度關注的是人的價值精神層面,尋求人的存在意義、生命價值與內心意志自由,法律規范關注的是人的行為層面,尋求人的行為自由[1]。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道德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外化為法律,法律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法律與道德雖同屬于上層建筑,但為不同的范疇:法律屬于制度的范疇,而道德則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的范疇。盡管如此,如我們從人類社會規范世界本身的形成和發展來看,法律和道德從在原始社會中原始的宗教、道德、法律,渾然一體,到規范分化為強強制力的法律和弱強制力的道德,而道德始終是實在法的價值靈魂[2]。可以說,法律雖作為一種專門化的社會控制手段,但“這并不會排斥司法過程的倫理方面。我們需要哲學、倫理學、政治學和法理學給我們提供幫助”[3]。因此,川島武宜說:“過去強調了法和倫理的分離,但是,現在兩者的關聯性的主張成為我們關心的對象。法與倫理這樣一個非常古老的問題,再次在新的聚光燈下的亮相,要求我們加以新的反思。”[4]
現代國家的法律體系通常是以憲法為核心,建設憲政法治國家。法治相對于人而言,其基本含義為法律至上和良法之治。古希臘偉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學》中明確指出:“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導致城邦‘善’的一個條件。”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于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有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他認為法治優越于人治,他說:“凡是不憑感情治事的統治者總是比憑感情治事的人們優良,法律正是沒有感情的。”因此,“誰說應該由法律來遂行其統治,這就有如說,惟獨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統治;至于誰說應該讓一個個人來統治,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這樣,法治的內涵或原則就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法的普遍遵守、良法的實體(內在)價值、良法的程序(外在)價值和基本制度原則。” 由此可見,法治不只是具體的法律,它反映的是一種原則、一種理念。對此,哈耶克作了精彩的闡釋:“法治不是一種關注法律是什么的規則,而是一種關注法律應當是什么的規則,亦即一種‘元法律原則’(或‘超法律原則’)或一種政治理想。”
那么,法治的倫理基礎為何?這是數千年來一直困惑著無數法學家和倫理學家的一個深不見底的問題。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美德倫理學(把道德視作為支配人們選擇的某種理想的品質),到休謨的道德情感論(把道德視作為源自人性中的自然原則即“同情心”的某種“約定”);從近代康德把道德(法則)界說為人的實踐理性中的“定言命令”,到現代馬克斯·韋伯基于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把倫理劃分為“意圖倫理”與“責任倫理”,無數的先哲對法治的倫理基礎作了無盡的探索。西方先哲對法治倫理基礎的探索,表明西方的法治倫理基礎似乎走了一條從入魅到祛魅的道路。開始于17、18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高舉理性的大纛,在近代西方這一特定歷史中推動并催生了具有工具理性的世俗生活秩序的徹底合理化。因此,“隨著宗教信仰的死去,工具理性就走向了僵硬的例行發展道路,消解了價值理性,從而導致工具理性所特有的計算理性橫行于俗世所有領域,隨著宗教的根死去,功利主義悄悄滲透了。”馬克斯·韋伯正是基于這種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異化,最早在《學術與政治》中提出責任倫理及意圖倫理的觀點:“一切倫理,不問其實質內容為何,均可劃分為下列兩大組:其一是‘英雄倫理’,即以之為表示人類努力方向的目標,藏于無窮的彼方,因此提出了他在偉大的生存奮斗中,如無此,即不能忍耐的原理要求。其二為‘平均倫理’,亦即謹慎地接受人類的日常性質為要求的準則。”“平均倫理”即責任倫理,是指以能夠計算和預測后果為條件來實現某種目的,行動者應對后果負責,且義無反顧。“平均倫理”強調責任感,即“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如此”。“英雄倫理”即意圖倫理,與責任倫理相反,它是指行動者只要意圖、動機、信念是崇高的,那么行動者可對后果不負責任,即“基督徒的行為是正當的,結果則委諸主帝”。也就是前者傾向于“此岸世界”,依據的是事實判斷,傾向于“入世”;后者傾向于“彼岸世界”,依據的是價值判斷,傾向于“出世”。具言之,意圖倫理的要義是:一個行為的倫理價值在于行動者的信念、意向的價值,它使行動者有理由拒絕對后果負責,而將責任推諉于上帝或上帝所容許的邪惡。意圖倫理只問動機,不問效果。責任倫理則意味著責任倫理要求行動者注重后果,要對后果負責,感受責任,責任感是核心,因此一個行為的倫理價值只能在于行為的后果,它要求行動者對自己行為可預見的后果承擔責任。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到底是以“意圖倫理”還是以“責任倫理”作為法治的倫理基礎?抑或兩者兼而有之?當然,要尋找它的答案確是件不容易的事,不過盧梭的話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我覺得人類的各種知識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備的,就是關于‘人’的知識。德爾菲神廟里唯一的碑銘上的那句箴言:‘認識你自己’,比倫理學家的一切巨著都更重要。”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任何社會科學都是關于人類自身的科學,進而都是以評估人的本性為基本出發點。因此,遍歷痛苦之萬劫,人渴求知道:他是誰?他從哪里來?他將歸依何方[6]?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其實關涉人的人性本質,關涉人的文化價值體系和認識方法論的問題。正如英國哲學家休謨所言:“一切科學對于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即使數學、自然哲學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種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學”。因此,筆者認為要考察法治的倫理基礎問題,還是要回到對人性探討的源頭,以人性作為確定法治倫理基礎的依歸。
二、人性的自由意志:法治倫理基礎的依歸
“人是什么?”這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命題。“人性就是人人具有的與生俱來的本質屬性,是不學而能的。”[7]也就是說,人性是與人一同來到世上的,從單個的個體的人的角度來看,人性是與人的生命存在相始終的。但人的存在不單是個體的存在,而且是作為集合的社會的類的存在,因此,人性又是與社會的歷史發展相伴而隨的。這就意味著:一方面,人性是人作為生命的自然存在形式具有動物本能的反映;另一方面,人性的大部分內容又是在自然本能的基礎上對自然本能的超越,從而具有社會性和意識性。正是基于此,馬克思對于人類的本性,提出了人具有自然性和社會性這兩種屬性,從而系統、多層次、完整地展示了人的本性。馬克思認為: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人是在社會中存在的,“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只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對他說來才是他的人的存在。”并且,“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他的生命活動是有意識的。”“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因此,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自由自覺的活動(自由意志)就是人的類本質。這兩點是馬克思理論的邏輯起點。
完整的自由意志概念最初是出現在基督教哲學中。基督教哲學家們認為上帝在創造人類時賦予了人類意志自由,人類能根據自己的意志決斷來自主、自我負責和能動地去生活和行動。奧古斯丁在《論自由意志》中認為,上帝之所以把自由意志賜予人,是因為如果沒有自由意志,人就不可能正當地生活,就不可能超越自然事物所遵循的必然性而成為真正的人[8]。因有自由意志,人的意志才是自由的:人在意志上愿意(意愿)什么和不愿意什么完全取決于人自己的意志的決斷,即決斷愿意服從或者不愿意服從的能力。當然,上帝在造人時,也知道他會受誘惑,因為他是有肉身的存在,而不是純精神的存在,但是,由于上帝給予他自由意志,使他有能力決斷不去意愿、追求誘惑物,也即說使他有能力經受住誘惑,能夠對任何誘惑說“不”[9]。因此,奧古斯丁通過追問罪與責的來源和根據而開顯出人的另一維更深刻的超驗存在即人的自由意志,由此開始了倫理學從“幸福生活指南”向“罪—責倫理學”的轉向。這種奠定在對自由意志的覺識基礎之上的罪—責倫理學,不僅使人在本性上區別于他物,而且使人在格位上與萬物有別:因為有自由意志,人的存在才獲得了正當性品格,也只有自由意志,人的存在、行動才有正當不正當的問題[10]。沒有自由意志,人的存在和行為與其他萬物一樣,都出自其本性。這種罪—責倫理學意義上的自由意志,從而在西方的宗教、哲學和倫理領域發生了“哥白尼式革命”,因而對政治和法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由意志使每個人成為他自己存在的目的本身。因為你被賦予了自由意志,你賦得了這樣一種權能,即你完全能夠只從自己的意志出發決斷自己的意愿,能夠把自己意愿什么和不意愿什么完全置于自己的意志支配之下,也即說,你有能力完全只根據自己的意志去決斷生活、行動。從自由意志這種權能,個人獲得了這樣一種絕對的法律屬性,即他在與他者發生法律關系時,他必須被允許根據自己的意志決斷生活和行動;而且,由于每個人賦得的自由意志這種權能是先天的超越性存在,每個人的這種法律屬性是絕對的、不可替代的,更是不可剝奪、不可讓渡的。同時,個人的這種絕對權利是其包括平等權在內的一切其他權利的基礎和前提,從而自由意志使每個人能夠只根據自己的意志決斷生活和行動,而不必以任何他者的意志,哪怕是最高存在者的意志為根據,任何國家權力都必須保障個人的這種絕對權利。每個人的存在不以任何他者為目的,而只以自己為目的,這在根本上是說,每個人的存在(生命)是不可替代的,不能僅僅被當作他者的工具,作為自己的目的本身存在是每個人的絕對尊嚴之所在,而這在根本上是說,人的絕對尊嚴來源于他的自由意志。
從上述我們可知人的自由意志存在的本性,決定了人是一種獨立自主的自在自為的存在,決定了人一方面是有意志的,另一方面意志又是自由的,從而人的自由本性使人有著天然的神圣平等的權利——人始終是目的,人的意志使人有行為或不行為的能力,而人的自由意志才使人能識別善惡以及選擇的可能和空間,并因此人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人的自由意志的本性為法治的倫理提供了來源,并決定了它的內涵:前者是意圖倫理,后者是責任倫理。法治的倫理必須以自由意志為其前提,如果沒有自由意志,我們迷失了人的存在意義與生命價值,沒有了神圣平等的權利這一根基;同時,我們也就沒有了識別善惡以及選擇的可能,我們也就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也就談不上道德或不道德。因此,康德說,自由不只是倫理學的基礎和前提,而且是整個純粹理性體系的“拱頂石”。
三、以意圖倫理為基礎與目的,以責任倫理為中介與手段:法治的混合倫理基礎
人的這種自由意志的自在自為本性,表明人是一種獨立自主的主體存在,也正是人的這種自由意志為人提供了存在意義、生命價值,奠定了法治的終極目標與關懷:人有尊嚴和追求幸福的自由,人永遠是目的,這些是神圣的、無條件的和絕對的,這構成法治的意圖倫理基礎。“人,其實而且每一個有理性的存在者本身,是自身為一個目的而存在的,不只作為一種手段為這個或那個意志所利用而存在的,因而在其一切的行動,無論這些行動是對于自己或對于其他有理性的存在者,都必須總是看為一個目的的”[11]。韋伯也說:“能夠深深打動人心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齡大小),他意識到了自己行為后果的責任,真正發自內心地感受著這一責任,然后他遵照責任倫理采取行動,在做到一定的時候,他說:‘這就是我的立場,只能如此。’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動的表現,我們每一個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須明白,我們都有可能在某時某刻走到這樣一個位置上。”而“內心地感受著”責任,以責任倫理行動,實際上就是以一個人的尊嚴或信念去行動,結局只能是“這就是我的立場,只能如此”,這正是意圖倫理價值之所在。
然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們不可能完全真正達到真、善、美,尤其是在一個沒有上帝、沒有先知的當今時代,經驗科學和功利取向已經把所有神圣的東西從這個世界上驅逐出去了,從而使人類陷入齊美爾所稱的“文化悲劇”:“人類已經喪失了文化的意義和價值,人已淪為一種物,成為一種工具而非目的;人與世界的人格關系已被橫行于世的貨幣所扼殺,貨幣消解了一切意義和價值,結局只能是思想凈土的世俗化,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12]。因此,在現實的法治建設中,任何純粹的“意圖倫理”在理論上顯得難以為人們接受,而更為重要的是在實踐上也顯得跛腳跛行,艱難為繼。那么出路何在?唯一的出路即在于責任倫理。在責任倫理中,責任感是責任倫理的核心。誠如康德所言:“理性存在者本身從來不僅僅被用作手段,而被當作限制全部手段應用的最高條件,在每種情況下都同樣被當作目的。”[13]“構成了任何事物都能成為自身目的的全部條件的東西不僅具有相對價值即價值,而且具有內在價值,也就是尊嚴。”具言之,通過“責任倫理”,一方面可以導出目標合理性行動,為經驗理性的行動方式提供倫理價值;另一方面又與“意圖倫理”相接,為抽象的道德理念奠定現實的實踐基礎。這樣,在現實的法治社會中,一方面,公民每一個人有恪守服從法律的義務,通過履行法律的義務,按應負的法律職責行事,從而明確出每一個人的獨立空間,進而生成和發展人的神圣、平等、寬容乃至博愛,無疑,人按照責任感行事的自由意志也就使人具有應有宇宙中最高價值——人的尊嚴或者說是一種人格;另一方面,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公共權力時,基于公共權力設定目的,遵守法定的有限的權力,按照法定的正當程序,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進而形成合理的公共權力的權威——公共權力應有的人格威嚴,達到保護和促進人權的最終目的。正是這種各盡其職,各盡其責,各享其利,才能形成這樣一個正義的社會,即一個真正的長久的和諧社會:給予每個人其應得的東西,也就是西塞羅所說的“正義是使每個人獲得其應得的東西的人類精神意向”[14]。
由此可見,法治的這種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基礎是相互相稱的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就此而言,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便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互為補充的,惟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才構成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根據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在現實的法治社會,一方面是以責任倫理為手段來合理性行動(工具理性)創造著相對價值,另一方面是以意圖倫理為前提的“法治的終極關懷”而產生的內在價值——尊嚴。這樣通過責任倫理的自覺,在現實的法治社會每個人獲得真正的和完善的人格、尊嚴及自由。可以說,在現實的法治社會,任何一種意圖與信念,唯有當它與責任倫理結合在一起時,才可能是有效的。
四、結語:法治倫理的無形之手
法治倫理是以意圖倫理為基礎與目的,以責任倫理為中介與手段的混合倫理。人是目的,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建構與運作都是以人是目的這一意圖倫理為基礎與前提的,以達到促進和保障人權這一出發點和歸宿點,讓國民追求和感受幸福生活;而法治倫理又憑借責任倫理為中介與手段來落到實處,在按責任行事這一責任倫理手段與過程中讓每個人真正享有人的尊嚴和完善的人格,并獲得正義——幸福的生活,也使公共權力獲取正當性和合理性而擁有權威來提供有效的公共產品,從而成為一個有自由和秩序的穩定和諧的社會。正是這種法治的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結合,才使每個人享有人的尊嚴和完善的人格,在有效的公共產品的保障下追求幸福生活,從而真正做到“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這樣的社會里,每一個人的充分自由的發展,每一個人的聰明才智的發揮,每一個人的利益最大化,每一個人能真正追求和感受幸福生活,這樣的國家豈不國強民富?這樣的社會豈不是真正的穩定和諧之社會?換言之,在法治的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結合下,民富是目的,是法治倫理的主產品,而民富了國也就富了強了,它始終是法治倫理的副產品,不能本末倒置。如果借用市場經濟的市場自動調節和發展經濟這一無形之手,那么,法治的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結合的作用也是無形之手,是相對于市場經濟無形之手而言的政治無形之手。
[1][2]高兆明.倫理學理論與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5-86,86-99.
[3](美)龐德.法理學(第一卷)[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72-73.
[4](日)川島武宜.現代化與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43.
[5]周永坤.法理學—全球視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28.
[6](俄)尼古拉·別爾嘉耶夫.人的奴役與自由——人格主義哲學的體認[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3.
[7]楊敬年.人性談[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48.
[8][9]奧古斯丁.論自由意志[A].奧古斯丁.獨語錄[C].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389-411.
[10]黃裕生.原罪與自由意志——論奧古斯丁的罪—責倫理學[J].浙江學刊,2003,(2).
[11][13](德)康德.實踐理性批判[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09.
[12](德)康德.康德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172.
[14](德)格奧爾格·齊美爾.時尚的哲學[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216.
Ethic of Conviction or Ethic of Responsibility——Introduction on the ethical basis of the rule of law
SU Zhong-qing
(Yancheng NormalUniversity,Yancheng224002,China)
The ethical basis of the rule of law ismixed ethics,which the intent and purpose is ethic of conviction and the intermediary andmeans is ethic of responsibility.The ethical basis of the rule of law is stemed from and deciced on the nature of free will.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ethic of conviction and the ethic of responsibility of ruleof law forms invisiblehand ofethicalbasisof the rule of law.We need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ethic of conviction and theethic of responsibility of ruleof law,invisible hand ofethicalbasisof the rule of law,to build justice society,which fulfill their duties every body and enjoy their benefits every body,namely a real long-term harmonious society.
ruleof law;freewill;ethic of conviction;ethic of responsibility
D90
A
1009-6566(2011)01-0089-05

2010-09-08
蘇仲慶(1965—),男,安徽無為人,鹽城師范學院法政系講師,法學碩士,主要從事憲法、法理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