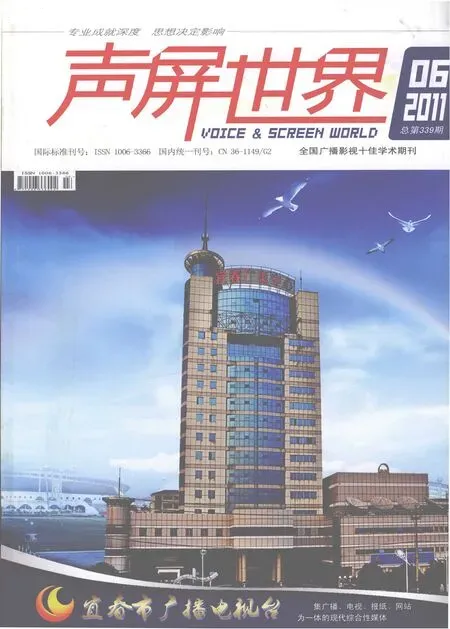走出困局:“視中植入廣告”轉向“視后營銷體驗”——影視節目植入廣告的困局與對策
□茍德培 謝華萍
2010年廣告風起云涌。從春晚到熱門電影、電視劇,贊助商的急功近利、制片人的唯利是圖、導演者的魚目混珠,讓繁蕪的植入廣告擠入影視作品,登上熒屏。而受眾的各種不滿與抵觸,也開始在新聞媒體對廣告無序植入的不斷揭露與批判中潛滋暗長,與日俱增。
如何走出受眾不滿的當前困局?除了呼吁廣告要精確植入、軟性植入、適時植入、適量植入、巧妙植入,可不可以立足植入另辟蹊徑,走出一條繞開抵觸、植入意念、誘導體驗、促成消費的新路?
前鑒:植入式廣告的營銷困局
視中植入即在影視文藝類節目的制作與演播過程中植入廣告元素進行隱性宣傳。雖然這種比傳統廣告更有“高針對性”和“低抵抗性”的商品營銷手段早在《超級女聲》《我型我秀》等真人秀節目中就已經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高潮,創下逐年攀升的產值,但論其為普通受眾所知,恐怕還得說虎年春晚。正是虎年春晚中植入廣告的集體亮相,使受眾對影視文藝植入廣告的反對、抵制與聲討,開始在媒體的助力下迅速達到高潮。
廣告植入有顯性、隱性之別。顯性植入如“蒙牛酸酸乳超級女聲”式,受眾能認可和接受,但是成本太高,贊助商較難承受。而隱性植入如影視中的廣告元素,投入成本不高,贊助商樂于接受,但受眾又不接受。面對受眾的聲討與媒體的圍剿,業界哀鳴:“眼下,植入廣告越來越難做,越來越難成了!”為什么?很簡單,無論制作方將廣告植入得是多么巧妙合理,多么適時適當,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植入一個廣告,既渴望被受眾識別出,又害怕被受眾識別出。渴望受眾識別出,是因為看不破,廣告效果可能就出不來,贊助商就不高興,失敗;害怕受眾識別出,是因為看破了,受眾又不高興,還是失敗。
沒有贊助認可、沒有受眾接受的廣告是沒有生命力的失敗廣告。反躬自省,為什么受眾會對植入廣告如此憎惡?依筆者之見,影視植入廣告至少犯有三忌。第一,對受眾情感的傷害。影視受眾觀看一集電視劇、一幕電影、一節小品,目的無外乎追求藝術美感、滿足視聽愉悅,同時放松身心、舒緩疲勞,而無孔不入的植入廣告無疑破壞了這種追求,被愚弄、貨賣、強迫和不被尊重的微妙情感讓受眾難以舒坦。①第二,對作品品質的傷害。伴隨著受眾對植入廣告的識辨、勘破數量的不斷增多,伴隨著受眾對植入廣告的厭煩、抵觸情緒的不斷增加,再好的藝術作品即便是人們喜聞樂見的 “本山小品”,或是人們嘆為觀止的 “劉謙魔術”,都被批評得灰頭土臉,挑錯至體無完膚。作品品質自然在爭議、詬病、厭棄中漸打折扣。第三,對廣告效果的傷害。當作品的品質與受眾的情感雙重受損的時候,怎么還可能指望正面的廣告效果曲線不斷上揚?不收看、不選擇、不購買,不僅讓廣告失去了廣而告之的意義,甚至惹來口水,惹來是非,惹來怨恨……如此一來,廣告效果從何談起?
更為糟糕的是,如果隔岸觀火的商業競爭對手趁機煽風點火,雇傭網絡“水軍”發出抵制的號召,以示憤慨和抗議,這個時候,無論是植入廣告的制作方、影視文藝的贊助方、影視文藝與植入廣告的推出方,都不得不站在輿論的口水中,飽受世人的詬病。
借鑒:體驗式營銷的成功范例
視后營銷體驗其實包括視中植入意念和視后營銷體驗兩個過程。視中植入意念是培養受眾對所需傳播意念的發現、認識、熟悉、記憶;視后營銷體驗是生產并推出與植入意念對照的產品,吸引受眾的選擇、嘗試、體驗,從而實現對意念產品的消費。
如以下幾個“視中植入意念+視后營銷體驗”的生動案例:
案例1:張賢亮鎮北堡“賣荒涼”。寧夏鎮北堡本是荒涼的代名詞。1993年,文人張賢亮在此創辦華夏西部影視城,截至目前,已有近百部影片在此拍攝完成。從謝晉的《牧馬人》到張藝謀的《紅高粱》,從何平的《雙旗鎮刀客》到徐克的《新龍門客棧》,從王家衛的《東邪西毒》到周星馳的《大話西游》……誕生于此的作品 “構成了中國影視劇歷史版圖上相當耀眼的一部分”,故享有“中國電影從此走出”的美譽。因為這些電影的拍攝,影視城景點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于是,張賢亮將 “感受體驗影視原景”轉化為商品“賣”給游客,打造出國家4A級景區。游客漫步在影視城里,仿佛走進了電影的世界。
案例 2:“哈利·波特”主題公園。在奧蘭多環球影城內,有一處以《哈利·波特》系列小說為藍本建成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在這個主題公園里,游客可以看到電影中最具代表性的幾處地點,包括霍格莫德小鎮、神秘的禁林、霍格沃茲魔法學校、九又四分之三站臺等多個地方。環球影視公司承諾,主題公園將復制系列小說中的一些經典場景,“哈迷”們不僅可以看到書中和電影中展現的場景和畫面,還可以進入霍格沃茲魔法學校參觀鄧不利多校長的辦公室,在對角巷奧利凡德魔杖店購物,在破釜酒吧里吃飯,在霍格莫德村的商店里購買電影與小說中獨有的巧克力蛙及黃油啤酒等,甚至親身來一次掃帚飛行。當然,大家恐怕得用“麻瓜”世界里的真實貨幣消費。
案例3:穆棱煙廠與宇宙牌香煙。在1984年春節聯歡晚會上,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馬季先生曾表演過一段推銷宇宙牌香煙的單口相聲,諷刺社會上夸大其詞、名不符實,在產品生產和銷售中弄虛作假的歪風。他那繪聲繪色的演技和入木三分的刻畫,至今猶是聲如在耳,形如在目。當時,我國并沒有宇宙牌香煙。黑龍江省煙草公司和穆棱煙廠的企業家們嗅覺敏銳,從馬季先生的表演中獲得了靈感,立即推出宇宙牌香煙,引起消費興趣。同時迅速與云南省昆明卷煙廠聯合,優化卷煙質量。從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宇宙牌香煙名揚煙海,暢銷不衰,撐起了穆棱卷煙廠的半壁江山”。
這幾個例子的共同點就是視中植入未來商品的意念,視后進行體驗式營銷。而綜合比較視中植入廣告與視后營銷體驗兩種營銷模式,其異同點各有哪些?相同點是都在植入意念,都在渴望關注,都在尋求消費;不同點是前者植入的是既有商品的意念,尋求的是競爭消費;后者植入的是未來商品的意念,通過受眾的熟悉與記憶,吸引受眾進行體驗消費。兩者又都借勢于影視與明星的推介,但植入方式不同,推介效果亦有不同。與植入廣告逐漸遭遇受眾抵觸不同,植入意念反而讓受眾樂于欣賞,樂于接受。一旦出現現實產品,還主動尋求體驗。
通過案例展示,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前者植入讓消費者厭惡并抵觸,后者植入卻反受青睞與眷顧?有一點顯而易見,后者之中沒有既有商品元素的廣告植入,當然也就無所謂大眾意義的廣告,沒有廣告,何來抵觸?沒有抵觸,也就可能有了新鮮、新奇,并渴望嘗試與體驗的沖動。
后鑒:互補式整合的交叉推廣
看清了“視中植入意念+視后體驗營銷”模式的效果,還得摸準其相應的植入路數與營銷方法,論者以為步驟有三:
先入意念,留下空白。何為先入意念?即將某種虛擬物品的意念植入影視文藝中,提前拋售,通過演員話語的烘云托月,借助熱播熱映熱收視,將虛擬物品的品牌、價值、性能等意念推介給影視受眾。讓影視受眾逐漸熟悉、記憶,并在潛移默化中形成對意念產品價值與品牌的認同。先入意念的核心即在拋售意念、營銷意念、推廣意念,讓意念先于產品面世、先與受眾相見,目的即為吸引受眾眼球、留下購買期待、培養潛在客戶。動畫片《海爾兄弟》中的“海爾品牌”意念先入,就是“從娃娃抓起”以培養潛在客戶的生動借鑒。而意念先入,產品后出中間的過程,又是留下空白供受眾體會與玩味的審美期待過程。空白可以調動和激發起受眾想象與企盼的“良好綿延”,轉換到營銷語境中即是:在產品尚未上市的空白時段里,意念中有、市面上無的該品牌的產品,實實在在地吊起了渴望體驗的消費者的胃口。
繞開抵觸,引導風尚。植入廣告讓心存芥蒂的影視受眾漸生抵觸,而植入意念則在回避與繞開中悄然化解了這一矛盾。無現實產品的植入,何來廣告抵觸的憂慮?視后體驗營銷變抵觸為順暢、愉悅的欣賞,變抵制為無遮攔、無防備的接受,把當下社會對植入廣告的厭惡、摒棄扭轉為對消費新風尚的引導——用新的消費資料打造新的消費觀念,用新的消費觀念引導新的消費風尚,用新的消費風尚打開新的消費市場。
視后推出,營銷體驗。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曾得出結論:“體驗”制造商將成為未來經濟的基本支柱之一。張立偉先生說:服務經濟是為“飽暖”服務,體驗經濟是為“飽暖思體驗”服務。體驗就是讓人覺得“爽”。②邁出先入意念、繞開抵觸、引導風尚等等的下一步,就是推出產品閃亮眼球,讓受眾滿懷著欣喜與沖動去嘗試與體驗,以此達成消費。而達成消費僅僅是體驗營銷的開端,要讓受眾確認產品價值、形成品牌信賴,然后自動貼近該產品成為忠誠的客戶,就必須保證產品確實異于同類而又優于同類。在保證或提高質量的基礎上翻新花樣,添加樂趣,增多選擇,不斷挑起、刺激、滿足受眾的體驗享受。否則,嘗試與體驗的欣喜和沖動就可能在平淡無奇中急轉直下,在失望與冷漠中前功盡棄。
欄目責編:黎 莉
注釋:
①朱 光:《話劇如此“失身”商業 植入廣告太泛濫引發抗議》,《新民晚報》,2010年9月19日。
②張立偉:《體驗·文化消費·產業》,《四川文化產業發展報告》(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