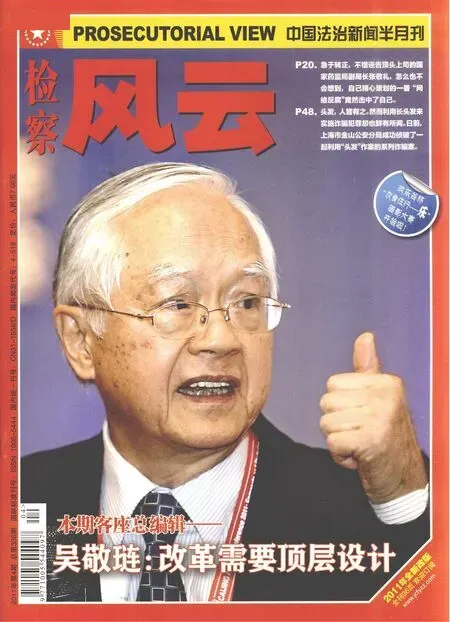行政高成本的合理與不合理
文/楊宇立
行政高成本的合理與不合理
文/楊宇立
哪些因素推動(dòng)了中國(guó)行政支出的合理上升
制度性的因素至少包括,⑴人員增加;⑵公職人員調(diào)資;⑶公檢法部門增支。
根據(jù)《中國(guó)統(tǒng)計(jì)年鑒2007》“按行業(yè)分就業(yè)人員數(shù)”欄目下“國(guó)家機(jī)關(guān)、政黨機(jī)關(guān)和社會(huì)團(tuán)體”一欄下的統(tǒng)計(jì),1978年的人數(shù)為467萬人,2002年為1075萬人,在其后的“機(jī)關(guān)”統(tǒng)計(jì)口徑下,2006年的數(shù)字為1111.8萬人。僅此人數(shù)之差就構(gòu)成行政支出翻一番的增支因素——在行政支出大項(xiàng)目?jī)?nèi),行政管理費(fèi)當(dāng)中的人員工資加上辦公經(jīng)費(fèi)。
為什么說該增支因素合理?答案是,以1978年公職人員總體素質(zhì)與2006年的情況相比,中國(guó)順應(yīng)了搞現(xiàn)代化建設(shè)必須不斷補(bǔ)充掌握現(xiàn)代知識(shí)的年輕人進(jìn)入公職崗位的要求。當(dāng)然,加上通過“借調(diào)”等方式長(zhǎng)期滯留在各政府公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工作的編外職工數(shù),肯定就不止于上述數(shù)字了。
據(jù)統(tǒng)計(jì),2006年全國(guó)公職人員的平均年薪為2.25萬元,但在1978年,全國(guó)公職人員的平均年薪即使按千元計(jì)算,即每月80元工資,也是個(gè)偏高的估算,到處都有活躍的“以工代干”者。假定人均年薪為千元,僅此一項(xiàng)就構(gòu)成23倍的行政增支因素,再根據(jù)公職人員數(shù)增加一倍來推算,就構(gòu)成46倍的行政項(xiàng)目增支因素。
人們都知道,“文革”的成果之一是“砸爛公、檢、法”,但“文革”時(shí)期中國(guó)還一直保有公安部。“文革”結(jié)束以后,中國(guó)全面恢復(fù)檢察院、法院系統(tǒng)。2006年中國(guó)公檢法機(jī)關(guān)的開支為2174億元,接近“四大班子”加上民主黨派和社團(tuán)經(jīng)費(fèi)的2/3。假定公安系統(tǒng)的開支占去公檢法的一半以上,全國(guó)檢察院、法院的行政支出絕對(duì)數(shù)額理論上也接近千億元之多,這筆支出相對(duì)于1978年的行政管理費(fèi)算得上是從無到有。
一方面,不可否認(rèn)中國(guó)公檢法系統(tǒng)存在浪費(fèi)現(xiàn)象,比如有些新建的檢察院、法院辦公樓宛如宮殿;另一方面,目前中國(guó)公檢法系統(tǒng)的辦案經(jīng)費(fèi)也絕對(duì)談不上足裕,在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特別是中西部的基層司法部門,能確保工資按月足額發(fā)放也不過是近兩年才實(shí)現(xiàn)的目標(biāo)。這些事實(shí)能支持的結(jié)論是,至少中國(guó)公安系統(tǒng)的經(jīng)費(fèi)不足,否則各地不會(huì)出現(xiàn)那么多“協(xié)警”、“協(xié)管”,同時(shí),全國(guó)范圍內(nèi)涉及公共秩序與安全的行政開支嚴(yán)重不平衡,基層司法系統(tǒng)的辦案經(jīng)費(fèi)還很緊張。
哪些因素導(dǎo)致了中國(guó)行政成本的不合理增加
即便人們考慮到各國(guó)的行政組織統(tǒng)統(tǒng)免于經(jīng)濟(jì)組織那般競(jìng)爭(zhēng)環(huán)境,中國(guó)行政增支的決定性因素也是明擺著的——缺乏公開透明的說實(shí)話、處細(xì)賬的財(cái)政預(yù)算,以及民意代表具有專業(yè)水準(zhǔn)的認(rèn)真審議。
從根本上說,陽(yáng)光政務(wù)源于陽(yáng)光財(cái)務(wù)。基本的因果關(guān)系是,陽(yáng)光預(yù)算越精細(xì),預(yù)算約束力越強(qiáng),可致日常行政工作中“一把手”調(diào)動(dòng)“公款”的隨意性越小。實(shí)踐證明,財(cái)務(wù)“一支筆”制度對(duì)于度過財(cái)務(wù)難關(guān)是有一定意義的,但當(dāng)財(cái)力充裕時(shí),該制度很可能成為少數(shù)人浪費(fèi)寶貴的公共資金的“幫兇”。
總之,有序推進(jìn)陽(yáng)光財(cái)政是現(xiàn)階段中國(guó)逐步限制各級(jí)政府公權(quán)力被濫用,以及管好、用好納稅人經(jīng)濟(jì)剩余所積累的公共資金的有效途徑之一。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要完全止住行政支出資金“出血點(diǎn)”很不容易,這是一個(gè)系統(tǒng)工程,涉及的問題太復(fù)雜。在歷史上,中國(guó)也許確如黃仁宇所說“缺乏數(shù)目字管理的經(jīng)驗(yàn)”,而現(xiàn)代化的中國(guó)是不可能拙于對(duì)“數(shù)目字管理”制度安排的。
還有一個(gè)傳統(tǒng)因素很麻煩并且被不適當(dāng)?shù)睾雎粤耍粗袊?guó)政府自古在集權(quán)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經(jīng)驗(yàn),它特別適于“辦大事”,那么“小事”怎么辦?靠士紳、靠宗族、靠幫會(huì),所以“皇權(quán)不下鄉(xiāng)”。
概言之,在傳統(tǒng)上中國(guó)政府不大擅長(zhǎng)社會(huì)管理。這在現(xiàn)實(shí)中構(gòu)成了一個(gè)相當(dāng)棘手的問題,當(dāng)中國(guó)社會(huì)發(fā)展日益多元化的時(shí)候,以下兩大難題不易輕解:⑴政府管理覆蓋社會(huì)管理領(lǐng)域,政府不承擔(dān)無限責(zé)任才不合邏輯;⑵政府用辦大事的制度去處理很具體、瑣碎的小糾紛和矛盾,行政成本不上升才不合邏輯。典型如,地方政府的一個(gè)官員從北京接回一個(gè)上訪者,平均直接成本不少于2000元。這還不算最初解決問題的費(fèi)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