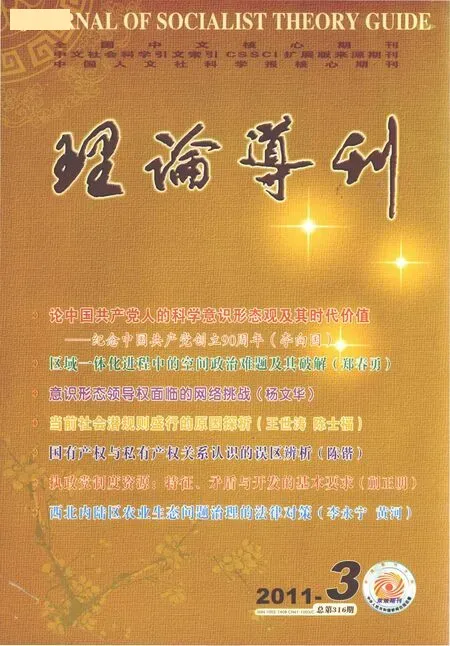評馮友蘭的人生四境界說
——兼論人生三境界
鄧曉臻,溫立武
(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山東淄博255049)
評馮友蘭的人生四境界說
——兼論人生三境界
鄧曉臻,溫立武
(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山東淄博255049)
馮友蘭賦予西方理念“人是理性的動物”以中國化的表達方式,由此提出了具有深厚中國傳統文化底蘊的人生四境界觀點。但是,他的邏輯起點仍然是對人的符號化定義,沒有包含人的價值規定性的全面性。他的人生四境界帶有非歷史的缺陷,有道德理想主義的缺陷,也帶有人類早期文化的自然崇拜的缺陷。從人的價值規定性及其實現程度出發可以看到人生三境界,即個人自我實現的審美意境、與社會同在的審美意境和與歷史同在的審美意境。
馮友蘭;人生境界;人的價值規定性;自我實現;審美意境
作為學貫中西的新儒學代表人物,馮友蘭賦予西方傳統中根深蒂固的理念“人是理性的動物”以中國化的表達方式,由此出發提出了具有深厚中國傳統文化底蘊的人生四境界觀點。但是,他的邏輯起點仍然是對人的符號化定義,這種定義沒有包括人的價值規定性的全面性。在他的人生四境界中,自然境界不過是沒有得到發展的、缺乏反思的人生境界,功利境界不過是近代西方商品拜物教之下的自然狀態,道德境界僅僅是傳統的政治共同體整體主義下的精神生活境界,而他的天地境界明顯帶有人類早期自然崇拜的內容。從人的價值規定性的全面性及其實現程度可以看到人生三境界,即個人自我實現的審美意境、與社會同在的審美意境和與歷史同在的審美意境。
一、馮友蘭人生四境界思想的理論依據
馮友蘭在《新原人》中指出,“人是有覺解的東西,或有較高程度覺解的東西”,“人生是有覺解底生活,或有較高程度底覺解底生活”,“這是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人生之所以異于別底動物的生活者”。在這里,“解是了解”,“覺是自覺”,覺解構成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禽獸雖有某活動而不了解某活動是怎樣一回事,于有某活動時,亦不自覺其是在從事于某活動。人則有某活動,而并且了解某活動是怎樣一回事,并且于有某活動時,自覺其是在從事某活動”。[1]526他還指出,“人不但有覺解……并且與覺解時,能自覺其覺解”,[1]530人之作為人就應該“求盡心盡性,應該充分增進他的覺解。”[1]576應該說,這是西方的普遍觀念“人是理性的動物”的中國化表達方式,人是理性的動物,意識、思維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本質規定。馬克思在其早期也有類似的認識:“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2]96“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么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2]97從叔本華開始的人本主義者把人看作是非理性的動物,卡西爾提出人是符號的動物從而是文化的動物;在中國古代,“人者,仁也”,人是道德的動物構成儒家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最基本認識。這些關于人的認識共同點是對人做出符號化定義,在這些定義中表現出來的思維方式是,提出一種價值標準,它構成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構成人的本質規定,仍然是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
馬克思(從1845年開始)和海德格爾堅決拋棄這種符號化定義的思維方式。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以處于具體社會歷史境遇中的“現實的個人”作為理論出發點,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得到的現成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3]23而且他還堅持把人放到人的生活活動、人的感性活動中進行研究,因為“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也就怎樣”。[3]24與馬克思非常接近,海德格爾作為基礎存在論建構起點的“此在”含義包括:(1)處于具體社會歷史境遇中展開其生存活動的人,“這種存在者,就是我們自己向來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它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還能夠對存在發問的存在者”;[4]9(2)人的實際生存活動,“此在能夠這樣或那樣地與之發生交涉的那個存在,此在無論如何總要以某種方式與之發生交涉的那個存在,我們稱之為生存”,[4]15而且“每一此在總都就作為實際此在而存在,我們把實際此在的這一事實性稱作此在的實際性”;[4]65(3)人的實際生存活動所構成的生活世界,“世界……是被了解為一個實際上的此在作為此在‘生活’‘在其中’的東西……是指‘公眾的’我們世界或者是指‘自己的’而且最切近的‘家常的’周圍世界”。[4]76海德格爾的“此在”的前兩層含義分別對應于馬克思的“現實的個人”和“人的感性活動”。兩者的共同點是拋棄對人的符號化定義,從描述人的實際生活過程研究人。馬克思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460“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5]452海德格爾也明確認為,“此在的‘本質’在于它的生存”,“在于它去存在”,[4]49共同點是在人的探究方面(也在哲學探究和整個理論探究方面)反對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應該說,在馬克思之后的西方,反對本質主義,拋棄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已經成為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探究的主流了。
二、馮友蘭人生四境界思想的缺陷
馮友蘭按照人的自覺意識的普遍程度提出人生四境界,既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筆者認為,其人生四境界說存在著自然崇拜、道德理想主義、反歷史主義和整體主義的缺陷。
首先,馮友蘭的人生境界思想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理想主義的缺陷。這突出表現在他對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的論述中。馮友蘭認為功利境界未必是不道德的,但由于沒有認識到自己是社會的存在者,他的行為一定是與道德無關的。關于道德境界,馮友蘭認為,“在倫謂之盡倫,在職謂之盡職”,而“盡倫盡職的行為,是道德的行為”,而且“無論盡某倫、盡某職,都是行義”,因為“行義者,其行為遵照‘應該’以行,而不顧其行為所可能引起底對于其自己的利害”。[1]609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人者,仁也”,人是道德的動物,人作為人就在于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和道德境界。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孟子曰:“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由此形成了重義輕利的基本價值取向,“義”“利”之辯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不爭的主題,無論孔子如何強調“生財有大道”而對“利”予以肯定。但是,一旦否定了“利”,“義”就成為空泛的道德原則了;“義”作為道德原則不能不包括對利益的協調。剝離了道德觀念和道德原則的具體歷史境遇,也就把道德絕對化了。道德境界的內在規定是對自己的社會之倫和社會之職的“覺解”,外在表現是“利他利人”,這仍然帶有中國古代重利輕義的色彩,馮友蘭的人生境界論沒有克服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思維的道德理想主義的缺陷。
其次,馮友蘭的人生境界思想帶有自然崇拜的缺陷。這突出表現在他對天地境界的闡釋中。在馮友蘭看來,天地境界包括“覺解”到自己是“天民”,處“天倫”并且自覺地“盡天職”,即人不僅認識到自己是社會的存在者,也是宇宙的成員,還基于這種“覺解”自覺為宇宙的利益而做事。但是,該如何理解天呢?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的含義有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和人文義理之天。自然之天嗎?在此意義上的“天理”、“天道”意指什么?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還是微觀上的能量的聚合與耗散?主宰之天是賦予自然以神的屬性(人的屬性),人文義理之天是以人的屬性和人文含義規定的自然,兩者都是人文化的自然。如果是此含義,那么天地境界就僅僅是賦予自然以人文義理的含義并用帶有此含義的自然和宇宙表達人生的意義和境界,這樣它的含義就仍然應該到文化中尋找,到人類的自我意識中尋找。進一步看,馮友蘭認為,天地境界的“覺解”包括人生規律、道德規律并且把它們看作“天理”和“天道”,“覺解”了“他的生活,以及實際事物的變化,又都是道體中所有底程序”,即“整個底太極”和“整個底無極”,[1]627“不但覺解其是大全的一部分,而且自同于大全”,[1]635從而“從大全、理及道體的觀點,以看事物”,[1]630在這里人道被看作天道,人倫被看作天倫,人的生活活動所形成的規律被等同于宇宙秩序,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取向。但是,宇宙運行規律是什么?在人類文明的早期階段,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是,以人的形象設計出神,賦予自然以神的屬性,把自然和宇宙神秘化,形成人類早期文明中的自然崇拜觀念,馮友蘭承認,“同天的境界,本是所謂神秘主義底。”[1]637對于自然崇拜,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由于“幾乎還沒有被歷史的進程所改變”,“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它的關系完全像動物同它的關系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服從它的權力,這是對自然界的一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3]35
再次,馮友蘭的人生境界思想帶有承認社會外在性和整體性的整體主義缺陷。馮友蘭對自然境界的解釋是,“順才或順習底”,[1]568“雖生活于天地間,而不覺解其是生活于天地間”,“雖生活于社會中,而不覺解其是生活于社會中。”[1]569他對道德境界的闡釋是,“人在社會中,必居某種位分”,“此某種位分,即表示其人與社會的關系,并決定其對于社會所應做的事”,因此,“凡社會的分子,在其社會中,都必有其倫與職。”[1]608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到,在馮友蘭看來,社會是先于個人并且外在于個人而存在的。先于個人并且外在于個人而存在的社會使個人有了具體的“位分”和“職”。但是,馬克思早在1844年就指出:“首先應當重新避免把‘社會’當作抽象的東西同個人對立起來。”[2]122經過深入的經濟學研究,他更深刻地指出:“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的,而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系和關系的總和。”[6]220也就是說,社會不僅是實體范疇,也是關系范疇,即標志人的社會生活空間的關系范疇。作為實體的社會如何可能?沒有人的內在的豐富與發展,社會就是外在于個人并與個人相對立的存在,個人被整合在血緣宗法的秩序之中,整合在“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7]194的政治國家所確立的專制秩序之中;有了人的內在的豐富與發展,就有血緣宗法關系的瓦解和地域隔絕狀態的突破,代之以普遍的社會分工關系、交換關系和交往關系。在中國傳統社會里,重視社會整體、忽視個人及其價值,在江山、社稷面前稱不出個人的重量。忽視社會存在的歷史性,看不到社會分工的歷史性,單純強調“盡職”、“盡倫”仍然是傳統社會的整體主義道德原則。
最后,馮友蘭的人生境界思想帶有非歷史主義的缺陷。人是具有系統價值規定性的存在者,因而是歷史的存在者,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是分工合作關系、分配交換關系和社會交往關系,人的生活本身就是社會的分工合作過程、分配交換過程及精神性的和休閑性的社會交往過程。人生境界不僅取決于人自身的豐富性和社會普遍性,也取決于社會存在本身。社會存在本身是歷史的,基于人的政治身份而確立人的社會關系和職業位置,是以人的依賴性為特征的政治社會;基于對金錢的追求,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社會(自由市場經濟階段);而基于人自身的發展,則是“自由人聯合體”。在政治社會里,盡倫盡職的行為本身與其說是道德行為,不如說是等級制度強制規定并輔之以社會道德體系約束的行為;在市場社會里,人基于自己獨立的道德意志按照自由平等原則追求自身的利益不僅符合社會的道德要求,也符合社會的法律要求;在自由人聯合體里,人基于自身天性的充分發展而展開的社會生活,不僅擺脫了政治強制,也揚棄了拜物教,達到基于自我實現所呈現的審美意境。自然境界是本身沒有得到發展因而沒有反思的生活狀態,更是農業社會及工業社會中沒有得到發展的底層群體的生活狀態;功利境界是生活在社會中卻沒有意識到生活在社會中的個體自覺狀態,這種境界與其說是生活的社會狀態,不如說仍然是自然狀態。馬克思對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研究揭示了,以利己為動機的自覺意識和獨立意志展開的個人生活在總體上造成整個社會存在的外在性和異己性,造成社會存在的盲目、自發、無序狀態,這種社會狀態仍然屬于“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8]它表明:“人們還處于創造自己社會生活條件的過程中,而不是從這種條件出發去開始他們的社會生活”。[6]108
三、從人生四境界到人生三境界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闡述了,人是一定生產力的使用者,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并且是一定社會意識形態的生產者和改造者。但是,馬克思在他一生的理論探索中,一直都有關于人的能力、需要及感覺、激情、意志、目的等等的論述,這里稱之為人的價值規定性,按照人的價值規定性人還是個人能力、個人需要及個人意識和個人價值觀念的有機統一體,[9]這里的個人意識和個人價值觀念不是康德所說的人基于理性和自由意志自我確立的道德律令,而是個人在個人生活歷程中的情緒、情感、審美體驗和反思判斷逐步積累并積淀下來,在對社會普遍的思想道德價值觀念進行能動地選擇、過濾、組織、加工、“改造”(馬克思語)過程中形成的,并且由于個人的反思判斷而處于自我否定和自我調整之中,它引導個人能力的發展和發揮方向,確定個人需要的滿足對象和范圍,引導個人休閑性的和精神性的社會交往,確定個人精神生活的內容和范圍。這里從人的價值規定性的豐富程度和實現程度探討人生的境界。人的價值規定性的歷史實現呈現為三個層次,即個人價值、社會價值和歷史價值,[10]與此相應,人生境界有自我實現的審美意境、與社會同在的審美意境和與歷史同在的審美意境。
所謂個人價值是指,在個人意識和個人價值觀念而不是社會因素的引導下實現個人能力的個性化發展和個性化發揮、個人需要通過社會交換達到的個性化滿足,及在社會的分工合作過程中、在社會交換過程中和在精神性的和休閑性的社會交往過程中實現的個人意識和個人價值觀念的個性化表現和外化,基于個人價值的這種片面發展、也是個性化發展所達到的自我實現。當然,如果有個人能力的全面發展,并且有社會分工領域的開放性,而且還有個人意識和個人價值觀念的獨立性及社會思想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個人能力的發揮就表現為個人自由游走于社會分工的各個領域,并且自我確定個性化發揮的領域;如果有社會消費資料的豐富,并且有社會的再分配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個人需要的滿足經過社會交換而達到的多樣化滿足,并且在此基礎上自我確定個性化的消費對象和消費范圍;如果有社會文化觀念建構的多元化,并且有自由、自覺而獨立的個人意識和價值觀念的引導,個人的精神生活和休閑消費文化生活就真正表現為個人的精神家園、個人的“自由王國”(馬克思語)。綜合三方面,人的感性活動、個人的生活過程就達到馬克思所說的“自由自覺的活動”和“自由個性”,這就是個人價值的全面發展所達到的自我實現。個人價值的個性化發展和全面發展所達到的自我實現使人的生活活動、人生呈現為伴隨著激情涌流審美體驗的審美意境,在這種審美意境中,時空隱退了,一切外在性和異己性都消解了,自我也隱退了。
但是,人的感性活動的社會展開展現了人的社會境遇。個人能力的發展和發揮確立了個人與他人之間的分工合作關系,從而個人能力的發展和發揮本身就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分工合作過程;個人需要的滿足確立了人與人之間的分配交換關系,從而個人需要的滿足過程本身也就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公平交換過程;同樣,個人意識和個人價值總是在與他人的交往過程(包括分工合作過程和分配交換過程)中的情緒、情感、審美體驗和反思判斷的積淀,并且通過消費社會的精神文化產品而選擇、過濾、組織、加工、“改造”社會普遍的思想道德價值觀念的過程中形成的,人與人的社會交往過程(包括分工合作過程和分配交換過程)本身也是人與人之間的思想道德價值觀念的碰撞、沖突、互動的過程,即人格尊嚴的互動過程。個人意識和個人價值觀念對這種具體的社會境遇的自覺向個人提出的絕對律令是:在個人能力得到個性化發展和發揮的同時必須為處于分工合作過程中的他人之個人能力的個性化發展和發揮創造條件,至少留下空間;在個人需要得到個性化滿足的同時必須為與他處于分配交換關系中的他人的個人需要的個性化滿足準備生活消費資料;在個人意識和個人價值觀念得到表現和外化的同時也必須為處于交往關系中的他人之個人意識的個人價值觀念的表現和外化留有空間、創造條件,——總之,在自我實現的同時也自覺地為處于社會交往關系(分工合作關系、分配交換關系及精神性的和休閑性的交往關系)中的他人也能夠達到自我實現創造條件,為他人的自我實現提供日益廣闊的社會空間,這就是人的社會價值的實現,它表現在:在自我實現的同時造福他人,有助于或者推動社會共同體的全體社會成員共同發展、共同享受社會的文明成果,即孟子所說的“達則兼濟天下”。伴隨著個人的社會價值的實現是這樣的審美體驗,既有自我實現所帶有的激情涌流的審美體驗,也有成就他人、造福社會的成就感,并且知道由于自己的創造,他人的生活也一樣處于自我實現的審美體驗和審美意境之中。由于個人意識到這一點而呈現為個人審美意境的社會擴展,即“我”的審美意境擴展為“我們”的審美意境、自覺到“我”與社會同在的審美意境。人與社會同在的審美意境,與馮友蘭的道德境界的共同點是自覺到人的社會屬性并且自覺造福他人與社會,區別在于它是以人的價值作為絕對原則,而道德境界是以社會的道德觀念作為原則,這樣就缺乏對社會的道德觀念的批判。
人的感性活動的歷史傳承展現了人的歷史境遇。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1]他還指出:“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數量的生產力總和,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關系,都遇到有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3]43我們不是處于“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孤獨境遇中,而是處于“前有古人,后有來者”的生命傳承鏈條之中。在歷史的“當下”,人的創造活動,他的需要的滿足,他的個性意識和價值觀念的形成,都是在前人所創造并留傳下來的物質、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實現的;個人能力的形成基礎,個人需要得以滿足的直接物質條件,個性意識和價值觀念得以形成或激發的思想資源,是前人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這些資源和成果并不僅僅屬于哪一代人,而是屬于每一代人,是生命的存在和延續的永恒的依托,是“自由個性”的歷史生成所依托的共同資源和條件。個人意識和個人價值觀念對這種歷史傳承的自覺向個人提出的絕對律令是:人在其現世的生活過程中,其任務不僅僅是使用和消費從前人那里繼承下來的這些資源和成果,還要維持和保護這些資源和成果,并且使其不斷得到增殖或者完善,并留傳給后代。這樣,后代人才能由于他的自我實現、他的創造而在更豐富的資源環境條件下、在更高的歷史起點上展開更豐富的社會生活。這就是人的歷史價值的實現,它表現在,人在繼承前人創造的條件下實現其自身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同時還推動社會資源的積累與增長,推動社會的制度設計的完善,推動社會的思想文化觀念的進步,自覺地為歷史的持續發展與進步、為后代創造和積累更豐富的物質、文化、制度和社會條件,即有意識地為“自由個性”的歷史生成奠定基礎和創造條件。因此,人活著,既要“擔當生前事”,也要“計身后評”;既要做到“瀟灑走一回”,又要做到“人過留名,雁過留聲”;對“粉身碎骨”誠然可以持保留態度,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歷史情懷是絕不可無的。伴隨著個人的歷史價值的實現是這樣的審美體驗,不僅有自我實現、造福社會的激情涌流的審美體驗,還有開創歷史、造福后代并被后代“確證”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有納入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的歸宿感,這樣個人自我實現的審美意境就超越了個人生命的有限界,擴展為“我”與生命同在、“我”與歷史同在的審美意境。馮友蘭的天地境界強調的是人是宇宙的成員,人自覺為宇宙做事,但是這里的宇宙是指生生不息生命之流嗎?是指人的歷史傳承之鏈嗎?如果是,那么這里的人與歷史同在的審美意境就與天地境界就有一致之處。但是,“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的含義不僅是歷史吧?更不要說為宇宙做事在內容方面含混不清了。
[1]馮友蘭.貞元六書(下)[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6.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60.
[4][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56.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 1979.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人民出版社,1965:194.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人民出版社,1962:9.
[9]鄧曉臻.“現實的個人”之人本維度及其與歷史維度的關系[J].甘肅理論學刊,2005,(1).
[10]鄧曉臻.存在:價值的歷史實現形態[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7,(5).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61:121.
B26
A
1002-7408(2011)03-0100-03
鄧曉臻(1970-),男,安徽宿州人,哲學博士,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講師,從事唯物史觀研究;溫立武(1964-),男,山東萊陽人,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責任編輯:宇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