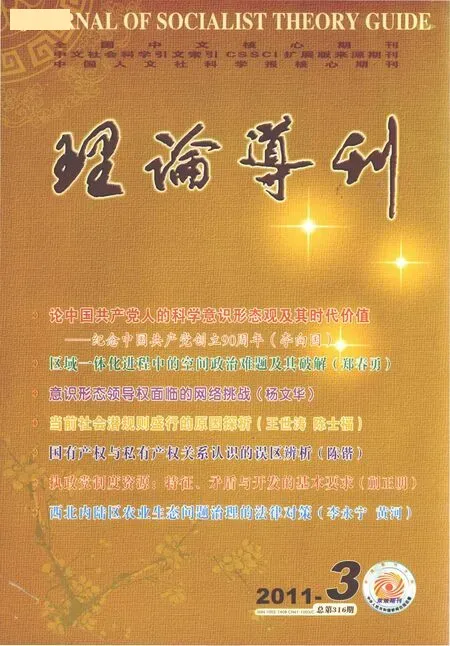拉美國家收入分配問題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馬強,孫劍平
(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南京210094)
拉美國家收入分配問題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馬強,孫劍平
(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南京210094)
拉丁美洲國家是最早開始工業化、現代化實踐的發展中國家。收入分配不公一直是困擾一些拉美國家的重要問題。我們必須在吸取拉美國家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吸收借鑒當代世界的先進發展觀念和理論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論和實踐模式即中國模式。
拉美國家;收入分配;實踐
拉丁美洲國家是最早開始工業化、現代化實踐的發展中國家。一方面,拉美的現代化進程確實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多數時期,經濟都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在拉美的發展過程中始終伴隨著嚴重的貧困問題,貧困以及由貧困引起的各種社會問題已經成為拉美發展的嚴重掣肘。[1]而收入分配不公一直是困擾一些拉美國家的重要問題。
一、拉美國家收入分配的特點及其后果
拉丁美洲經過三個階段的發展,取得了巨大進步。從1945年~1980年,拉丁美洲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到了5.6%,并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加入了世界中等收入國家之列。2002年,拉美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了3280美元,低于上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但高于下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拉美各國自然環境不盡相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因此對整個拉美地區的收入分配狀況目前還缺乏全面系統的數據。盡管如此,依據國際金融機構和各國學術界對拉美地區不同時期基尼系數、收入分配差距、貧困人口數量等指標的研究和估測,仍可大致勾勒出這一地區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歷史概貌和現實狀況。
據美洲開發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90年代,世界各國的平均基尼系數為0.4,而在拉美地區,除牙買加(0.38)外,其他國家的基尼系數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11個拉美國家的基尼系數高達0.5,遠遠高于當時的世界平均水平。聯合國拉美經委會的統計年鑒數據顯示,在3個拉美大國即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中,2005年占總人口10%的高收入者獲得的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42%-51%,而占總人口20%的低收入者獲得的收入僅占國民總收入的2.5%-3.7%。其中,在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巴西,1999年基尼系數曾超過0.64。90年代后期的巴西經濟增長雖使國內收入分配形勢稍有好轉,但2005年的基尼系數仍高達0.613。[2]拉美地區的貧困人口數量一直居高不下,就是在經濟發展取得長足進步的同時,貧困問題反而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一方面,拉美國家的貧困人口不斷增加。據拉美經濟委員會統計,到2000年上半年,38%的拉美人是窮人。有的拉美國家,處于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甚至超過50%。另一方面,拉美國家的貧富懸殊不斷擴大。國家的經濟增長需要不斷擴大內需,內需不足將帶來一系列問題。一般來說,收入差距的擴大達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社會消費力不足會導致嚴重的需求不足,國家經濟增長將完全失去動力。這一現象在拉美國家,比如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魯等比較普遍。最近十幾年,在經濟增長的推動下,拉美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和總體形勢雖有不同程度的逆轉,但還沒有跡象表明,這種暫時性、階段性的好轉會促成整體性、根本性的改善。
大多數時期的經濟增長伴隨著幾乎每個時期都存在的嚴重貧困問題,這種不協調現象已經成了拉美經濟發展的區域“特色”。在拉美長期貧困背后,深刻影響的是拉美經濟發展自身,帶來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不協調等一系列發展困境和問題。貧困背離了人類的基本生存原則,在拉美引起極為不良的后果。伴隨著貧困和收入不公的加深,拉美的販毒、走私、綁架、兇殺等暴力活動也日益突出,每年因犯罪蒙受的經濟損失高達300億美元,相當于地區國民生產總值的2%。貧困還使拉美出現了政局動蕩,構成了對穩定的威脅。與此同時,拉美許多國家貪污腐敗之風盛行。而貧困帶來的其它方面損失,如對社會凝聚力的損害,則難以用金錢來衡量。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會像拉美國家一樣因為收入分配極端化而引起廣大的社會中下階層通過政治訴求以加強政府對社會公正問題的關注。收入分配不公本來是反映出國家經濟政策上存在著不合理的問題,但是,在拉美國家收入分配上的極度不公已經演變成政治問題。例如,2001年阿根廷爆發貨幣危機后,緊跟著引發了經濟危機,進而導致社會動蕩和政治危機,一個月內竟然五易政府。阿根廷現象深刻地揭示了收入分配、貧困與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之間的關系,說明了若不關注收入分配問題,就會導致一系列的惡性循環:貧困加劇、經濟低水平徘徊、社會動蕩和政治不穩定,會使國家付出了高昂的政治成本和社會成本。
二、拉美國家收入分配不公的成因分析
拉美國家的收入分配格局從殖民時期形成至今已經達到了極端化程度,這給拉美國家帶來了日益嚴重的貧困問題,而且深刻地影響了拉美國家的經濟健康發展,導致社會動蕩不安和政治信任危機。具體分析,造成拉美國家收入分配極度不公的既有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歷史因素,也有拉美國家現代化進程中一系列的制度因素。
1.發展觀念存在嚴重缺陷。拉美貧困問題的根源在于經濟增長與社會全面發展之間的脫節,歸根結底,這是拉美發展觀念的嚴重缺陷所造成的。一些長期在拉美流行的發展理論,如“蛋糕論”、“積累優先論”、“發展主義”理論等,都割裂了經濟增長同結構改善、經濟發展與人和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用這樣的發展觀念指導實踐,必然產生嚴重的后果。導致“拉美陷阱”的最主要原因,是找不到新的增長動力。經濟增長方式也存在較大的問題,它們走的是重工業、大型企業和進口替代的發展道路,導致大量人口失業,貧富差距不斷拉大。
2.發展格局不協調。一是工業發展與農業發展不協調。拉美國家為了加速經濟增長,長期以來把重心放在工業上,忽視甚至歧視農業的發展。相應的政策使得農業長期凋敝,從而導致低收入階層、特別是大部分農村居民陷入貧困之中,而農業的凋敝又迫使農民移居城市,導致其城市人口膨脹、城市貧民增加。二是工業內部發展不協調。拉美國家普遍有歧視勞動密集型工業發展的傾向,造成了勞動密集型工業發展緩慢、就業減少,延誤了勞動力轉移的過程,而勞動力供給過剩使資本家能夠最大限度地壓低工人工資,這就導致了低收入階層大量存在;剩余價值集中于少數資本家手中,從而造成了收入的巨大懸殊。三是經濟發展與城市化不協調。拉美地區是世界上城市化最快的地區,但拉美的城市化屬于一種“超前”現象,與它的經濟發展水平并不相適應。城市無法為急劇膨脹的居民提供就業及其他生存與發展的條件,從而造成更加尖銳的社會問題。四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協調。拉美的社會政策具有相當大的脆弱性,表現在:社會開支不足及其分配不合理;社會保障制度存在嚴重缺陷;教育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拉美的教育對少數人高度集中,窮人得不到良好的教育,這也是一些國家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之一。[3]五是各地區發展不協調。經濟活動高度集中于一兩個地區是拉美國家的普遍現象。
3.土地分配不公平。在導致收入分配不公的諸多制度因素中,最根本的當屬生產要素占有制度。拉美地區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最初產生,即與該地區歷史上由大地產制造成的土地占有高度不平等有密切關系。拉美的大地產制形成于16-17世紀,是歐洲殖民主義統治時期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在大地產制下,統治者和上層階級憑借權力和武力占有拉美國家的大部分土地,進而幾乎完全壟斷拉美國家在咖啡、棉花、礦產等各經濟部門的生產和出口,從中獲得了豐厚的壟斷經濟利益。在這種壟斷性的政治權力之下,政治變成上層階級的游戲,權力淪為赤裸裸的利益工具。在上層階級的操縱下,不僅土地不公平占有獲得的經濟利益被合法化,而且由上層階級制定的各項經濟、政治和社會政策也都是為其自身利益服務的。大地產制因而成為拉美社會早期分化和不平等的制度根源。一些國家在獲得獨立后進行過“自由改革”,試圖通過建立土地市場和勞動市場為資本主義發展創造條件,但各國上層階級不斷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財富,大肆掠奪土地,使土地進一步集中,大量農民失去了土地。生產要素占有的日益集中使業已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進一步加劇,土地問題成為拉美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
4.工業化和城市化畸形發展。拉美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對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和地區間的分布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也是導致如今拉美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重要原因。拉美國家早期工業的發展是在19世紀后半期初級產品出口繁榮的帶動下開始的,主要表現為初級產品加工業和部分滿足內需的制造業得到發展。與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同,礦產資源的開采和土地資源的開發具有資本密集型特點,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較小。早期工業化的這一特征提高了資本的收益,卻極大地限制了就業規模的擴張。加上當時勞工制度的局限性,勞動力價格被大大壓低。19世紀后期,拉美城市化進程出現加速趨勢。城市化進程的動力來自外部,主要受初級產品的出口繁榮和大量歐洲移民涌入的推動。由于工業發展尚處于初期階段,這一階段城市的發展“主要取決于這些城市及它們所在的地區被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程度”。[4]易于進行國際貿易的沿海城市和地區的經濟得到迅速發展,而由于受地理環境和交通條件的限制,內陸地區和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十分緩慢,從而在沿海與內陸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出現了明顯的經濟增長鴻溝及與之相伴隨的區域間收入差距的擴大。集聚性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確使主要拉美國家的經濟得到較快增長,但地區間和城鄉間的發展失衡卻明顯加劇。
5.新自由主義改革虛假繁榮。在新自由主義的各項改革中,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收入分配效應最不明顯,但其影響卻不容忽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只注重刺激經濟增長,忽視社會公正,使收入分配格局更加不合理,造成城鄉收入和人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導致地區不平衡問題進一步惡化,貧富差距懸殊,貧困化問題進一步加重,進而引起社會混亂和社會中下階層的不滿。同時,金融自由化改革加大了宏觀經濟的脆弱性,引起經濟增長的劇烈波動。在多數拉美國家,隨著結構性失業的上升,最高收入階層和最低收入階層的兩極分化實際上進一步加劇,新自由主義改革初期的虛假繁榮是不可持續的。
三、對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啟示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我們應吸取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避免在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走彎路。
1.堅持民本思想。一個國家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和采取怎樣的政策必定基于其執政黨的指導思想和執政理念。拉美國家先增長、后分配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在拉美過去100多年的現代化進程中,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發展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與此同時,由于拉美國家指導理念上的偏差、政策運用的失誤造成人口與日俱增,大量的人口苦苦掙扎在貧困邊緣,致使社會問題和矛盾日益突出。“拉美陷阱”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的惡化。而在我們今后的發展中,收入分配狀況將會不斷改善。這一方面由發展階段決定,勞動力短缺推動工資上漲;另一方面,政府對收入分配重視程度很高,一直致力于縮小收入差距。對于我們來講,適應新階段發展的新要求,開辟發展的新思路,拓展發展的新空間,必然要求我們進一步落實科學發展觀。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說明,一個國家的執政黨必須從具體國情出發,善于抓住不同歷史時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始終以民本思想為原則,確立執政黨的執政理念和追求目標,堅持科學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2.加強政府社會功能。拉美國家過去幾十年的經歷證明,發展不會自動導致社會公正。無論是在六七十年代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還是在90年代新自由主義改革時期,拉美國家無視甚至放縱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導致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不斷加劇的重要原因。[2]中國應吸取拉美國家的教訓,避免重走拉美國家“沒有再分配的增長”(growth without redistribution)的老路,使政府在平衡收入分配、實現社會公平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當前尤其要正視資產價格波動和教育、醫療不合理收費對中低收入家庭生活的影響,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房價和物價過快上漲,加大治理藥價虛高的力度;盡快糾正住房、教育、醫療改革中過度市場化的傾向,強化政府公共責任;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養老、醫療、住房保障體系,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考慮地區發展的差距,有必要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對貧困落后地區在初級醫療、初級義務教育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推動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從長期來看,改善收入分配需要政府加快革除阻礙社會公平的體制性問題,特別是要嚴厲打擊各種形式的腐敗現象,消除經營壟斷,整頓分配秩序,強化稅收調節,從而從根本上遏制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表明:不能改善收入分配不公就不能減少貧困,就要付出高昂的經濟代價、政治和社會成本,社會就不能得到可持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拉美國家過于依賴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來解決社會問題,但是事實證明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總是有利于強大行為者的利益,弱勢群體往往是市場競爭的弱者而受到傷害,因此,依靠市場化并不能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相反卻加大了貧富差距,收入分配更加惡化。要解決上述問題,必須加強政府的社會功能,發揮政府的作用。政治決心、政策導向并輔以財政上的支持是解決貧困問題的首要條件。因此政府必須把社會政策納入國家發展的總體框架,發揮政府的作用,動員各方力量解決社會問題,使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社會成員。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如果一味地認為問題出在再分配上,把過多的精力都用于再分配,走到極端反而會傷害經濟增長。歷史上任何國家收入分配的根本改善,都源于就業的擴大和人口的自由流動,沒有一個是主要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3.重視發展和改革模式。事實證明,一個國家或社會堅持什么樣的發展觀對它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同的發展觀往往導致不同的發展結果。發展和改革模式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對收入分配產生影響:[5]一是不同發展模式對效率和公正的不同偏好決定了不同的初次分配格局。一旦初次分配出現嚴重失衡,再通過其他方式恢復社會公正,需付出很高的經濟代價和社會代價;二是發展和改革模式決定了生產要素在區域和社會群體間的配置,這種配置如果出現失衡,將直接導致收入分配的失衡;三是發展和改革模式的優劣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如果一種發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經濟增長的劇烈波動必然會造成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拉美國家收入分配不公的現實表明,要改善收入分配狀況,建設和諧社會,就必須扭轉重效率輕公平的政策取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對于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而言,必須特別關注地區間和城鄉間的發展平衡問題,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對貧困地區和落后地區應在政策、資金和人才方面給予必要的傾斜和支持。由于低收入者相對高收入者在經濟波動中更脆弱,更易遭受失業和通脹的打擊,因此,要改善收入分配,必須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在今后一段時期內,有必要進一步改善和加強宏觀調控,努力消除影響經濟增長的不穩定因素;四是發展模式必須充分體現生產要素占有的公平。拉美收入分配不公的現實再次說明,生產要素在收入分配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拉美國家之所以長期無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主要生產要素特別是土地的占有極不公平。中國未來要有效地抑制收入分配不公的趨勢,關鍵在于防止出現生產要素的不公平占有。
4.科學尋求效率和公平平衡。長期以來拉美國家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發展,等同于現代化,片面追求高經濟增長率。從理論來說,效率優先固然在競爭的市場領域里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是提高經濟效益的主要動力,但是對于社會進步而言,只注重效率,長期忽視公平將導致社會問題積重難返,破壞社會和諧的政治基礎,削弱國家的綜合競爭力。拉美教訓說明了一個國家要實現社會經濟的共同發展,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率是無助于國家整體競爭力提高的,必須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發揮國家的作用,通過宏觀調控制度、財產轉移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稅收制度等對國民收入分配制度進行重大調整,從制度的層面上,確立效率和公平的平衡點,推動社會公平和經濟增長的共同發展。
[1]伯恩斯.簡明拉丁美洲史[M].王寧坤,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368.
[2]江時學.拉美國家的收入分配為什么如此不公[J].拉丁美洲研究,2005,(5).
[3]人民網.科學發展觀形成的國際背景[EB/OL].2010-02-09.
[4][美]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M].馮明方,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14.
[5]蘇振興,袁東振.發展模式與社會沖突——拉美國家社會問題透視[M].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
F170.47
A
1002-7408(2011)03-0108-03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08JA790072)。
馬強(1970-),男,江蘇南通人,副研究員,博士生,研究方向:人力資源管理;孫劍平(1953-),男,江蘇鎮江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人力資源管理。
[責任編輯:宇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