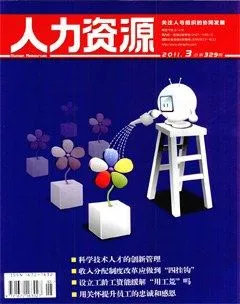東方財富觀箴言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道德經·第四十四章》
名聲與生命相比,哪個更珍貴?生命與財物相比,哪個價值更大7獲得名利與失去生命相比,哪個有害々過分地追求名利必定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過多地積藏財物必定要招致慘重的損失。所以,知道滿足就不會受到屈辱,知道適可而止就不會招致危險,如此才可以保持長久。
圣人不秘,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道德經·第八十一章》
圣人沒有私藏,盡其所有來幫助人民,自己反而更充實:傾其所有給與人民,自己反而更富有。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道德經·第九章》
滿屋子的金玉財寶,并不能長久擁有;身處富貴而驕狂自大,等于給自己留下禍殃。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道德經·第十二章》
稀有難得的東西,會使人行為不軌。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經·第四十六章》
禍患莫過于不知道滿足,罪過莫過于貪得無厭。所以知道滿足為止的人,永遠是滿足的。
儉故能廣。《道德經·第六十七章》
儉嗇,所以能寬廣。
知足者富。《道德經·第三十三章》
知道滿足的就是富有。
少則得。多則惑。《道德經·第二十二章》
少取反能多得,貪多反而迷惑。于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篇》
孔子說:“富裕和顯貴,是人人所希望得到的,若不是按正當的方法得到它,君子也不要。貧困和下賤,是人人所厭惡的,但若不是按正當的手段來擺脫它,君子也不擺脫。”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篇》
用不正當的手段得到富與貴,對我來說,就如同天上的浮云。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論語·憲問篇》
貧困卻沒有抱怨,很難:富有卻不驕縱,容易。見利思義。《論語·憲問第十四》
看到利益就想到是否符合道義。子貢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論語·學而篇》
子貢說:“貧窮卻不諂媚,富有而不驕傲,這樣的人怎樣?”孔子說:“好是好,但還比不上貧窮卻能明道自樂、富貴卻能節制好禮的人啊!”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大學·第十章》
發財致富有一個大原則:生產的人多,消費的人少;生產的速度快,使用得緩慢:那么國家的財富就能經常保持充裕了。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大學·第十章》
有仁德的人,以財物幫助他人,來充實生命,完善自我,不仁德的人,卻以犧牲生命去聚斂財富。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大學·第十章》
美德是根本,財富是末梢。如果國家表面講道德,實際上貪婪財富,那么就會出現民眾相互爭利、搶奪財富的事情,所以,財富聚集在國家,平民百姓就會離散,財富散落在民間,民眾就會歸附國家。
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禮記·大學》
國家不應該以利益為根本利益,應該以正義為根本利益。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富國》
使國家富足的途徑是:節省費用,使百姓富裕,并妥善貯藏好剩余的財物和糧食。
富貴雖樂,一切無常,五家所共,令人心散,輕躁不定。《大智度論》[注:五家是指水災、火災、官府、盜賊、不肖子]佛告善生:六損財業者,一者耽湎于酒,二者博戲,三者放蕩,四者迷于伎樂,五者惡友相得,六者懈墮。是為六損財業。《善生經》
一個人用錢應該合理,并且跟他的收入成比例,不可浪費也不可吝嗇。不可處心積慮貪圖財富,也不可揮霍奢侈。《佛陀的格言》
在家人應該把財產分為四份:一份供日常使用,兩份作為儲蓄或施舍之用,另—份留作緊急備用。《佛陀的格言》
財富會毀滅愚笨的人,但不能毀滅想斷除煩惱的人;當愚笨的人渴愛財富時,他不但害了自己,同時也損了別人。《佛陀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