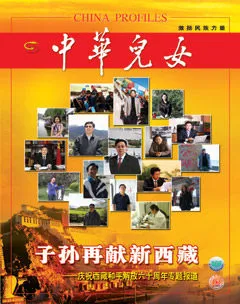格桑 一脈忠誠在高原
2011-12-29 00:00:00華南
中華兒女 2011年10期



西藏自治區政府副秘書長格桑,是十八軍進入西藏的第二代。上至父母、下到子女,格桑家扎根在雪域高原半個多世紀、跨越三代人。在格桑心里,祖籍四川、出生地北京,似乎都不如高原西藏親切,充滿了赤誠和情感。
父母的進藏故事
1951年初,格桑的父親計美鄧珠在四川康藏地區加入了解放軍,正式成為十八軍進藏部隊中的一名藏族小戰士。就在這個時候,家在四川康定地區的姑娘卓瑪也光榮地入伍準備跟隨解放軍的隊伍進發西藏了。
彼時這兩個四川藏區的小戰士相互之間還沒有什么交集,或許更想不到跟隨解放軍的隊伍進軍西藏、和平解放西藏之后,所改變的不僅是他們個人的生活,使兩人結為終身伴侶,更將他們一生的事業和命運,與雪域高原的新發展緊緊相連。
其實早在1949年,計美鄧珠就已經是一名進步青年,他參加了“東藏民主青年同盟”,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康區的外圍組織。因為一直要求進步,計美鄧珠于1951年初,解放軍進藏前,先期被派到北京,在中央民族學院進行簡短培訓,主要就攝影方面的技能和黨的民族政策等方面進行學習培訓。
卓瑪的出身和經歷似乎更富有傳奇色彩。卓瑪的父親,是國民黨時期蒙藏委員會藏文翻譯官。在九世班禪轉世和十三世達賴轉世的過程中,曾擔任藏文翻譯,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1949年7月,震驚中外“驅漢事件”發生,國民黨駐藏機構的官員眷屬和其他漢族人員200多人,被嚴密監視,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驅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經海路遣返回內地。卓瑪的父親,也在這事件中被逐出西藏。不過,他并不反對女兒再次進藏并且為了國家的統一而解放西藏。卓瑪在重慶進行進藏前培訓時,他還曾去看望女兒。
后來,卓瑪也被送到北京學習。兩個人在北京相識,攜手一生。因為計美鄧珠的工作原因,卓瑪帶著全家幾次輾轉北京、拉薩兩地,最終留在雪域高原。直到退休,老兩口才回到成都安度晚年,卻仍舊把所有孩子都留在了高原上。
“父親用手中的攝影機記錄西藏的變遷”
計美鄧珠是新中國第一代藏族攝影師。身為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的高級攝影記者,計美鄧珠大半輩子的時間里都在西藏進行拍攝,全藏區73個縣,到處都留下了他的足跡。現在所能看到舊西藏最野蠻、最殘忍、最血淋淋的農奴制、新西藏民主改革之后的很多新貌,都是通過他和澤仁、扎西旺堆等幾個同事一同記錄保留下來的。
這是艱苦卓絕的工作。
西藏剛剛和平解放時,艱苦是所有進藏干部最為深刻的記憶。前蘇聯的嘎斯69汽車,已經是最高級的汽車,只有自治區領導才能因公使用。而拉薩之外的地區,條件更是難以想象。在格桑的記憶里,父親每次下鄉拍攝,都要準備很多很多工具,包括攝影器材、反光板,小到繩子、修理工具都不能缺。他跟同事的公務用車就是一輛破吉普,他們既要當司機,又要當攝影師,還有兼任修理工。藏區路況本來很差,高原地區氣候又變化無常,車在路上拋錨是家常便飯。更有時候,因為當時西藏剛剛和平解放,叛亂分子和境外派來的特務仍在不時騷擾新生的縣、鄉政府,情況十分復雜,每到一地,當地人員都對外來者十分警惕。1960年,計美鄧珠和同事到日喀則謝通門縣拍攝《高原短途運輸》新聞主題。因為兩個人都只帶了記者證,沒有帶地區的介紹信,加上整天騎馬走路,樣子十分狼狽,而且為了防身,每人還背著一只長槍和一只短槍,自然引起當地干部的注意。到了縣城的時候,兩個人已經走了兩天,又餓又累,一頓吃了一百多個餃子,更引起他們的懷疑。計美鄧珠和同事怎么也證明不了自己,當晚就被軟禁在一間又黑又小的房子里,直到縣里與地區、拉薩電報聯系核實,明確他們的身份后,才配合拍攝工作。
這也是一項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囿于通訊,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的攝影記者們鏡頭所對準的,都是國家建設中的新變化、新經驗,計美鄧珠他們所拍攝的更是如此。每次電影之前所播放的新聞簡報、祖國新貌,就成了全國人民了解國家進步的窗口。因此,即便再苦,計美鄧珠也從未想過放棄。
已過半百,格桑仍舊感念于父親留給自己的這種精神與情懷。
2010年12月15日,西藏墨脫公路控制性工程——嘎隆拉隧道順利貫通。2012年,通往墨脫的等級公路將正式建成通車,墨脫不通等級通路的歷史將就此終結。而今,已經有兩條季節性公路通往墨脫,越來越多迫不及待的好奇的游客探訪這朵“白蓮花”,然而當年,揭開墨脫真實面紗的就是計美鄧珠和同事。
“他們是步行進入墨脫的,背著攝影器材,邊走邊拍。”1981年,計美鄧珠和同事次登,踏上了墨脫采訪之旅。雖然行前已經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和物質準備,進入墨脫之難還是超出他們的想象。進去的時候已經是5月,雖說是進入墨脫的最佳季節,但是徒步從米林縣境一個叫派的地方出發,翻越多雄拉雪山,走路三天多,到達雅魯藏布江下游江畔的八崩鄉,再從八崩順江而上,進入墨脫縣城,這一路地勢險要,氣候變化無常,經常發生雪崩或被雪風阻擋,沒有當地熟悉情況的向導,沒人敢去。途中,還要有幾天時間是經過無人區,大量的螞蝗叮得人鮮血直流。
那時條件艱苦,經濟上也很緊張。拍墨脫,計美鄧珠和同事他們只有5000元的拍攝經費,兩個人手上總共才有20多盒30米的16毫米膠片,再多的美好,也要精打細算,節省拍攝,精心策劃之后,才能開機。5月進入墨脫,8月出山來,歷時3個多月的艱苦跋涉,終成首部忠實記錄墨脫的紀錄片《綠色墨脫》,第一次較全面完整地向國內外展示了西藏高原迷人的風光和獨特的民俗,引起了外界的極大關注,對于宣傳西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白蓮花”墨脫終于將自己的風采向世人展示了出來。
在西藏攝影站工作的幾十年中,計美鄧珠拍攝了大量的有關西藏的新聞主題,用真實可信的鏡頭向世人展現了封建農奴制度下百萬農奴悲慘的生活和民主改革后翻身農奴當家作主人的喜悅之情,不少影片和新聞主題獲得了各種獎項。
1985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授予西藏站計美鄧珠等四個老同志嘉獎,表彰他們在新聞電影事業上所作出的優異成績。
“我用忠誠守衛國家的安全”
1961年,格桑出生在北京。
一歲時,父親計美鄧珠正式到新影廠駐西藏站工作,格桑也跟著父母進藏了。至今,格桑已在西藏度過了自己的半生。
格桑家是個大家庭,父親計美鄧珠共有兄弟姐妹13人,可是由于舊時生存條件實在太惡劣,最后只活下來三個。計美鄧珠是個十分孝順的人,在參軍有機會走出牧區的時候,就主動把兩個姐姐的四個孩子帶出來讀書,輾轉北京、拉薩,共同生活。因此從記事起,格桑就是在大家庭里跟父母和哥哥姐姐一起生活著。
從1962年到初中畢業,格桑在西藏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記者父親總是下鄉采訪拍片,格桑印象中,母親的身影格外忙碌。母親卓瑪也是十八軍進藏的小戰士,進步青年,入伍后先在康定民族干部學校學習漢語,后來當上了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為數不多的幾位漢語老師,當時很多上層進步人士都是她的學生。后來,卓瑪又在共青團中央工作了一段時間,因為要隨駐站的丈夫進藏,才調入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改學電影剪輯,后來就隨著丈夫進藏了。應該說,為了丈夫的事業,卓瑪將更多精力花在家庭中——照顧一個大家庭,周轉生活,負擔他們的衣食保暖和思想教育,但她從無怨言,默默地支撐著這個大家庭,對姑姐的四個孩子也視如己出,并將他們逐個培養成人。
改革開放之前,社會物質生活普遍貧苦,西藏更是如此。格桑在家里排行第七,在格桑的記憶中,那是家庭條件還算不錯,但兄弟姐們的穿著總是補丁摞補丁。可是父母無聲的教育,父親對工作的執著、母親待人的善良誠懇,還是給了他人生中最寶貴的財富和最甜美的人生記憶。
而在人生中的每一個階段,格桑也在父親這樣的思想指導和影響下做出自己的選擇。
1976年,格桑即將初中畢業,“文革”尚未結束,高考尚未恢復,求學無門成為格桑他們那一代青年人內心中最為苦悶的事情。恰好,一天上課時,部隊來招小兵,說是招到部隊后要送到南京政治學院深造。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招考很嚴格,陣勢也很大,“當時全校的男同學都被叫到操場上進行身體素質測試和才藝展示,同時還要參考學習成績。”格桑樣樣都排在前列,而且學習成績優秀,成為那一批被招入部隊的藏區僅有的10個小兵之一,而且是唯一的藏族。
然而之后不久,因為種種原因,格桑他們這批戰士不能去南京軍校學習了,而是要跟普通戰士一樣充大兵進部隊。條件肯定更艱苦了。“當時母親有點心疼我,不想讓我去了,可是父親不讓,他說既然組織上選中了你,就必須去!這是鍛煉,也是組織的信任,更會為你的人生留下最寶貴的經歷!”在父親這位十八軍老戰士對部隊的情結和對黨、對國家的崇高信仰,將自己的兒子“攆”進了部隊。
四年之后,格桑退伍,進入剛剛成立不久的西藏自治區旅游局,干過很多工作,甚至包括賓館房間整理,覺得有滋有味,大有作為,但是學習欲望從來沒有消退,得知可以高考了,格桑毫不猶豫報名參加。當年,格桑考中了西藏民族學院。“原本打算學英語專業,結果那一年因為招生太少沒法開班,我們都轉到了歷史系。”回顧自己的生活,似乎總跟最初的打算不合拍。不過格桑并不覺得有什么不妥,因為心懷的信念與理想始終如一,“這絕對來源于父親的言傳身教。”
又是一個四年。
1984年,格桑作為當時為數不多的大學生回到拉薩。現在回想起來,他似乎從未想過留在內地,一門心思要回到拉薩,建設新西藏。這個問題他跟很多同樣經歷的人交流過,幾乎所有像一樣的“第二代”們都是這樣想的。他把這歸結為一種情懷。
最初,格桑想回到旅游局工作,但是他被分配到西藏自治區宗教局。“當時我在局領導家里從晚上八點一直坐到半夜十二點,他也不同意放人。”領導給他的唯一理由是在西藏工作,民族宗教十分重要,要干好這一行可以大有作為。年輕的格桑那時并不是很理解,心里難免嘀嘀咕咕,但是知道領導是為了他好,也就踏踏實實地在宗教局里埋頭工作。
時值“文革”結束不久,全國范圍內的撥亂反正工作正在進行,西藏地區寺廟眾多,而“文革”時被保留的僅有9座,其余全部被毀,撥亂反正工作任務繁重。格桑那時的主要工作就是跟著時任局長赤來深入各地區對被毀寺廟進行調查摸底,“那幾年跑了五六十個縣,幾乎去了所有的寺廟,對寺廟和西藏宗教情況有了一定的了解。”這幾年的學習過程,幾乎決定了格桑日后的工作。
他開始站到反對極少數宗教分子分裂、保護宗教儀軌、維護國家統一的前線。十幾年來,格桑先后參與到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等幾個重點寺廟的整頓工作,還多次駐寺廟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都很有效果。而在格桑的心中,最為難忘的還是參與對十一世班禪金瓶掣簽的工作。這項工作差不多持續了兩年,1995年12月8日凌晨五點,在拉薩大昭寺釋迦摩尼佛像前,按照歷史的宗教儀軌,進行金瓶掣簽,由佛祖來神斷第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在黨中央、國務院、西藏自治區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44位佛教界高僧大德及各界代表的共同注視和見證下,“5點20分,喇嘛的誦經聲停了下來。一個身著淺綠色藏裝的藏族青年男子,從金瓶中取出如意頭的象牙簽牌,放在手中的托盤里,端到西藏自治區主席江村羅布面前,這是著名記者劉偉在《十一世班禪坐床記》一書中對當時格桑請各位領導驗簽時場景的描述。之后,格桑拿起用藏、漢文寫有堅贊諾布、貢桑?旺堆、阿旺南索三個候選靈童名單的紙條,仔細地各貼一面在簽牌上……格桑將名單逐一在簽牌上貼好,放進托盤里。
格桑端著托盤從國務委員羅干開始,依次讓生欽?洛桑堅贊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波米?強巴洛卓活佛、十七世噶瑪巴活佛、喇嘛?次仁和三個候選靈童的父母等先驗看并核察名簽,他們首肯無誤后;然后又依次讓在座的西藏自治區黨政領導驗看名簽。
最后驗看名簽的是國務院特派專員、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他驗完簽后,拿起托盤中細長的黃緞封套,將名簽套上。可能黃緞套過于細瘦,封裝每只簽,葉小文都用了一定的時間。這期間,整座大殿寂靜無聲,人們的眼睛都緊張地盯著葉小文的手。終于,葉小文鎮定地將三支名簽都裝進了黃緞封套,他抬起頭來,神色明顯輕松了許多。
江村羅布大聲宣布:“經審核,三名候選靈童的名單驗簽無誤,請封簽。”
后來只要談到此事,格桑總是萬分感慨:“能親歷西藏最高級的佛門盛事,終身難忘”。當然,重要的是此前多年在宗教局的積累。“沒有之前的積累,后面的那些工作都是拿不下來的。”在政府部門的不同崗位上工作這么多年,格桑總是部門里被借調工作時間最長的人,很多突發事件,都是派他出去處理。工作的時間多了,陪伴家人的時間自然就少了,不過對于格桑來說,做好工作義不容辭。
責任在三代人之間延續
計美鄧珠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在西藏當攝影記者,沒有對黨的事業的忠誠,沒有記者的職業道德,沒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是絕對不行的。這話,也是格桑聽父親講的最多的一句話。在他眼里,父親不止是這樣說說,更是在幾十年的工作時間里,恪盡職守地實踐。
小時候,格桑看到的,幾乎都是父親背著器材下鄉拍攝的背影。上到初中,格桑覺得自己也長成了大小伙子的時候,就主動要求跟著父親工作。“其實就是想給他們打打下手,跑跑腿。”直到若干年后,父親退休回到成都,一家人仍舊將工作放在第一位。格桑家里有不成文的規定,每到周末全家人必須要聚一聚,而逢年過節,更是要到父母家里報到,一家人在一起聚餐,其樂融融。母親特別愛吃格桑做的菜,他自己也笑稱自己的前世可能是廚師。要是誰不來,父親要生氣,不過要是誰有工作缺席,父親則一定要在第一時間里“攆”他走。“我這沒事,工作要緊!”格桑無數次聽到父親這么說他。
在家里,父親是表率。“理想和信仰總是決定著前輩們的追求和堅守,在他們那一輩人身上就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情懷。從他們一生的工作與奉獻中,能真切地感受到、觸摸到、學到、體會到。”格桑的幾個兄弟姐妹,都分布在不同的部門和崗位上,有的從文、有的從理、有的從軍,也都在父輩精神的感召下為新西藏建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工作后,格桑在與各族干部之間的交往和學習中充分感受到了這種責任和敬業精神。1985年,格桑入選第一批藏族統戰干部培訓班,到北京中央統戰部脫產學習一年。而西藏民主改革之后,在不同時期都有大批進藏干部、援藏干部為新西藏建設出力流汗,格桑跟他們在一起,多年來感悟更多。
“比如李作明, 他可以在同一個筆記本的左右兩面同時做筆記,一邊是藏文一邊是漢語,會開完了會議紀要也做完了,而且真的是藝術。”讓格桑時隔多年仍舊念念不忘的還有國家鐵道部原部長屠由瑞,論證青藏鐵路時他專門來沿途考察輪漲,他的筆記本真是一絕,一路下來記了六本,圖文并茂,畫的圖就像小人書一樣,地形、凍土和涵洞等等十分準確。
“這些老領導、老前輩的能力和作風,真是不得了。”格桑也努力地學著。國務院辦公廳和秘書局的同志來援藏,他總同他們一道工作,并從他們的身上學到很多寶貴的經驗和工作方法。總之,他總是在學習。漢藏之間的交流多,隔閡自然就少了。而且在他看來,不論在藏干部還是援藏干部,還是像他們一樣老革命留在西藏的第二代,大家的目標都只有一個,就是建設一個新西藏,責任感統一、目標一致,還有什么委屈呢?
現在,這種作風也被格桑遺傳給了女兒。女兒尕美卓美廈門大學法語系畢業后,恰逢西藏自治區公安部門特招,經過考試,女兒成了一名公安戰線上的戰士。初入隊伍時8個月的軍訓,格桑沒有心疼,讓她去充分鍛煉。加班是家常便飯,愛人心疼女兒,經常抱怨,格桑很坦然,她只要在工作,就讓她去忙吧。西藏和平解放60年來,格桑的父輩就是憑著這種精神和責任將一個新的西藏交到了格桑他們這一輩人手上,格桑說,他要繼續把這種使命傳承下去。他們的下一代,必須能扛起責任,肩負使命。
2010年上海世博會,格桑是世博西藏館(網上西藏館)副館長、西藏館駐上海世博園區辦公室主任,半年多的時間里,格桑親眼看到游客們帶著好奇走進“天上西藏”的大門,乘著模擬青藏線奔赴雪域高原,再看著他們被兼具雄渾壯美和珍奇秀麗的風光所震撼,被西藏的日新月異發展所驚嘆,“這是真實壯美的新西藏、幸福生活中的新西藏,發展變化中的新西藏。”半年多時間里,西藏館迎來了超過800萬的游客,格桑在場館里看著川流不息、面帶驚喜的人們,回味著父輩和自己一路走來的歷程,覺得怎樣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直到現在,上海世博會的紀念獎杯被格桑精心挑出來擺在辦公桌顯眼的位置,可能不止意味著付出,還是對“新西藏、新發展、新變化、新生活”的期許。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大慶之年,格桑分外忙碌,身為自治區政府副秘書長,他受命任大慶辦活動組副組長,正在與各方共同忙碌著辦大慶。大慶,不只是慶祝,更是回顧,是展望;是憧憬,是激勵;是傳承,是發展,“要畫好一個句號,再翻開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