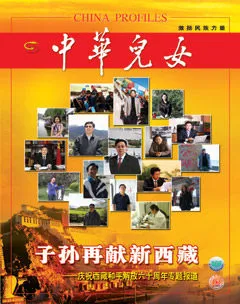盧小飛:我是西藏的女兒
2011-12-29 00:00:00張惠清楊瀅
中華兒女 2011年10期




很多年以后,盧小飛仍然能回想起當(dāng)年她從西藏的山頂上往下看,那一排排土坯房的洋鐵皮屋頂,在陽(yáng)光的照射下反射出明晃晃的光,大片大片的直晃人的眼睛。
在西藏這片圣潔的土地上,盧小飛像一株迎戰(zhàn)風(fēng)雪和嚴(yán)寒的格桑花,在遼遠(yuǎn)的雪域高原揮灑了十一年的青春時(shí)光。
在一批批援藏工作者中流傳這樣一句話:獻(xiàn)了青春獻(xiàn)終身、獻(xiàn)了終身獻(xiàn)子孫。現(xiàn)任中國(guó)婦女報(bào)總編輯的盧小飛卻沒有這種感覺。她說(shuō)起西藏的經(jīng)歷,全然是一副壯懷激烈的樣子。西藏的道路是她自己的選擇,她享受那種動(dòng)蕩的、充滿未知的生活。她說(shuō),西藏給予她的,遠(yuǎn)比她奉獻(xiàn)的要多。
來(lái)自父輩的西藏印象
盧小飛與西藏的淵源,還要從父輩說(shuō)起。父母的軍旅生涯,使與和平解放西藏同齡的她自小便領(lǐng)略了軍旅的顛沛,而父親的人生抉擇和報(bào)效祖國(guó)的品質(zhì),更是像基因一樣在她的血液里流淌。
盧小飛的父親夏川是參與和平解放西藏的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二野十八軍的宣傳部長(zhǎng),原名盧鎮(zhèn)華,從年輕時(shí)代投筆從戎算起,在部隊(duì)就一直從事新聞宣傳工作,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他創(chuàng)作的抗戰(zhàn)詩(shī)歌和歌詞曾經(jīng)激勵(lì)過(guò)無(wú)數(shù)抗日志士,他曾是冀魯豫軍區(qū)的四大筆桿子之一。
1950年,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勢(shì)如破竹般地解放了西南諸省,夏川時(shí)任第二野戰(zhàn)軍第十六軍的宣傳部長(zhǎng)。他所在的兵團(tuán)有一部分人準(zhǔn)備轉(zhuǎn)業(yè)到地方工作了。當(dāng)時(shí)他正按照組織命令參與接管貴州省文教工作,正巧遇到了十八軍軍長(zhǎng)張國(guó)華。張國(guó)華說(shuō)夏川你在這啊,我們馬上就要去西藏了,你跟我們?nèi)グ桑鞑厝蹦氵@樣的人。
剛剛誕生的新中國(guó),給人民的幸福生活帶來(lái)無(wú)限希冀,在和平年代選擇去西藏,去依然沒有擺脫封建農(nóng)奴制度的雪域高原,無(wú)疑是選擇“第二次長(zhǎng)征”。夏川卻沒有猶豫,憑著一腔激情,他毅然決然地投入了奔赴西藏的解放部隊(duì)之中。當(dāng)時(shí),盧小飛的母親已有孕在身,不能跟隨大部隊(duì)進(jìn)藏,便留守在四川新津縣的純陽(yáng)觀。當(dāng)時(shí)十八軍的后方留守處就設(shè)在那里。
1951年,當(dāng)父親做為解放西藏的十八軍的宣傳部長(zhǎng),正隨大部隊(duì)走在西藏的祟山竣嶺之間的時(shí)候,盧小飛出生了。當(dāng)時(shí)成渝鐵路還沒有修通,在盧小飛生下來(lái)第12天的時(shí)候,她便隨母親搭乘一架便機(jī)飛回北京。這么小的孩子坐著飛機(jī)從天而降,家里人都覺得很新奇,奶奶說(shuō),這么小就坐了飛機(jī),就叫“小飛”吧。
大部分“藏二代”們都是在保育院里長(zhǎng)大。盧小飛也不例外。直到她5歲那年,夏川調(diào)回到八一廠工作,他們一家才得以團(tuán)圓。
在盧小飛兒時(shí)的記憶里,家中總是會(huì)來(lái)一些從西藏過(guò)來(lái)的客人。父親性格豪爽,交友廣泛。往來(lái)于家中的西藏客人們有他的領(lǐng)導(dǎo)、老戰(zhàn)友,還有藏族同胞,只要他們來(lái)北京,都會(huì)到他們家吃吃飯敘敘舊,有時(shí)還會(huì)一起到八一廠去看新上映的片子。國(guó)家發(fā)生三年自然災(zāi)害的時(shí)候,家家糧食短缺,饑餓像烏云般籠罩。然而,盧小飛記得家里會(huì)間歇地收到來(lái)自遙遠(yuǎn)西藏的牛肉、黃羊肉和酥油。
盧小飛記得,1963年,八一廠籌備拍電影《農(nóng)奴》。當(dāng)時(shí),西藏話劇團(tuán)的演員就住在八一廠旁邊的炮兵營(yíng),每天都會(huì)在八一廠進(jìn)行拍攝工作。拍電影的時(shí)候廠里的孩子們經(jīng)常去蹭著看。這使得他們也有機(jī)會(huì)客串一下群眾演員,或者參與配音。她跟這些藏族的演員很熟,演強(qiáng)巴的,演蘭朵的,包括一些演配角的,她都混熟了。他們打籃球,她就在一旁看。在盧小飛幼小的心靈中,這些遠(yuǎn)方來(lái)客格外的親近。那時(shí)候開始,她有一種朦朦朧朧的遐想:什么時(shí)候我也能夠到西藏看看呢?文革的時(shí)候,她家樓下有一個(gè)鄰居女生串聯(lián)到西藏,羨慕之余她似乎也種下了遐想。在她內(nèi)心深處的西藏情結(jié),已經(jīng)濃得化不開了。
風(fēng)雪高原的生命驛站
也許是命運(yùn)的安排,在盧小飛大學(xué)畢業(yè)后,終于圓了去西藏的夢(mèng)想。
上大學(xué)的時(shí)候,她和現(xiàn)在的愛人朱曉明情投意合。兩人都是曾在延安插隊(duì)的北京知青,可謂志同道合。朱曉明當(dāng)時(shí)在校學(xué)生會(huì)任宣傳部長(zhǎng),畢業(yè)那年國(guó)家需要一批畢業(yè)生去西藏工作,朱曉明從學(xué)生會(huì)聽到消息,回來(lái)就告訴盧小飛,西藏建設(shè)需要人才,咱們?nèi)グ。克宦牐浅<?dòng),立刻回應(yīng)“好啊”,內(nèi)心對(duì)西藏的向往之情再次點(diǎn)燃。
夏川知道女兒要去西藏的事情之后非常高興,他為此題詩(shī)表達(dá)對(duì)女兒的支持。
“闊別雪域二十載,山河依舊入夢(mèng)來(lái)。女兒接我移山志,憾恨頓消心花開。”盧小飛自己也表了決心:
“愿做鯤鵬飛萬(wàn)里,鄙棄燕雀戀小巢。”
帶著心中對(duì)遠(yuǎn)大理想的向往,帶著那個(gè)年代保爾?柯察金式的理想與激情,1976年10月,新婚的盧小飛與朱曉明身處一批豪情滿志的大學(xué)畢業(yè)生之中,慷慨激昂地奔赴西藏。
由于盧小飛和朱曉明是大學(xué)畢業(yè)生中為數(shù)不多的夫妻倆一起來(lái)的,負(fù)責(zé)接待他們的工作人員一時(shí)沒有準(zhǔn)備,就將“文革”時(shí)期用來(lái)宣傳的廣播室騰出來(lái)給他們住。當(dāng)時(shí)的西藏自治區(qū)黨委宣傳部和組織部在一個(gè)大院兒,辦公樓是一座兩層的石頭房子,其他都是土坯房,你要是拿鐵锨“咣咣咣”在墻上杵幾下的話,能杵出個(gè)大洞來(lái)。當(dāng)?shù)氐母刹扛嬖V她,這已經(jīng)是好不容易找來(lái)的住所了。
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便是屋內(nèi)所有的家具。盧小飛把北大為他們制作的兩個(gè)木頭箱子合并在一起,上面鋪上褥子,就成了一張沙發(fā)。他們的小家,是一起進(jìn)藏的同學(xué)們最愛來(lái)的地方,每逢周末的時(shí)候,他們都過(guò)來(lái)蹭飯,用從北京帶來(lái)的煤油爐子煮上一大鍋面條,拿洗臉盆拌一盆菜,再開一瓶老燒酒,大家吃得都倍兒香。這個(gè)小小的廣播室,承載了他們五年的美好記憶。
到西藏后,盧小飛在西藏日?qǐng)?bào)社擔(dān)任編輯記者,從鉛字排版拼版起家。她回憶,當(dāng)時(shí)西藏日?qǐng)?bào)社全是干打壘的土坯房,房頂是洋鐵皮搭建的,太陽(yáng)曬過(guò)之后炙熱難熬,天冷的時(shí)候又抵御不了嚴(yán)寒,一下雹子就叮叮咚咚直響,大的雹子都能夠把房頂砸出坑來(lái)。社里沒有幾輛車,下鄉(xiāng)采訪大都是搭便車,傳稿子只能靠發(fā)新聞電報(bào)。天氣冷的時(shí)候,他們都是穿著軍大衣坐在太陽(yáng)下寫稿。
那時(shí)候鐵路沒有開通,航空運(yùn)輸成本又特別高,所以物資非常緊缺。由于長(zhǎng)期吃不上蔬菜,缺乏營(yíng)養(yǎng),盧小飛的指甲蓋兒整個(gè)都癟下去,又在前端翹起來(lái),想吃雞蛋也很難買著,就算能買著,也要兩塊錢一個(gè)。那時(shí)的兩塊錢啊,盧小飛感慨。
然而,面對(duì)這些艱苦,樂(lè)觀的盧小飛很淡然,她說(shuō)自己是能吃苦的人。她經(jīng)歷過(guò)上山下鄉(xiāng)的艱苦生活,也經(jīng)歷過(guò)文革時(shí)期的動(dòng)亂,到西藏后,她覺得西藏除了氧氣少以外,其他的苦都不算什么。
更何況,十八軍的父輩們“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zhàn)斗、特別能奉獻(xiàn)”的老西藏精神也像一盞明燈照耀著她、引領(lǐng)著她。在艱苦的雪域高原上,有一個(gè)畫面不斷在盧小飛的腦海里閃現(xiàn):住著并不能阻擋風(fēng)雨的帳篷,吃著發(fā)霉的豌豆和青稞,在氧氣稀少、躺著都使人十分難受的大山上,十八軍的父輩們把汽車和大炮拆成零件,連扛帶抬地過(guò)雪山冰河,帶到了西藏。這種精神激勵(lì)著她在寒風(fēng)如刀的雪域高原上跋涉,在艱辛漫長(zhǎng)的工作道路上疾行。
通常,年輕女記者下鄉(xiāng)是比較麻煩的,但盧小飛和其他男記者一樣摸爬滾打,每到一個(gè)新地方,都能迅速地和當(dāng)?shù)馗刹咳罕姶虻没馃帷:每偷霓r(nóng)牧民會(huì)習(xí)慣性地用穿得油亮亮的皮袍子擦碗,倒上酥油茶遞過(guò)來(lái),她第一次喝,不習(xí)慣味道,一口下去忍不住吐了出來(lái),但接著屏住呼吸一飲而盡。性格豪爽的她吃著藏民招待的風(fēng)干的生肉,喝著醇烈的青稞酒,到西藏各地調(diào)查研究,記錄身邊人物的故事。幾年下來(lái),無(wú)論是西藏的東部森林、西部草原,還是北部荒漠、南部山地,到處都留下了她的足跡。
在藏期間,盧小飛是我國(guó)第一個(gè)進(jìn)入阿里高原采訪的女記者。她介紹,從地圖上看阿里專區(qū)是在“大公雞”的雞屁股的位置上,地域遼闊,在唐代的時(shí)候它是一片以游牧部落為主的高原地帶,它的上部是比藏北高原還要邊遠(yuǎn)的地方。由于那里海拔很高,它的草原上僅生長(zhǎng)低矮的小草,而且大部分地區(qū)還是無(wú)人區(qū)。那時(shí)候從拉薩到阿里還沒有公路,這就意味著她這一路要穿過(guò)無(wú)人區(qū),要經(jīng)歷很多危險(xiǎn)。盧小飛覺得記者就是要堅(jiān)持在第一線,把那些人所不知的東西,用真相和真實(shí)面貌告訴讀者。于是,1981年7月至9月,為深入采訪牧業(yè)生產(chǎn)責(zé)任制,她用兩個(gè)月時(shí)間跑遍了平均海拔4800米的阿里6縣,寫作了《日土人民的喜和憂》《多瑪二隊(duì)的啟示》等一批生動(dòng)反映阿里牧區(qū)改革發(fā)展的報(bào)道,同時(shí),她撰寫的《西去羌塘》《察隅六章》《阿里紀(jì)行》等等,也成為了西藏改革開放初期的淳樸記錄。
兩代人共鑄西藏情
1983年,因?yàn)楣ぷ餍枰R小飛被調(diào)回北京在《人民日?qǐng)?bào)》擔(dān)任農(nóng)村部編輯,七年的援藏工作使她累積了扎實(shí)的采訪調(diào)研功力和敏銳的觀察思考能力,回到人民日?qǐng)?bào)后,她深入西北農(nóng)村牧區(qū)調(diào)研采訪,發(fā)布了許多關(guān)于農(nóng)村牧區(qū)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深度報(bào)道,成為當(dāng)年新聞和經(jīng)濟(jì)界熱議的話題。四年后,人民日?qǐng)?bào)社開始在各地重建記者站,鑒于她對(duì)于西藏工作的熟悉,報(bào)社領(lǐng)導(dǎo)考慮她為侯選人,她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新的挑戰(zhàn),再度進(jìn)藏?fù)?dān)任人民日?qǐng)?bào)社駐西藏首席記者。“第二次進(jìn)藏的心情特別激動(dòng),那時(shí)候女兒七歲多,孩子太小沒辦法只能把她帶到西藏,后來(lái)因?yàn)槲乙锣l(xiāng)采訪,又把她送了回北京,女兒至今還說(shuō)認(rèn)為童年最快樂(lè)最幸福的時(shí)光就是在西藏。”
兩次進(jìn)藏,在她心中,已經(jīng)永遠(yuǎn)結(jié)下了一個(gè)刻骨銘心的“西藏情結(jié)”。 她從西藏獲得了受益終身的人生體驗(yàn),既有豪邁和艱辛,也有生命的感悟。只要看到或聽到“西藏”二字,便立即會(huì)高度關(guān)注,她也在竭盡所能為西藏做一些事情。“這種情結(jié)就是兩代人的傳承,父輩們沒有豪言壯語(yǔ)、沒有大道理,有的就是一言一行對(duì)我們的耳濡目染。”
盧小飛常聽父親講述,在他剛到拉薩的時(shí)候,沒有地方住,有幸被派駐到西藏貴族家庭郎敦的家中,郎敦的父親是達(dá)賴?yán)锏母绺纾抑幸髮?shí),有兩套樓房,其中一套分給十八軍政治部的同志們住,雖然郎敦家住了很多人,但只有他跟郎敦家結(jié)成了生死之交。
郎敦家族里的成員都是堅(jiān)定的愛國(guó)者,他們?cè)谖鞑厣蠈映霈F(xiàn)分裂的時(shí)候堅(jiān)定的站在共產(chǎn)黨這一邊,他們家的孩子們也都加入了共產(chǎn)黨。老大郎敦?班覺是西藏作家協(xié)會(huì)的副主席,班覺日后回憶道他之所以加入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就是受了夏川的影響,在班覺的印象中,夏川和藹可親,溫文儒雅,夏川的為人和學(xué)識(shí)讓他了解到,漢族人并不是像藏獨(dú)分子所描述的那樣可怕與可憎。夏川與郎敦家的這種友誼后來(lái)演變成了親情,一直延續(xù)到了盧小飛這一代,乃至再下一代。
“我們?cè)谠毓ぷ髌陂g,干群關(guān)系處理的非常好,在藏族同胞們眼中,解放就意味著千百年來(lái)禁錮他們的枷鎖被打破,解放軍就是活菩薩。不光是老百姓感謝共產(chǎn)黨,就連貴族對(duì)共產(chǎn)黨的那種感激之情也是不言而喻。”正是因?yàn)槎嗄陙?lái)在西藏的歷練,對(duì)西藏問(wèn)題的研究,才讓盧小飛對(duì)西藏問(wèn)題有了理性的思考,盧小飛認(rèn)為,西藏的和平解放不僅解放了農(nóng)奴而且解放了貴族,解放的是他們的精神,他們的思想,讓他們走上了一條光明的道路。
盧小飛至今記得她在《西藏日?qǐng)?bào)》時(shí)期的第一任小組長(zhǎng),叫群覺,群覺來(lái)自窮苦的勞動(dòng)人民家庭,他的媽媽帶出來(lái)的孩子全部加入了共產(chǎn)黨并且全都當(dāng)上了干部。“群覺家人對(duì)我們的理解和愛護(hù),以及我們下鄉(xiāng)采訪看到當(dāng)?shù)乩习傩盏哪欠N純樸,真是非常感動(dòng),你可以隨便坐在老百姓家中的臺(tái)階上,他們會(huì)傾其所囊拿出家中的佳肴美酒款待你,包括解決我們采訪中遇到的很多困難,太多的回憶,點(diǎn)點(diǎn)滴滴,凈化心靈。”
“西藏就在我的家”
為紀(jì)念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盧小飛去年開始策劃撰稿“《西藏的女兒》——60年60個(gè)婦女的口述實(shí)錄”,她希望能通過(guò)60位不同領(lǐng)域的藏族婦女的口述來(lái)真實(shí)的呈現(xiàn)西藏婦女這六十年的足跡,見證西藏和平解放后這六十年來(lái)的發(fā)展與變遷。“之所以采用口述實(shí)錄這種形式,是因?yàn)樗钅苷鎸?shí)的展現(xiàn)歷史,不會(huì)人為拔高,不會(huì)有太多主觀色彩的東西。”
在這本著作中,有一個(gè)叫卓瑪?shù)呐耸潜R小飛不能跳過(guò)的篇章。1987年,盧小飛和中國(guó)婦女雜志的一位女記者去西藏的邊防錯(cuò)那采訪,路途遙遠(yuǎn),公路被洪水沖的凹陷進(jìn)去,險(xiǎn)境可想而知。車子在雪山邊上的冰河公路上行駛,突然前面的路塌陷了,盧小飛和同事連人帶車掉進(jìn)了冰河里,她們趕緊想辦法爬出了車廂,可汽車卻深深地陷在了河床的泥沼里。在盧小飛看來(lái)這只是一次小挫折,一向心態(tài)樂(lè)觀的她先是安慰同事讓她的情緒平靜下來(lái),告訴她一定會(huì)有辦法解決這個(gè)問(wèn)題的。她隨即搭上了后面過(guò)來(lái)一輛車,去到兩公里以外的公路養(yǎng)護(hù)段搬救兵。
“我是人民日?qǐng)?bào)的記者,我們的車掉進(jìn)了冰河里,洪水馬上就要下來(lái)了,只要洪水一來(lái),車就要被沖走,情況非常危急,請(qǐng)你幫幫我們。”公路養(yǎng)護(hù)段的副段長(zhǎng)卓瑪聽完后說(shuō),立刻派人帶著一輛車前去拖車,最終將車子從危急中解救了出來(lái)。這件事之后,盧小飛一直記得卓瑪,記得她堅(jiān)毅真誠(chéng)的眼神,和她的那句:“你放心,有我們?cè)诰陀心銈兊能囋凇!?br/> 時(shí)隔二十多年,2010年夏天,盧小飛幾經(jīng)周折終于找到了卓瑪,卓瑪居然對(duì)這件事一點(diǎn)印象也沒有,早就忘了。這讓盧小飛極為震撼,從而也引發(fā)了她的思考。挽救了《人民日?qǐng)?bào)》記者的生命,在當(dāng)今人看來(lái),完全可以表功論賞了,但卓瑪卻完全沒有放在心上,她認(rèn)為這種事經(jīng)常會(huì)發(fā)生,是再平常不過(guò)的了。這就是她們,這就是藏族同胞的純樸和善良,做了那么多好事卻從不記得,從未想過(guò)青史留名, 這就是西藏的老百姓,西藏的人民。
在盧小飛心靈震撼的那一瞬,她把那種感覺記錄在了《西藏的女兒》的前言:“她們是被埋在泥土里的珍珠,時(shí)間空間的泥土把她們掩埋的太深太久,需要我們新聞工作者去把土扒開,讓她們放出光芒。”
雖然已經(jīng)離開了西藏,但對(duì)盧小飛來(lái)說(shuō),西藏就在她的家。盧小飛的愛人現(xiàn)任中國(guó)藏學(xué)研究中心研究員,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都與西藏有著割舍不斷的關(guān)系。“我覺得每一代人,無(wú)論是思想還是青春都會(huì)留下時(shí)代的烙印,而我們是在時(shí)代洪流中搏擊風(fēng)浪的,我們沖在了時(shí)代的前列,所以我們當(dāng)時(shí)會(huì)有那樣的選擇,因?yàn)槲鞑匦枰覀儯瑖?guó)家需要我們?nèi)槲鞑氐陌l(fā)展奉獻(xiàn)我們的力量,我們就理所應(yīng)當(dāng)?shù)娜?shí)現(xiàn)這種希望。而對(duì)我們的下一代,我們會(huì)尊重她們的選擇。”
盧小飛說(shuō),退休后她依然會(huì)發(fā)光發(fā)熱,寫西藏,寫人生,在促進(jìn)西藏事業(yè)的發(fā)展上,她還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