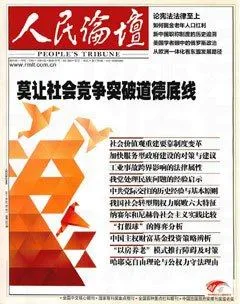中共黨際交往的歷史經驗與基本原則
改革開放以來,按照黨際交往四項原則,中共開拓了中國特色政黨外交的嶄新局面。我黨恢復和發展了同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關系;本著“超越意識形態分歧,謀求相互理解與合作”的精神,恢復和發展了與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的關系;與發展中國家各種類型的民族民主政黨建立了多種形式的交往與聯系;同西方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進行了不同形式的交流和接觸。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90年前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的建立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中共建立后不久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此中共從建立的那天起,就面臨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及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經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何正確處理黨際交往關系的重大問題。中共在長期黨際交往的過程中,走過了一條不平坦的路,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值得反思的教訓。回顧90年來我們黨的黨際交往歷史,能從一個側面反映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依靠外援到獨立自主,從不成熟到成熟的發展過程。
共產國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并幫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
90年前中共的建立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建黨后不久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此在中共黨際交往的歷史中與共產國際的關系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思想理論前提。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就開始傳入中國,然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真正傳播是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尤其是在共產國際建立和五四運動之后。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共產國際起過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前,中國先進分子主要是向西方尋求救國救亡的真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震撼了世界,使中國先進分子的目光轉向了俄國,開始學習和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周恩來、李達、惲代英等一批中國早期的先進分子,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經驗的過程中,注意到共產國際這一新生的無產階級國際組織的建立。1919年1月下旬,外電報道了共產國際即將召開一大的消息,李大釗得知后于2月著文說:“為了解放的運動,舊組織遂不能不破壞,新組織遂不能不創造。”又說,“中歐的社會革命一經發動,世界的社會組織都有改變的趨勢,為應世界的生活的必要,這國際組織、世界組織、是刻不容緩了。”①表達了中國早期先進分子對建立共產國際的歡迎態度。
共產國際直接向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始于1920年3月。經共產國際批準,當時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處領導人威廉斯基·西比里亞科夫派遣以魏金斯基為首的工作小組來到中國。小組成員包括魏金斯基及夫人庫茲涅佐娃、馬邁耶夫及夫人、波林、斯托揚諾維奇、楊明齋等。
魏金斯基一行來華前,雖然在五四運動中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宣傳已經比較普遍,但總體上說當時思想理論界還很混亂。混雜在馬克思主義之中的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各種思潮,這些思潮造成人們對馬克思主義認識上出現偏差或誤解,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魏金斯基等來華后,針對這種情況,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宣傳工作,幫助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統一思想,真正開始了共產國際直接向中國傳播馬克恩主義的歷史。
為在中國更廣泛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在共產國際代表幫助下,改造和創辦了當時一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例如,把《新青年》改辦為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專門刊物,譯載列寧著作,開辟了俄羅斯研究專欄。創辦了中國第一個無產階級黨刊——《共產黨月刊》,介紹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基本知識等。為向工人階級灌輸馬克思主義,創辦了工人刊物《勞動界》。魏金斯基等人不僅參與創辦這些刊物,而且親自為之撰稿。共產國際對當時這些刊物的創辦和印發提供了主要的經費資助。
魏金斯基等共產國際使者在宣傳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經驗的同時,為在中國組建共產主義政黨作了大量工作。他們來到中國后,即通過北京大學俄籍教授柏烈偉和伊風閣的介紹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雙方在交談中,就建黨問題交換了意見。魏金斯基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共產黨的條件,李大釗表示同意,且希望此事由陳獨秀來領導。之后,李大釗介紹魏金斯基赴上海會見了陳獨秀。魏金斯基向陳獨秀介紹了俄國革命和共產國際,并就中國革命交換了意見。雙方一致認為,應當在中國發起建立共產主義組織。在魏金斯基等的幫助下,經過幾個月的醞釀籌備,1920年8月,由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7人發起,在上海成立了共產黨小組。小組擬定了一個類似黨綱黨章的文件。關于黨的名稱叫社會黨還是共產黨,陳獨秀在征求李大釗的意見后,決定叫共產黨。1920年11月,上海小組擬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為此,要通過革命的階級斗爭,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上海小組作為黨的發起組和聯絡中心,在建立全國統一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上海黨組織建立后,陳獨秀立即發信給李大釗,相約在北京也同時建立共產黨組織。1920年10月,繼上海之后,北京的共產黨小組成立。此后,湖北的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湖南的毛澤東、何叔衡,山東的王燼美和鄧恩銘,廣東的譚平山、譚植棠,分別在各地發起建立了共產黨小組。在日本、法國也有由留學生先進分子組成的共產主義小組;對各地共產黨小組的建立,共產國際都給予了具體幫助。魏金斯基去上海時,馬邁耶夫留在北京幫助李大釗從事建黨活動。馬邁耶夫還曾南下武漢了解湖北建立共產黨小組的情況。魏金斯基和楊明齋經常往來于北京和上海之間,途中還到過濟南,與王燼美、鄧恩銘等進行過會談。廣州共產黨組織最初是在俄共(布)黨員斯托揚諾維奇和波林的幫助下成立的。共產國際使者還幫助在上海、北京等地相繼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用以團結進步青年。1921年春,上海、北京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接受少共國際的邀請,分別派出代表去莫斯科參加少共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
在建黨過程中,魏金斯基等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在上海創辦了外國語學社,它為輸送中國的進步青年去蘇俄學習,為中國共產黨培養干部,作出了重要貢獻。1921年6月,馬林來到中國。稍后,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遣接替魏金斯基工作的尼科爾斯基也到達中國。他們互相配合,著手幫助籌備召開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出席了大會,并在大會上分別發言。馬林在發言中談到國際形勢,共產國際的使命和中共的任務。建議中共應特別注意建立工人組織。他在會上說:中共的成立在世界上具有很重大的意義。第三國際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黨添了一個東方朋友,世界上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了。他還希望中共的同志努力為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國際的指導。尼科爾斯基在發言中介紹了赤色職工國際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情況。
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幫助下,大會經過熱烈討論,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決議。黨綱明確宣布要“聯合第三國際”,大會決議則進一步規定了黨與第三國際的聯系,即“黨中央委員會應向第三國際提出報告”,“在必要時應派遣一名特命全權代表前往設在伊爾庫茨克的第三國際遠東書記處。”②
中共一大召開,標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它所通過的綱領和決議,表明中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以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為榜樣的新型無產階級政黨。從此,中共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匯入了共產國際所領導的世界革命洪流之中。中國革命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共產國際幫助中國革命的最初成果。
共產國際指導了中國共產黨民族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
中共一大規定了黨的最終奮斗目標是“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③但對如何進行中國革命,并未規定明確具體的綱領策略方針。由于這時黨還處在幼年時期,在中共一大的文件中,還包含“應永遠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任何黨派建立任何相互關系。”④等帶有左傾宗派主義色彩的內容。這說明剛剛成立的中共迫切需要制訂一個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民族民主革命綱領,用以指導黨的行動。
中共民族民主革命綱領的制訂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幫助和指導下完成的。共產國際二大確定的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基本理論和戰略策略,對中共制定民族民主革命綱領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雖然在中共召開一大時,參加過共產國際一大和巴庫大會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沒有來得及貫徹列寧和共產國際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思想,但是在1922年1月前后,共產國際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已經傳入了中國。如1922年1月的《先驅》創刊號發表了題為《第三國際對民族和殖民地所采取的原則》的譯文,部分介紹了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這對中共思考中國革命問題產生了重要影響。
對中共制定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影響較大,起到直接指導作用的是共產國際于1922年1月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的“一大”。遠東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對抗帝國主義的華盛頓會議。號召遠東各被壓迫民族在俄國和西方無產階級的援助下,引進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大會著重研究了中國革命問題。季諾維也夫在關于《國際形勢與華盛頓會議的結果》的報告中,揭露了華盛頓會議的實質,是英、法、日、美帝國主義列強以“民主”、“進步”為幌子,爭奪和瓜分在遠東的利益。特別是美國要通過“門戶開放”的自由競爭,在中國市場上戰勝所有其他資本主義競爭者,從中國榨取更多的利益,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薩法羅夫根據列寧和共產國際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策略,作了題為《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及共產黨人的態度》的報告。報告為中共指出了面臨的首要任務,是把中國從外國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實現土地國有,推翻軍閥統治,建立單一聯邦制的民主共和國。報告指出:共產黨人應支持所有的民族革命運動,但是以它不反對無產階級運動為前提。報告還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運動的第一階段是民族民主運動,它的矛頭指向帝國主義”。同時還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產黨在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時,“不能放棄自己的共產主義綱領。”中共中央對這次大會十會重視,出席大會的中國代表團有中共黨員14人,青年團員11人,國民黨代表1人,無黨派代表13人。會議期間,列寧會見了中共代表張國燾,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和鐵路工人代表鄧培,在接見中,列寧提到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的問題,國共兩黨代表作了肯定的回答。
遠東會議的內容和列寧對中國革命的關心,對中國代表產生了深刻影響。1922年上半年,出席遠東會議的中共代表相繼回國,帶回了大會精神和共產國際的指示文件。1922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開了二大,會上通報了遠東會議的情況,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列寧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列寧和共產國際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以及遠東會議的精神,在這次大會通過的文件中得到體現。
大會通過的《宣言》,正lGWrmhtw3nUiYiNoPV/RcFNhYWHVVJB7fBuAi5XigP4=確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的經濟政治狀況,明確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規定黨的最高綱領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主義社會。⑤確定黨的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宣言》指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是中國開明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運動。”中國無產階級應該與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合同動作”,才能使民主主義革命迅速成功。
中共二大通過的《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闡述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關系,并宣布中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決議指出:無產階級是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也是世界的,況且遠東產業幼稚的國家,更是要和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是以增加革命的效力。中共二大決定“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議決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⑥
中共二大完成了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綱領的任務。這既是共產國際指導和幫助中國革命的結果;更是中國共產黨人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結合中國社會具體實際,解決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成果。
中國共產黨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逐步積累了獨立自主處理黨際關系的經驗,提出了黨際交往的基本原則
共產國際和蘇共是中共最早的交往對象。由于中共初創時期既缺乏經驗,又缺乏活動經費,需要接受來自共產國際和蘇O3hyJpAQXNlu+YvqasCYVdzdD+zb5UjNe6DCtGPDwCU=聯的支持。從1922年中共二大決定正式加入共產國際后,中共在較長時期內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黨際交往基本處于在共產國際領導下和世界共產主義政黨體系內。但由于蘇共和共產國際并不了解中國的特殊國情,在幫助和指導中國革命的同時,多次出現“左”或右的錯誤,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危害。隨著中共在思想和理論上的成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在處理與共產國際的關系中,既尊重共產國際的組織和思想領導,又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面臨的許多問題,同時堅決抵制其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錯誤指示,初步積累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獨立自主處理黨際關系的經驗。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蘇共干涉別國內政和別黨內部事務的言行日趨嚴重。中共對此進行了有理有利的斗爭。1956年波蘭事件發生后,毛澤東曾指出:“蘇波關系不是老子與兒子的關系,是兩個國家、兩個共產黨之間的關系。按道理,兩黨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⑦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圍繞著對斯大林的評價和對國際形勢以及國際共運總路線等看法,中蘇兩黨爆發了大論戰。其中原因除了中蘇兩黨在重大理論問題上的分歧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共堅決主張各黨一律平等。中蘇兩黨關系的破裂導致兩國國家關系的惡化,也導致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走向分裂和解體。
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今天回過頭來看,在處理黨際關系的過程中,我們黨并非一切都是對的。比如,中共在與蘇共“老子黨”言行進行斗爭中,維護了我黨的獨立自主,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論戰中我們黨也犯了用自己的經驗和觀點對別的黨評頭論足的錯誤,把不贊成我黨某些觀點和作法而贊同蘇共的黨,都看成是“修正主義”,并與之中斷交往。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我們的黨際關系帶來了更加嚴重的沖擊,產生了負面影響。當時全世界89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中,就有78個先后與我黨中斷了關系,使我黨陷于自我封閉和孤立之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與此相適應,中共的黨際交往工作也進入了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和開拓進取的歷史新時期。根據時代主題、國際形勢和黨的工作重點的變化,我黨沖破舊的思維模式,超越了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來認識黨際關系。黨的十二大第一次提出:“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展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關系”,并正式寫入十二大黨章。這一表述將我黨的交往對象限定為“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糾正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將外國共產黨劃分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和“修正主義的共產黨”的錯誤和將交往對象僅限于與我黨觀點一致或相近的共產黨的做法。這是改革開放后我黨對黨際交往關系認識和做法的一次重大調整。黨的十三大在重申上述原則的基礎上,將黨際交往對象進一步擴大到共產黨之外的“其他政黨”。1992年,黨的十四大又強調“同各國政黨”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系。這表明我黨的黨際交往對象擴展到各國各類政黨。各國各類政黨在與我黨交往中,都完全處于平等的地位,沒有黨的性質差別,沒有大小黨之分。黨的十五大繼承了十四大的提法,把黨際交往對象確定為“一切愿與我黨交往的各國政黨”,即不管什么類型的政黨,只要愿與我黨交往,都可以與之發展新型的黨際交流與合作關系。
中共提出的黨際交往四項原則是一個緊密聯系的整體,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獨立自主”,即充分尊重各國黨的獨立自主地位;尊重各國黨從本國國情出發,選擇本國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各國黨有權獨立管理和決定黨內一切事務,自己觀察國際國內形勢并制定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完全平等”即各黨不分大小強弱,歷史長短,執政與非執政,都是平等的。在進行黨際交往時,各黨應平等相待,任何黨不能對別的黨發號施令,不能把自己的觀點和做法強加于其他黨;只有各黨一律平等,才能保證各黨的獨立自主。
“互相尊重”即黨與黨之間存在分歧是難免的,不能強求一律,要超越意識形態差異進行合作;互相尊重,就是沒有尊卑上下之分,黨與黨之間應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求同存異、開展合作。
“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即各國黨的內部事務應由各國黨自己去處理,任何別國黨都不能進行干涉,不允許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不利用黨際關系去干涉別國內政,黨際交往應有利于國家關系的建立與發展。不利用雙邊黨際關系反對第三方政黨,不應損害第三方黨的利益。不利用黨際關系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由各黨自行選擇本黨方針政策。
中共黨際交往的四項原則反映了世界各國黨多年來爭取獨立自主和平等地位的愿望和要求,順應了黨際關系發展的趨勢,體現了新型黨際關系的根本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按照黨際交往四項原則,中共開拓了中國特色政黨外交的嶄新局面。我黨恢復和發展了同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關系;本著“超越意識形態分歧,謀求相互理解與合作”的精神,恢復和發展了與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的關系;與發展中國家各種類型的民族民主政黨建立了多種形式的交往與聯系;同西方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進行了不同形式的交流和接觸。針對蘇東劇變后的復雜的政黨現象,本著求真務實的精神,積極主動而又慎重穩妥地開展了對該地區各類政黨的工作;積極參加多邊政黨交往活動,等等。
目前,我黨已同世界上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400多個各種類型的政黨和組織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聯系和交往。他們當中既有執政黨、參政黨,也有重要的在野黨和與中國沒有外交關系的國家的政黨;既有共產黨和工人黨,也有社會黨、工黨和自由黨、人民黨、保守黨;既有發達國家政黨,也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黨。還有國際性和地區性的政黨聯合組織。我黨與這些政黨不同形式、不同層次、不同渠道的友好交往,不僅有助于加深彼此的了解、友誼與合作,推動黨際關系從而促進國家關系的發展,也推動著世界和平、發展與進步事業。這種新型的黨際關系,不僅是我黨觀察世界、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平臺,也日益成為世界了解我黨倡導的科學發展、推動建設和諧世v7xqVPAu+GdjxxHcO9IS3vgr7ZmwCAx4m59vPkH+v7I=界等理論和實踐的重要窗口。中國特色政黨外交的新局面,也促進了我國國家對外關系的發展,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更為有利的外部環境。
中共從90年前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到今天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執政的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領導著世界五分之一人口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歷史見證了90年來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和成熟,見證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見證了中共從曾經的自我封閉到今天形成了對外開放、豐富多彩的政黨外交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取得的成就,必將對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和人類社會發展做出更大貢獻。(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科社部科社原理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導)
注釋
①《李大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34頁。
②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5、67頁。
③④《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頁。
⑤《六大以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頁。
⑦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