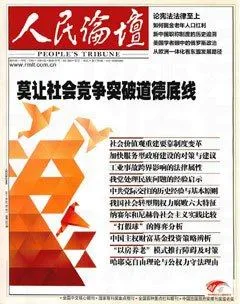受賄罪認定中的疑難問題
【摘要】受賄罪的定罪量刑一直是刑法理論研究及司法實踐中的焦點問題,其犯罪手段表現越來越隱蔽和多樣化,由此引發出一系列爭議。研究認為以后的立法有必要將財產性利益納入到賄賂的范圍當中,或者是對賄賂的范圍進行擴大解釋;事后受財行為也應認定為受賄罪;可以用分解比較法或綜合分析法來區別“人情往來”和受賄行為。
【關鍵詞】受賄罪 事后受財 人情往來
期的司法實踐過程中都將其認定為財物。從立法規定看,受賄罪的對象中包括財物以及財產性利益是不言而喻的,同時也和立法精神是相一致的。但是這里存在另一問題,即非財產利益是否屬于受賄罪范圍。對此,我國目前立法上沒有規定,理論界則存在肯定態度。筆者認為,不應該將其認定為受賄罪的對象。因為非財產性利益往往無法用金錢來進行估價,同時在其危害性上也難以認定,如果將非財產性利益認定為賄賂,那么由于無法估價也就無法對刑罰的輕重進行確定,這會對司法的嚴格執行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就罪刑法定原則而言,我們不能肆意擴大受賄罪中的賄賂范圍。同時,要看到現在腐敗方式中,常常出現“財產性利益”,所以以后的立法有必要將財產性利益納入到賄賂的范圍當中,或者是對賄賂的范圍進行擴大解釋。
關于“事后受財”構成受賄罪的認定
“事后受財”的特征。從立法明文規定中我們可以看出,受賄主要包括兩個類型,一個是索賄,另一個是受賄。對于受賄而言,必須同時滿足收受他人財物和為他人謀取利益這兩個方面的條件才能被認定為受賄罪。但是收受他人財物和為他人謀取利益這兩方面的內容并不存在一個必然的前后時間關系問題。可以是先謀利再收受財物,也可以是先收受財物再謀利,還可以是同時進行。而在對不屬于自身的非法財物進行接受的情況,只會存在時間先后順序上的不同,其他的并沒有區別。在對受賄罪的認定方面,本身的重點在于權力和財物之間的交易,需要打擊的是這方面的內容,在對受賄罪的罪行以及故意犯罪的認定上,并不在于行為人是否有收受財物的主觀意圖,而在于行為人在收受非法財物的過程中是不是明知該財物就是自己利用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而得到的回報。因此就“事后受財”行為而言,只要行為人可以意識到這一財物就是自己為他人謀利所獲得的回報,實際收受了財物,就符合了主觀故意的要件,應該被認定為受賄罪。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收受財物的行為是出現在事前還是事后,同時無論行為人有沒有事先想過該謀利有可能會獲得對價的財物回報,這種行為都是對國家工作人員在自身廉潔性保持上的一種嚴重破壞,因此應該被認定為受賄罪。
“事后受財”構成受賄罪的認定。正如上文所說,只要行為人可以意識到財物是為他人謀取利益而獲得的回報,那么這對自身的職務行為就是一種出賣,就侵害到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事實上“事后受財”和事前約定受財后謀利的行為之間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具體而言,在形式上一般的受賄行為是在事前對雙方所存在的對價關系以及財物上的交換已經做好了約定,而在“事后受財”中,并沒有對這些對價關系和交換進行約定,而是將該約定無形中延遲到了事后受財的時候來進行的。行為人在明知該財物屬于謀取利益后的對價而依然收受財物的行為,依然屬于權力和財物之間的交易,也形成了一定的事實上默契。同時從法律本質上來說,無論是哪種形式上的受財,都會對受賄罪所要保護的法益造成很大程度的侵犯。
有些學者認為,在事后受財的情況下,行為人之前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并不是對自身職務行為上的買賣,而且在事前沒有約定的情況下,他人在獲取利益之后,也沒有必要再去向行為人支付對價。但是筆者認為,這些都不能掩蓋職務行為的廉潔受到嚴重侵害的事實。同時從司法實踐中可以得出,由于國家工作人員往往在某一職務上行使職權的時間較長,而事后受財的這種情況往往處于行賄人或者是所求的利益將長期處于行為人的職務范圍之下,因此行賄人存在繼續依賴行為人而謀取利益的巨大可能性,在獲得利益之后還會去向行為人支付對價,也就是支付財物,而在這個過程中行賄受賄的意圖就會非常明顯了。其次,就一般的受賄罪而言,行為人只要在收受財物之后,承諾以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就可以被認定為受賄罪,在事后受財的行為中,行為人已經為他人進行了謀利,對職務行為的廉潔侵害已經成為了既定的事實,那么其罪行的認定自然也應該被歸于受賄罪。只是就像在生活中我們所看到的“貨到付款”一樣,對權錢交易的完成進行了延遲。而在同樣滿足對受賄罪所要保護的法益進行侵害的前提下,認定事后受財行為不屬于受賄罪的范疇明顯是不合理的,同時也難以被社會公眾所接受。
還有人認為,行為人在收受他人財物的時候并沒有對行賄人承諾會為其謀利,因此這種情況應該不屬于受賄罪的構成要件。但是這里所提到的“承諾”,在很多國家的刑法中被稱為“期約”,僅僅只是受賄罪構成的最低要求,在事后受財中行為人已經為他人謀利,這要比僅僅承諾謀利的行為要嚴重的多,在對法益的侵犯上也更加直接和明顯。
從與其他受賄類罪行相協調的角度上來看,也應該將事后受財行為認定為受賄罪。由于受賄罪中包括兩種類型,其中受賄和索賄之間的差別僅僅在于是否必須滿足“為他人謀取利益”,而在其他方面的內容上都沒有任何區別。在索賄中也存在行為人先為他人謀取利益,后臨時起意向他人索取財物的行為,該行為在認定上明顯被歸于受賄罪,那么就協調性上來說,其事后受賄的行為必然也應該被認定為受賄。
“人情往來”的受賄案件的認定問題
在對受賄罪進行認定的過程中,“人情往來”和受賄行為之間往往容易產生混淆。筆者認為在對其區分的過程中,要對受賄罪的構成要件實現準確把握的基礎上,可以采取以下兩種方式來進行區分。
分解比較法。這種比較方式是建立在將人情禮尚往來和受賄行為主客觀方面各個要素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采用比較分析的方式尋求這兩種行為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從而進行區別。首先就兩者之間的主體關系而言,其性質是不同的。人情禮尚往來所形成的主體關系是一種私人感情關系。一般而言這種私人關系就是親屬關系、好友關系以及其他有親密聯系的私人關系。但是在司法實踐過程中對于這些關系范圍的認定都較為復雜。關于親屬范圍的界限問題,首先要確定界限的原則,既要考慮到我國傳統的文化,又要參照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并且還有有利于同賄賂犯罪作斗爭的現實需要。筆者認為,對于親屬范圍的認定,結合現實與我國傳統的文化,應該定義為:直系血親、三代以內旁系血親、直系姻親、三代以內旁系姻親。總之,都是以血緣為紐帶的人與人的關系。而對于好友和有特殊感情關系的范圍界定相對要復雜一些,標準不容易把握。但是筆者認為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在司法實踐中應該從嚴把握。可以認定為好友的標準,一是群眾公認,即在一定的群體范圍內,大家都有共同的認知,認為當時雙方確為好友關系;二是提供事實自我證明,即由當事雙方或一方提供確實可信的事實與證據,證明雙方確因群眾還不知悉的事由與原因成為了好友關系,如同鄉、戰友、同學,以及外界有關人員中關系比較好、建立了友情的人。而對于受賄,其主體的雙方是利害關系,在利害關系發生之前的一段時間,并沒有長期固定的交往,其實質是權錢交換的關系。收禮與受賄在主體雙方關系產生的基礎上,也是截然不同的。正常的收禮,送禮人與收禮人之間是血親、姻親或者比較密切的私人關系。而行賄與受賄雙方關系產生的基礎是受賄人因特定身份而擁有的特定的權力。其次,從主觀上進行比較分析。收禮與行賄的動機和目的不同。送禮方的動機是基于親友情意而將財物或者各種利益贈與收禮人,并不要求得到以收禮人職務行為為對價的回報。而對于行賄人而言,將財物或者各種利益給予他人,是為了利用他人職權為自己謀取利益,對于回報的要求是具體而明確的。
綜合分析法。是指把收禮與受賄的要素綜合起來進行分析研究,做出判斷。對利用職權為親朋好友謀取了利益(包括合法利益與非法利益)而收受了財物的,不能僅僅因為主體雙方的特殊關系而將這種行為歸為合理的收禮,也不能簡單地從法條的形式規定上將其理解為受賄,而應該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分析研究,根據不同的情況做出不同的判斷。一是看是否有排除因素。對直系血親、三代以內旁系血親、直系姻親、三代以內旁系姻親所給予的較小的財物,一般不宜以受賄罪論處。但是如果所送的財物數額較大的,除直系親屬所送的財物外,只要存在職務行為與收受財物的對價關系,一般應該認定為受賄。二是看是否有職務行為為對價。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而收受了數額較小的財物的,應認為是收禮;如果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而收受了財物,數額較大的,應認定為受賄。三是看數額。數額是衡量受賄與收禮界限的一個重要因素,一般來說,所送財物價值明顯超出社會一般人的觀念,則就有受賄的嫌疑,如果有職務行為為對價就應以受賄論處。如果數額較小,在社會一般人的觀念之下能夠接受,就不能以受賄罪論處。(作者單位:焦作大學法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