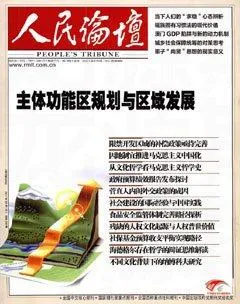“人情”在司法衡平中的倫理作用
【摘要】在個案中,判決結果與法律規范的預期有所不同,其原因是司法衡平之必然結果。人情作為社會的倫理現實在司法衡平中起著重要作用,它不僅是倫理衡平的現實依據,也是法律衡平的內在要求。鑒于人情在司法衡平中的局限性,應在對人情內涵全面把握基礎上,才能構建和諧司法衡平體系。
【關鍵詞】人情 司法衡平體系 倫理衡平 關系
引 言
司法中影響裁判結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法律方面的可稱為法律因素,其他方面則稱為非法律因素。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具有深厚倫理傳統的國家,非法律因素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考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情。在社會學意義上,我國仍屬于熟人社會,人們生活的許多方面包括司法都受到人情之影響。人情對司法的影響集中表現在它與法律的博弈中。一方面因法律的滯后性與機械性,導致適用僵化并使司法過程成為三段論的簡單運用;另一方面因人情因素的多面性與本土性,使法律曲態適用并走上背離之路。這都極易導致法官“同案不同判”的出現,其結果會使公眾對司法公信力產生懷疑。為此,充分挖掘人情價值的合理性,解決法律與人情因素的沖突,實為實現司法目的之必須。
司法目的下的“人情”解析
司法目的之通說在于實現公平正義,即在于解決糾紛化解矛盾,最終實現社會各種利益的整體平衡。從一般法理分析,司法目的即在實現立法目的,執行立法本意。
司法目的的層次。司法目的可分為兩個層次。第一是法律之適用。即法官適用法律規范對案件進行判決,其實質是法律發生效力、使案件當事人利益達到平衡的過程。第二是法意之實現。這是較高層次的、也是法律目的之所在。它大多以抽象的價值概念為標準,比如公平、正義等;同時該目的屬于價值層面,只有通過具體的法律規范才能實現,由于規范的缺欠給法官裁判留下很大空間,因而公正之實現全系于個人認知及社會輿論的影響。在這兩個層次之間,會出現法律確定性與非確定性、具體化與抽象化的問題,而人情則在這兩者之間游離,成為影響司法審判的重要因素。但是,從司法目的之表現層次看,低層次的法律適用目的在平衡當事人的利益,實現個體公平;高層次的法意實現目的在平衡社會整體利益,實現社會公正,二者最終都歸結為一種“和合”狀態。
司法目的論下的“人情”。西方社會沒有合適的詞語與人情相對應,但可基于對中文人情的理解推導出與其對應的理論。諸家學說的人情是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下的一般理解,而司法目的中的“人情”遠非這些解釋所能涵蓋,甚至存在相悖之處。
綜合學者之說,人情基本含義有四個層面:一是指人的喜、怒、哀、樂等,是簡單、低層次的;二是指作為人際交往的一種非商品化的資源,①主要作用是人之間的關系聯絡;三是指基于血緣形成的親情關系、基于婚姻形成的婚姻關系等;四是指社會成員認同的社會情感,代表了社會成員共同的觀念,其代名詞有“情理”、“民意”等。
司法目的語境下的人情僅限于后兩種含義。法律對第三層面人情的評價是多重的,比如訴訟回避制度充分考慮到其負面影響,排除它對司法過程的作用。但有學者也考慮到它在訴訟中的客觀作用,認為基于傳統與現實考量有必要將“親親相隱”②引入現代刑事制度中。第四層面的人情最具普遍意義并在司法過程中有重要影響。基于此,司法過程中第三、四層面人情因素的作用是客觀存在的,尋找它們與法律之間的“衡平”,達到“和諧”,也為必然。
“和合”語境中的司法衡平傳統及其價值
司法衡平源于西方,指在司法過程中為避免僵化地適用法律,在個案審判中引入倫理、價值判斷等非法律因素以使案件得到公正處理。作為一種司法技術它在不同法系中表現不一,中國古代沒有衡平概念,但卻有類似西方衡平的做法,如“屈法申情”③以及“天理、國法、人情”三者的邏輯關系等。
司法衡平的基本價值:和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源遠流長,也與當今和諧理念不謀而合。從深層理解,社會公正的價值即包含在和合中,張立文教授在總結傳統和合思想時認為:“和合是指社會、自然、人際、心靈、文明中諸多元素、要素相互沖突、融合,與在沖突、融合的動態過程中各要素、各元素和合為新結構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綜合。”④
和合在司法衡平上即“化紛止爭”。司法衡平之目的與司法目的同一。具體來說就是法官利用倫理及價值判斷等對案件權衡,以實現社會正義與個案公正的平衡,而此過程即化紛止爭。糾紛乃是案件中各種利益的沖突形式,止爭乃是法官對各種利益權衡之后作出的判決。從因果關系看,案件事實是和合中的沖突,法官的判決是和合中的融合,衡平是促成沖突轉變的關系鏈。衡平關系鏈中也包含了沖突與融合,當法律因素與非法律因素產生矛盾時是沖突,但沖突必然向融合轉變并表現為兩種情況:一是促成非法律因素法律化,二是促成法律因素穩定化。當法律對案情無明確規定時,法官就對法律持嚴謹審慎態度,并嚴格按照法律基本原則或參考判例進行審判,這在大陸法系國家有典型例證。綜上,無論是司法衡平的目的還是過程都蘊含著濃厚的“和合”價值。
司法衡平的傳統模式。因衡平依據不同,可將其分為法律衡平與倫理衡平兩種模式。法律衡平主要依據一般法理進行,處理個案時嚴格遵守法定程序,其傳統主要在西方,特點主要是規范化,衡平的依據主要是法理法規。倫理衡平是在司法中直接適用倫理道德,將僵化的法律排除或選擇適用以達公正,中國傳統司法衡平即屬此,其特征主要是不規范并形散化,衡平依據是倫理道德。
兩種衡平有重合之處,表現為法律衡平倫理化與倫理衡平法律化。前者指衡平中除運用法律規范外還適用倫理因素進行裁判,通過個案經驗的積累使倫理因素成為立法者的考慮并最終確定為法律。后者指在運用倫理因素進行裁判時必須按照法定程序進行,以此對倫理衡平因素加以制約。
“人情”與司法衡平的關系
人情是倫理衡平的現實依據。作為具體倫理現象的人情實質上是倫理衡平的現實基礎,沒有人情也就無所謂倫理衡平。主要表現在:一、在法律允許范圍內人情可作為法官裁判的依據;二、在立法充分考量的情況下人情會成為法律淵源;三、在法律無規定時,人情可能成為裁判的解釋性因素。法官解釋法律,常見的是進行法意解釋從而推知立法意圖及實踐目的,以得到預期結果。這時法官往往會運用社會學、倫理學等知識,于此不可避免地會將人情因素考慮在內。
人情是法律衡平的內在要求。這可從道德與法律的發展關系來看(道德是人情上升化、集中化體現):第一為前法律階段,法律和道德融合在一起;第二是法典化的習慣,法律的作用不及道德;第三為衡平或自然法階段,道德逐漸融入到法律中;第四是法律成熟階段,道德是立法的參考,而法律是為法官準備的。當然在運用人情進行司法衡平時必須滿足兩個必要條件,一是人情必須嚴格按照一般法理解釋并具有合法性與限制性;二是人情因素的適用必須嚴格遵守法定程序。
人情在司法衡平中的局限性。人情作為血緣倫理理解時在司法中的影響是有限的。原因有二:一是它不能成為罰則免除的直接依據。法律責任的構成中并沒有將血緣倫理作為要素,同樣法律規定的免責情形也鮮見因次免除的;二是它的衡平范圍有限。由于法律規定的不明確或空白,因而在適用血緣倫理進行衡平時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
人情因素作為社會認同與情感被理解時,在司法衡平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一方面,社會認同與情感對司法過程的影響具有滯后性。司法是維系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但它具有被動性特征。如果法官作出的判決使法律與社會認同沖突,那么法官只能首先維護法律,事后才可能通過一定的方式對判決產生影響。另一方面,社會認同與感情衡平存在局限性。由于成文法的滯后性,當新問題出現時法律仍按規定對待之,這是司法系以保護法益的最佳模式,但同時也限制了社會認同與情感及時、充分的表達。
結 語
人情在個案中可以作為審判依據,這也是法律衡平的內在要求,但人情卻是有限的、受法律制約的。人情與司法衡平的關系類似于和合關系。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人們對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