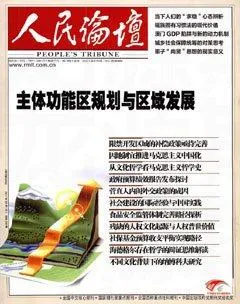從文化哲學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
進入21世紀,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開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方法論的反思階段。這種反思的本質是要建立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書寫范式。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只有在文化哲學的范式內探討和建立起歷史理性,才能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
哲學史有本來的哲學史和書寫的哲學史之分。本來的哲學史是歷史的東西,書寫的哲學史是邏輯的東西。如何看待歷史的東西和邏輯的東西的關系,是哲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長期以來,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只重視歷史的東西而忽視了對邏輯的東西的研究,致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書寫范式一直建立不起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容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內容也無法以哲學史的身份加以敘述。為此,本文專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邏輯的東西,以期建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書寫范式。
邏輯的東西研究之必要性
筆者認為,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邏輯的東西之必要性,是由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狀況決定的。
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是在已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解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并沒有經過哲學史方法論的反思,而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解讀的模式簡單地運用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書寫之中,這就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一開始就缺失了研究邏輯的東西一環。由于沒有研究邏輯的東西,所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書寫始終存在著兩個缺陷:
其一,在敘述的主線上,缺乏邏輯的一貫性。我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的解讀主要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都只論述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思想。后來,我國學者把這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稱之為領袖思想史。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開展,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的內容大大豐富起來了,首先是把第二國際的一些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比如拉法格、拉布里奧拉、普列漢諾夫,寫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其次是把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納入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緊接著又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思想家的介紹納入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最后,在“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名稱下,以國別史的方式敘述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發展起來的各主要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但是,這些都只是在作思想材料的擴充,并沒有實現形式上的更新和突破。而沒有形式上的更新,思想材料的敘述必然雜亂無章。我國20世紀90年代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著作就是如此。從總體上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書寫體例不論是在總體的結構上,還是在對個別人物和派別思想的敘述上都極不協調,也不一致。在總體結構上,主要表現在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鄧小平的哲學思想的書寫結構和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書寫結構不一致:前者基本上是以人物思想為主線,后者卻是以國別或派別為主線;在對個別人物和派別思想的敘述上,時而是人物思想的敘述,時而是重點著作的介紹。造成這種結構上和體例上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邏輯主線。由此可見,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書寫的問題主要出在形式上,而不是出在內容上;形式的問題解決了,內容的問題也就很容易解決了。形式的問題,說到底,就是邏輯的問題。這樣一來,探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內在邏輯就成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書寫中首先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其二,在敘述的方法上,缺乏必要的抽象。從方法論上看,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中出現體例的不一致和不協調,究其根本,是我們沒有對經典作家的原著解讀模式作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辨析。根據馬克思對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規定,經典作家原著的解讀模式恰好是研究方法,而不是敘述方法。這一方法對于我們探討經典作家的哲學思想是有用的,但是,把它搬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敘述上來卻是有問題的。因為研究方法呈現出來的,只是經驗的材料、歷史的東西,而不是思想的聯系、邏輯的東西;如果經驗的材料不相同,那么,敘述出來的各個部分之間也必然不一致和不協調。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中出現的體例不一致和不協調恰恰是因為使用了研究方法,而不是敘述方法。因此,要克服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敘述的缺陷,就必須反思和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敘述方法。
不可否認,敘述方法要以研究方法為前提,它只能在研究工作完成后才能確立,但是,研究工作的完成并不意味著敘述方法就能夠建立起來,從研究工作的完成到敘述方法的確立,還有十分艱巨的工作。這個工作至少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對研究工作的結論進行分析、概括和抽象,從中找到敘述的邏輯起點,就像馬克思找到“商品”這個概念作為敘述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那樣;第二,進行理論的和方法論的研究,建立駕馭和敘述材料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框架。這一工作并不是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才開始的,而是與研究工作交替展開的。就像馬克思發現唯物史觀與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關系那樣。這兩方面的工作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書寫來說,都是必要的,但是,就我國目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狀況看,最重要的、也是亟待解決的,還是后一方面的工作。因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中一些長期得不到解決的難點問題,比如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如何進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以及應該如何評價的問題,等等,都是因為我們沒有把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區分開來,缺乏邏輯的抽象,所以,找不到敘述的原則和敘述的起點。從這一方面看,我們同樣需要開展對邏輯的東西的研究。
上述兩個方面表明,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邏輯的東西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探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主線,這是屬于研究方法的內容;二是確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敘述原則,這是屬于敘述方法的內容。這兩個方面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理論建構來說,缺一不可。
文化哲學的研究范式與歷史理性建構
在哲學史上,對哲學史的邏輯的東西的研究并不是統一的,因而也不存在既定不變的邏輯的東西,相反,邏輯的東西從來就是隨著哲學史的發展而不斷被建構的。在哲學史上,我們不僅有黑格爾的理性主義的哲學史,還有文德爾班的文化哲學的哲學史。前者屬于近代哲學的哲學史,后者屬于現代哲學的哲學史。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于19世紀40年代,是在批判近代哲學中發展起來的,本質上屬于現代哲學。不僅如此,它在創立的過程中,曾經受到過浪漫主義思潮、歷史學、人類學和文化哲學等現代人文科學的強烈影響,而在20世紀的發展中又吸取了存在主義、現象學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影響,并且在東西方國家的發展中形成了多種形態,這些都不是用近代哲學的科學理性能夠敘述出來的,必須采用文化哲學的研究范式,建立現代哲學的歷史理性,才能敘述出來。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邏輯上,歷史理性都是在文化哲學的范式中建立起來的。文化哲學的研究范式在哲學史的領域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以問題為中心,研究不同時代哲學發展的特點和獨特的形態,并通過哲學形態的變革揭示哲學發展的質變。這是哲學史研究的時間向度。二是以民族文化為背景,研究不同國家、民族哲學傳統的形成及其歷史演變,并通過這些不同的哲學傳統敘述哲學發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這是哲學史研究的空間向度。這一研究范式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尤為重要,因為它能夠使人們看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在傳統和不同形態的歷史演變。這兩個特點構成了歷史理性的內容。但是,有了文化哲學的研究范式,有了歷史理性的內容的規定,還是不夠的,要把歷史理性貫穿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敘述之中,還需要開展兩個方面的研究:
第一,清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史和外史,確定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對象和敘述方式。長期以來,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者習慣于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特殊性為由,拒絕討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史和外史的問題。在這些學者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等其他一切哲學是不同的:其他哲學本質上是知識論的,因而有自己的概念體系,而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質上是實踐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哲學創造中從來就沒有作抽象的概念的研究,而是緊密地結合時代的問題、結合工人運動的實踐來闡發他們的哲學思想。由于這一區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不能采用西方哲學史、中國哲學史的書寫方式。不可否認,馬克思主義哲學因其實踐性而具有反概念化、反體系化的特點。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哲學不能有自己的概念體系,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沒有自己的內在邏輯主線。馬克思在論述《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時,把“抽象力”和“敘述方法”作為他研究資本主義規律和表達自己思想的主要方法。這一點就已經充分表明,馬克思主義哲學雖然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它從來不拒絕哲學的邏輯,不拒絕哲學的思維方式,不拒絕用概念的、邏輯的方式來敘述自己的思想,相反,它是把哲學的邏輯、哲學的思維方式和表述方式提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使其能夠穿透現實,改造政治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等更為具體的學科,成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門融哲學于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為一體的學說,就在于它運用了哲學的思維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哲學邏輯。既然馬克思主義有自己的哲學,那么,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任務,就是要通過對已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思想進行邏輯的抽象,發現和敘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在邏輯。這就是清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史和外史的工作。
從文化哲學的觀點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史,就是馬克思的實踐和辯證法的批判精神與多元化的哲學傳統和理論形態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創造的歷史。這一歷史,就其按照實踐和辯證法的批判精神而言,它是理性的,是一般的。但是,就它在不同民族的發展以及所形成的理論形態而言,它是多元的,是歷史的。這兩個方面的有機結合就構成了歷史理性的敘述原則。概括起來,這一原則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準確地描述各個哲學家的創造活動。實踐和辯證法的批判精神是決定馬克思主義哲學本性的方面,但這一精神不是預成的,而是通過個體的哲學家創造出來的,因此,要敘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及其發展,就必須研究哲學家個體的富有個性的思想創造。這是從整體上敘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基礎;第二,以問題為中心,研究不同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特點和獨特的形態,通過哲學形態的變革揭示哲學發展的質變,從而建立起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敘述的時間向度;第三,以民族文化為背景,研究不同國家、民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形成及其歷史演變,特別是比較東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統,通過這些不同的哲學傳統比較,敘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從而建立起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敘述的空間向度。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外史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內史決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其他哲學的區別著重表現在兩點上:第一,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建立在對以機器生產為標志的工業和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分析之上的,因此,要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每一個原理、它的發展以及在不同民族的表現,就必須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工業文明的進步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意義。第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發展是在融合和改造各民族的文化傳統中實現的,因此,要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性發展,就必須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各民族文化傳統之間的關系。這兩個方面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外史的內容。
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只有完成了這種內史和外史的清理工作之后,才能建立起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敘述方式,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成為一門哲學史的科學。
第二,研究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要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史,我們還必須開展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這是由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點決定的。
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在反對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觀念中展開的。在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19世紀馬克思主義者走向改良主義和庸俗唯物主義的根源,就在于他們僅僅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科學社會主義學說,而沒有看到支持科學社會主義的革命理論——馬克思的辯證法。因此,要恢復馬克思的革命傳統,就必須承認,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哲學。從這一觀點出發,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發動了一場深刻而全面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運動。在西方,柯爾施明確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和哲學關系的討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哲學,是革命的辯證法,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這一觀點經過葛蘭西、盧卡奇、柯爾施、霍克海默、馬爾庫塞等的發展,創造了以文化本體論為核心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在東方,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反對當時流行的以新康德主義或馬赫主義補充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中,創造了以自然本體論為核心的東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通過東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這些創造,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價值就呈現出來了:一方面是對馬克思的哲學思想作了充分的闡釋,使馬克思哲學中在19世紀沒有充分發展的內容全部展示出來了;另一方面是創造了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和哲學形態,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內部有了傳統的分化和哲學形態的變革,從而構造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發展的格局。在這雙重的價值中,前者給了我們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哲學和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哲學新的、更廣闊的視野,后者向我們展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多元形成和哲學形態的變革,使我們能夠從考察它們之間的聯系和區別中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內在邏輯。
以上兩個方面的研究表明,研究邏輯的東西,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這門學科來說,是更為重要的方面,因為,邏輯的東西恰恰是我們寫好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根據。如果繞過了對邏輯的東西的批判性反思而直接進到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原則,那么,情景將會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書寫滿足了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原則,但它卻不符合哲學史所要求的邏輯的原則。這就意味著,我們書寫出來的可能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而是國際共運史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解讀史。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邏輯又不能是科學理性的,而只能是歷史理性的;只有遵循歷史理性,我們才能揭示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發展的內在機制,展示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當代風貌。(作者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