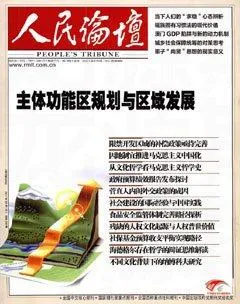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納博科夫研究
【摘要】納博科夫自身身份及其文學的特殊性使得不同時期不同文學文化背景下的納博科夫研究存在差異。俄羅斯文學界對納博科夫的評價批評褒揚俱有,批評為主;美國的納博科夫研究則上升到了美學、形而上學和倫理學三者關系的研究視角;中國的納博科夫研究起步較晚,受美國影響較大,延續(xù)著后現(xiàn)代主義的研究思路。
【關鍵詞】文學文化背景 俄羅斯文學文化 美國文學文化 中國文學文化 納博科夫研究
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文學家之一,納博科夫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跨文化和跨文學特點為世界文學界帶來了一種嶄新的創(chuàng)作視角,為俄語文學和英語文學都做出了極大貢獻。隨著思想的不斷解放,針對納博科夫的文學作品、寫作風格和自身經(jīng)歷的研究逐漸成為世界文學評論界關注的焦點。本文從比較的視角出發(fā),對三種不同文化背景影響下的納博科夫研究進行述評。
俄羅斯文學文化下的納博科夫研究
俄羅斯文學評論家對納博科夫的文學作品一直都存在批評和褒揚兩種不同的意見。縱觀20世紀以來俄羅斯文學界對納博科夫的評價,批判之聲占據(jù)了主導地位。
對于納博科夫這種褒貶不一的爭論態(tài)度起始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俄羅斯流亡文學圈。鄉(xiāng)愁、家園的失落和還鄉(xiāng)的沖動是這個時期俄羅斯流亡文學的經(jīng)典標志。納博科夫的第一部小說《瑪麗》正是這種流亡生活的寫照,但之后,納博科夫的寫作興趣逐漸與俄羅斯流亡文學疏離,從第二部小說《王,后,杰克》和其后的文學作品《從左邊佩戴的勛章》、《洛麗塔》都圍繞著“時間”、“記憶”等主題,作品中表現(xiàn)出了一種美學藝術。納博科夫這種對美學的推崇,使他游離于19世紀以來俄羅斯文學所熱衷的“誰之罪”、“怎么辦”等社會、政治、道德的文學創(chuàng)作主題之外,這種異類性使納博科夫在俄羅斯流亡文學圈中產(chǎn)生了激烈的紛爭。阿達莫維奇認為,納博科夫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重形式的風格導致了其內容上的疏忽和深度上的匱乏,表面看起來光彩奪目,內在卻極其空虛,其作品庸俗平淡①。另一些文學評論家則將目光集中在了納博科夫作品的文學性上,對他在美學上的造詣給予了高度評價②。
雖然納博科夫的文學作品在俄羅斯的流亡文學圈中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但前蘇聯(lián)時期卻很少被提及,即使被一些文學評論者偶爾提及,也往往是作為一種批判的意識形態(tài)出現(xiàn),其文學作品因內容的“非俄羅斯化”,30多年沒有出現(xiàn)在前蘇聯(lián)的任何刊物上。
1989年,納博科夫作品在俄羅斯全面解禁,關于納博科夫的紛爭又一次成為當時俄羅斯文學圈的焦點。米哈伊諾夫從文學實用主義的美學角度來衡量納博科夫的作品,認為除了其第一部作品《瑪麗》之外,其余的作品都與俄羅斯傳統(tǒng)的實用主義經(jīng)典文學格格不入,是一個“沒有文學的文壇巨匠”③。這種不把納博科夫納入俄羅斯文學主流的觀點在當時的俄羅斯文壇被大家廣泛接受。但其中也不乏推崇者,他們從文學的美學性角度為納博科夫辯護,認為納博科夫文學作品表現(xiàn)出了被壓抑的俄羅斯美學文化,他是將傳統(tǒng)俄羅斯文學從封閉、狹窄帶向開放、宏大的領路人,為俄羅斯文學融入歐洲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隨著前蘇聯(lián)的解體,傳統(tǒng)俄羅斯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思想已慢慢淡薄,而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觀念漸漸被人們接受,對納博科夫的認識也不斷加深,其文學作品在俄羅斯也被廣泛接受,納博科夫的文學地位在俄羅斯日漸穩(wěn)固。
縱觀俄羅斯文學界對納博科夫的爭議,不難發(fā)現(xiàn),圍繞著納博科夫作品的藝術形式,爭論者從不同的鑒賞角度做出了自己的價值判斷。作為一個遠離現(xiàn)實、沉醉于藝術的文學作家,納博科夫基本上是作為一個美學家的形象出現(xiàn)在俄羅斯文學界的。
美國文學文化下的納博科夫研究
作為使用英語寫作的俄裔美國作家,納博科夫身份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使他在美國文學史上一度的邊緣化,并進而影響了對其的研究、認識與評價。縱觀美國文學史或文學選本,對于納博科夫作品的收錄少之又少④,直到納博科夫百年誕辰前夕,美國國會圖書館才全面印發(fā)了納博科夫文集,第一次將其納入到美國作家的行列中來。
雖然納博科夫的身份妨礙了其作品在美國的傳播,但他依舊成了文學評論界爭論的焦點。威爾遜、格林等人對其個別作品極力推崇,使其在美國文學界受到熱烈追捧,厄普代克更是認為納博科夫在開放的英美文學與文化傳統(tǒng)之間開創(chuàng)了一條新的創(chuàng)作道路⑤。20世紀60年代,受俄羅斯流亡文學評論圈影響,美國文學界對納博科夫的研究集中于其作品的結構、語言、技巧等形式和風格方面。而這一時期對納博科夫的批評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新批評思潮的影響,但進入70年代,隨著新批評思潮的回落,女權主義的興起和文學焦點向拉美文學、非洲文學的轉移,具有男性中心主義傾向和濃厚歐洲中心主義氣息的納博科夫逐漸被美國文學評論界邊緣化。80年代,伴隨后現(xiàn)代思潮的風靡,納博科夫那種不關心任何社會、甚至不關心如何去反抗任何社會的創(chuàng)作特點,無疑為他在美國文學界貼上了后現(xiàn)代的標簽。厄普代克認為納博科夫是后現(xiàn)代主義新傳統(tǒng)的先驅⑥。到了90年代,納博科夫研究在美國又出現(xiàn)了新的方向,從美學研究的模式轉向倫理和形而上學的研究模式。納博科夫文學作品中經(jīng)常提及的“彼岸世界”⑦成為新的研究焦點。對此,亞歷山大洛夫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納博科夫創(chuàng)作中所表明的形而上學、倫理學與美學是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三者緊密聯(lián)系,構成了一個呈現(xiàn)三角關系的“彼岸世界”,他所有的創(chuàng)作作品都能在其中找到相應的位置,或是靠近美學,或是靠近形而上學、倫理學。納博科夫研究由此提升到了一個縱深的維度,納博科夫作品從不同的角度得以更加清晰地展現(xiàn)。
美國文學界對納博科夫的研究,是從單一的藝術美學的評論闡述,發(fā)展到多層次、多角度的不同文化、不同文學的研究演變過程,而這種跨文學、跨文化研究已經(jīng)成為納博科夫研究的主流。
中國文學文化下的納博科夫研究
受制于政治思想禁錮,20世紀80年代,納博科夫的作品才出現(xiàn)在中國,與博爾赫斯、貝克特等同時代文學大家相比,中國關于納博科夫的研究十分欠缺。
首先,80年代初的中國文學界,納博科夫作品的翻譯呈現(xiàn)出較為混亂的局面。《普寧》、《洛麗塔》等多部作品被出版社翻譯出版,形成了多個不同的中譯版本。這看似繁榮的表象下,其實存在著很深的問題,譯者翻譯水平的參差不齊和翻譯質量的不高,制約了納博科夫作品在中國的傳播,進而造成納博科夫研究者的缺乏。其次,從研究角度來看,中國的納博科夫研究受國內美國文學史教材影響,沿襲了美國70、80年代對納博科夫的評價,認為納博科夫是后現(xiàn)代小說的引領者,從而造成研究角度的單一化。
1989年,《洛麗塔》在中國翻譯出版引起的強烈轟動也反映出當時中國文學界的思想轉變。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封閉意識形態(tài)的消除,在引進西方文學思想的過程中,學術界更偏向于現(xiàn)代主義和理想主義,納博科夫跟隨一批有“現(xiàn)代派”、“現(xiàn)代主義”烙印的作家傳入中國。進入90年代,隨著思想進一步解放,理想主義的沒落,《洛麗塔》、《黑暗中的笑聲》等具有強烈后現(xiàn)代主義思想的作品在中國文學界引起強烈反響,映射出當時中國文學文化界后現(xiàn)代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進入2000年以后,中國關于納博科夫的研究呈現(xiàn)出相對繁榮的景象,出現(xiàn)了大量從作品人物形象、敘述角度等方面對納博科夫作品《洛麗塔》與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特征相互聯(lián)系的研究。此外,《普寧》、《黑暗中的笑聲》、《微暗的火》也成為中國研究者關注的對象。
總體來看,中國對于納博科夫的研究走過了三個階段:80年代的萌芽,90年代的發(fā)展和2000年以后的研究高潮。但翻譯質量不高、研究角度單一等制約著納博科夫研究在中國的發(fā)展,研究視角的擴寬和對作品研究的關注是納博科夫研究在中國的未來發(fā)展方向。
結 語
俄羅斯文化背景下的納博科夫是“非俄羅斯化”的納博科夫,有悖于傳統(tǒng)俄羅斯經(jīng)典文學,遠離俄羅斯社會;美國文化背景下的納博科夫研究不再僅僅停留在藝術美學的層面,而是上升到了美學、形而上學和倫理學三者關系的研究視角,視納博科夫為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先驅;中國的納博科夫研究起步較晚,受美國響較大,延續(xù)著后現(xiàn)代主義的研究思路。
對俄羅斯文化和美國文化視角下納博科夫研究的廓清,有利于發(fā)現(xiàn)中國納博科夫研究的不足。現(xiàn)階段,國內對納博科夫早期作品研究較少,在思想層次、研究角度等方面都有欠缺,研究方向存在巨大的擴展空間。(作者單位:中原工學院研究生處)
注釋
①Brian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