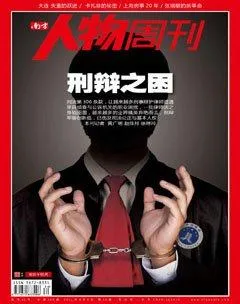中國興起“學習型官員”
2011-12-29 00:00:00何三畏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30期

各級官員請專家們去給他們閉門上課,他們最想聽到的是維穩的錦囊妙計
一位省級重要部門退居二線的官員,來縣城“講課”。聽眾是一個縣城的主要官員和主要公務員。講的內容,則相當“敏感”,諸如官民關系、上訪截訪、貪污腐敗,以及當前種種社會矛盾。他揭官員的丑,指官方愚蠢和短視,評體制的弊端,深入具體,語言“開放”。
設想一位對社會尚無了解的中學生聽到這樣的課,一定深感困惑:既然這個體制和官員的行為這樣沒有規則,這樣充滿矛盾和沒有正義性,為什么還要繼續這樣運作呢?又設想如果把演講者和聽眾的名字和身份去掉,只把內容呈報給管理輿論和宣傳或國家安全的部門,勢必會聞風而動,一陣緊張的。至于媒體,他的演講稿是根本沒有可能發表的,互聯網也是無法上傳的,因為可能涉及敏感詞。
問題是,官場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演講,公務員為什么愿意聽?只有公務員愿意聽可不行,一定得有縣里的主要領導同意并發出邀請。而這位先生能這樣講,也只能取決于臺下聽眾的需求。否則,即便他再“敢講”,也沒必要這樣講。
筆者這里舉的絕不是一個特例。當前,從最基層到相當級別的官員,產生了“提神醒腦”、聽聽這樣的課的內心要求。于是,一些對社會問題有著深入和獨特思考及演講才能的人,走上了他們的講臺。我們知道,于建嶸先生為這樣的演講忙不勝忙。實際上,全國有不少體制內外的學者專家,大學教師,特別是黨校教師,奔走于這樣的講臺。
值得一提的是,某種程度上,體制內的學者、黨校教師,比來自于一般學術研究機構的學者專家,更“能講”,更“敢講”。前者有更多切身的體驗,更知道“自己人”想聽什么。前面舉的這位走出省城、到地市州縣去巡講的先生即屬前者。
在公開的層面,多數官員會表態說,這些演講的內容偏激。但實際上,他們內心忐忑,想聽聽這樣的話。就連在于建嶸面前報怨說“不是我們這樣行政,你們學者便沒有案例”(“沒飯吃”)的那位地方官,也愿意聽聽于建嶸怎么說,否則,于先生便不可能登上他的講臺。再說,今天的官員們,關起門來講話差不多也都會罵體制,甚至罵得比媒體和網絡更“難聽”。升遷無望,正在淡出官場的官員罵,正在享受腐敗利益和灰色收入的,也罵。
為什么會是這樣?原因當然比較復雜,但簡而言之,大致可以說,體制內的利益爭奪既無原則,分配也不公正。他們不是服從原則和法制,而是服從政策和上級,每一個公務員在不斷變換的政策和上級面前都是弱者,官大官小都有“相對被剝奪感”。然而,作為體制中人,罵歸罵,內心卻不希望這個體制規則的利益格局有所變革,因為他們都從這個體制里獲得了普通大眾望塵莫及的利益。
如此,關鍵的問題產生了:各級官員請專家們去給他們閉門上課,分析社會矛盾,出發點只有一個——既能保證現行利益格局的穩定,又能緩和甚至化解現實矛盾。他們希望從專家學者那里聽到維穩的錦囊妙計。他們的底線在于“應對”,他們的落腳點在“擺平”和“搞掂”(擺平就是水平,搞掂就是穩定)。他們希望專家學者們直接告訴他們這個。
基于此,一些奔走于各地官方講臺的人士,也直接打出“維穩課”的標簽。最大的特色就是教你如何“應對突發事件”。因為官員平時很安全,突發事件就是突然變得不安全。你不是說,在突發事件到來時,網絡輿論難于應付么?那你就告訴我一條秘笈。所以,只要他們獻計維穩,主要領導和各部門負責人馬上掏出小本子記錄。筆者想起,在提倡以德治國以后,有一段時間提倡過建設“學習型社會”,那么,在本文涉及的意義上,現在的官員已經是一個“學習型的官員”了。
然而,體制外的專家學者畢竟白面書生居多。例如,他們老是說,新聞發言人要如此這般如此這般,就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最主要的是要在第一時間公布真相,搶先占領輿論空間。
其實,僅僅這么說,官員們并不愛聽,因為他們心里明鏡似的,他們要有“拿得出手”的真相,也不會藏諸密室啊。要知道,如果僅僅靠“發言”就可以擺平和搞掂,那么,也就不需要以法治國或以德治國,“發言”就可以治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