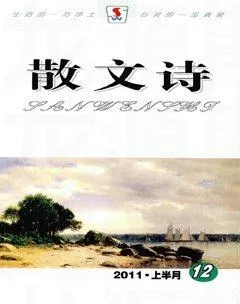平原深處
河灘上有一群水牛
如果是在兒時,我一定會給它們行注目禮——這些農業的英雄、豐收的功臣、敦厚的伙伴!
河灘上的野草更加蔥綠,蘆葦叢中驀然飛出一只水鳥。水牛家族在安閑地享受著陽光與青草。牛媽媽溫柔地抬一下頭,小牛犢也幸福地遙望著大河的流向……
如果我還是當年的牧童,一定會為它們的安閑欣喜,并怡情地爬上牛背,吹響一聲葉笛,背誦一首唐詩。
如果我現在就是牧童,決不敢摸一下它們搖籃般的背脊,哪怕比家中的牛皮沙發更溫暖寬厚;更不敢看一眼它們澄靜的眸子,哪怕比四月江南的天空更明亮溫潤!
如果將來還需要牧童,請讓我和水牛都不要長大!
河岸人家
隔著一條河,我望見對岸的人家大門敞開.像掀開的一本新農歷的封面。
河水平靜,兩岸的青草與雜樹,綠得深不可測。
遠處有一縷炊煙升起,在天空中越走越寬,最后消失在一片透明的瓦藍中。就像門口那條路,越走越隱約,最后消失在遍地的莊稼中……
艷日當頭,勞作的人影還在田野深處。
后園寂靜,楊枝籬笆上爬滿藤蔓,那籬笆多像我的父親親手所插;
園角還有毛桃樹,想必也擠滿青果,那桃樹多像我的母親親手所栽;
園中的蔬菜瓜果,都如鄰里鄉親,內心燦爛,笑容謙遜。
我仿佛曾在對岸度過一日,或者一生,就像這初夏的風,從河面從容掠過,一波之后,牽出層層的競走的浪痕……
黃昏時走進村口
登上河堤,我踩著大葉楊斑駁的樹影走進村口。
三五只水鴨游上岸,老遠就小心地停在岸邊等我經過,就像我兒時給陌生的大人讓路。
黃昏或許是從田野和村莊里漲起的時光的潮,從一蔸禾、一株麻、一棵樹中滲出的墨綠色音樂,悄然將明凈的天空覆蓋。
不見炊煙,天空突然被暮色擁擠。
不見炊煙,就像不見母親晾曬的衣裳,心中一陣空落。
那些整修后的農舍,新春的大紅對聯還在門楣上滿含笑意。
在這個年代,在我的平原和故鄉,在這個黃昏,我看到老人平靜,孩子快樂,看到幾只燕子靜靜地站在瘦瘦的電線上,像是歌唱前的虔敬,又像是歌唱后的愜意。
那些燕子們啊,抑或是在諦聽——把剩下的孤獨,諦聽成村路遠方五彩繽紛的夢……
后窗就是田野
后窗的杉葉紅了,秋天正在奔走。
后窗的稻子黃了,秋天還在等候。
后窗滿是田野。
天空,自顧往深處藍,像只透明的酒壇子。田野不動,稻子不動。此刻,它們仿佛孝子一齊跪下,送走一年的秋風。
還有玉米、高粱、大豆、芝麻、紅薯,這些南方的雜糧,幸福地呆在園中,不懂命運,卻在執著地等待命運。
后窗是農家不常打開的窗子,即使天天在后窗的田野勞作,只記得陽光從南方走來,越過村莊,留下時光的金印;總感到一扇后窗,足可以抵御一生的風雨。
摘棉花的女人
靜下來,再靜下來——哪怕是厚厚的流動的陽光,哪怕是爽爽的掀動黃葉的秋風,直到聽清楚女人的指尖輕輕觸到棉花的戰栗。
潔白、明亮、溫暖、柔軟……棉的果汁什么時候完成了如此燦爛的表達?
平原遼闊,村莊一座連著一座;棉花灼灼,宛若繁星紛沓。此刻,心也要靜下來,聆聽棉花欣然捉住女人的手,聆聽女人準確捉住大地樸真的靈思。
棉根里淌有女人的汗水,棉葉上還有女人的指溫。此刻,棉花簇擁在女人胸前,天地間最壯闊繁復的嬗變,讓女人和棉花簡單得只剩下最原始的交流,即便是開得最低的棉花,女人也要稍微彎一下腰,就像去觸摸一下孩子的頭。
所以要靜下來,讓女人和棉的牽掛猶如黛青色的棉籽,深深棲居在那一團團潔白明亮的安詳之中……
靜坐的老農
一個老農安詳地坐在門口,三月的陽光依偎在他的腳邊。
老農身后是暗橙色的磚墻,掛著一柄斂著寒光的鐮刀和一頂舊斗笠,還有粘糊著瓜果子種子的草灰泥。
老農沒有更多的氣力重復那走了一輩子的田壟,咳嗽中的旱煙味也仿佛來自壯年時的某個寒夜。
現在,老農沒有思想,也不像偶像。陽光、菜花的金黃、此起彼伏的蛙鳴從田野四周涌來。這些幸福的春潮,只有像老農一樣在田地里埋頭耕作了一輩子,把所有春色都錯過的老農,此時才能親切感知。
靜坐家門口的老農,偶爾咽了一口津水,把永遠熟悉而又新鮮的農事默默反芻成底肥。墊進暮年的墓坑,就像自已是一顆等待下地的春種。
平原深處
平原深處,在大路和高樹的遠方,是綠的開闊,是星羅棋布的村舍,是百里雞鳴,是光亮的魚池,是稻田、棉花地,是新架的大棚和葡萄架。
還有紫燕和春風,水杉和電桿并行走進的故園,藍天下的任何一點,都是平原深處經典的關鍵詞。
也就是上兩代人,把水的傳奇,演繹到了極致!
八百里洞庭,水從四面來,種下平原;水從四面走,長出平原。
這個普通而壯闊的故事,從筑垸的箢箕、伐荒的鐮刀、耕耘的犁耙開始.從一個時代的信仰、一句豪邁的口號開始,寫進人和土地、歷史與家園的頌詞。
平原深處,沒有誰比莊稼更古老,也沒有誰比莊稼更年輕。沒有比和一株大豆站在一起更令人感到大地的厚重、踏實,也沒有比一滴汗水與一粒糧食親切交談更深遠的快樂……
平原深處,農墾這個熟稔的詞匯。像擱在鄉音里的農具,只要和土地接觸。就錚錚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