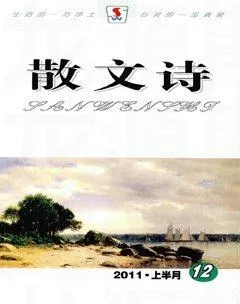許淇《城市交響》選讀
“他的作品表明,他是一位能夠融匯古今中外的大師。”王幅明先生是這樣稱許許淇的。當代散文詩領域中,他是最富開拓精神和學養豐厚、胸懷宏闊的幾位大師之一,最近出版的《城市交響》一書,再次提供了具有說服力的明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過去,散文詩中的城市題材作品依然不多。其實城市不過作為背景而存在,關鍵在于現代化帶給社會尤其是人的狀態的變化這一深刻的課題,尚遠未得到重視,許淇當之無愧地成為開拓者與先驅,理應受到歷史的尊重和足夠的重視。
打開書,想從喜歡的篇目中挑幾章介紹給讀者,最后選定的,并不是他為中國或歐洲城市畫像或剪影的哪一篇,也不是他著意于“交織、復沓、重疊、并列”這樣的“交響音樂”,而是頗為“另類”的幾章。也許,由于我的偏愛,也許應了常言所謂“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的說法,作出的成功創造。往往是其藝術修養成熟和不經意間“流露”出的,最是自然、獨特和天衣無縫。
《嗚咽》的不過是小提琴和大提琴。并非交響,然而卻包容了比交響尤為復雜的“非人間的語言”。全詩的奧妙恰恰在于詩人從中昕出了人間的“痛苦之上的痛苦”、“生的無奈和對轉瞬即逝的祭禱”,這便是在單純中涵納了繁復,最具有散文詩的文體特征,或詩性特征,不是實錄,不是什么“報告體”,也不是交響音樂的直接演奏,不是。而是經由詩人消化了的,加入了自己豐富體驗和想象力改造過,重新奏出的獨特的“音樂”。“嗚咽是灰色的。”詩人用了一系列“猶如”淋漓盡致地給“嗚咽”著色,其語言之多彩多姿,堪稱一絕。“嗚咽是一條老狗”的一段,尤見突出,這嗚咽其實恰恰是現代人內心世界的一個“音響造型”,它“繞著街心公園的一棵樹,繞著河流橋墩暗綠的倒影”已確鑿無疑地鎖定在現代城市的環境中了,而“城市,轟轟然矗起新浴的嬰孩般的樓群”這一結尾更畫龍點睛地點出它的“時代”胎記。這章散文詩的成功告訴我們,現實、生活的原型等等原始的素材越是經過詩人的消化、轉型、加工而升華了,也許越能深刻地表現生活的本質。散文詩不是報告文學,也不是一般的散文,她是詩,是散文詩。
《撥弦渡爾卡》便是為現代化城市中的某種人畫像的了。是人撥“弦”,還是“弦”撥人?我看,恐還是“時勢造英雄”。“你當過流水線插件工,你當過制版工……”這個“不斷跳槽”的“你”,不是一個“個體戶”,而是類型化了的,看起來是“你隨意撥動那上帝的琴弦”,其實是“市場”或社會的“上帝”在“撥動”你,問題的詭秘性在于“你”早已被撥成仿佛“自動”和“自覺”的一根“弦”了。“你是玩家”,這“玩家”二字,恰好掩蓋了被“玩”的真相和實質。
“商品個個似胸脯豐滿的女人和奶色西裝挺括的‘白馬王子’。你口袋里有‘卡’。你要的是多元的布局和充分選擇的自由”,這就十分準確、深刻且形象地揭示了那只“撥弦”之手來自于哪里的現代商品社會的面目了。
語言之跳蕩、靈動與形式的起伏多變也是這章散文詩的特色,顯示了充分的“現代”氣息。尤以“從這根弦到那根弦,撥這弦、那弦:壓、跳、勾攏……”這一節段最為出色。
《一天》是別具特色的一個杰出的散文詩短章,他的語言風格和出奇地冷雋幾近于殘酷地極寫人世匆匆,這一人的悲劇命運的主題,被他處理得如此完善,我以為無論在許淇的散文詩作中,還是在當代散文詩佳作的長廊里,都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
夸張原是古今中外許多文學作品常用的手法,許淇在狀寫人世匆匆這一個盡人而知的現象時,如果僅止于寫實性的平鋪直敘,便不足為奇了,他用了“早晨”“中午”“黃昏”和“夜晚”這一天中的四個時序,所取的意象都十分新鮮、形象、生動,絲毫不落俗套,顯示了他非凡的語言魅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語言。
“鴿子窩棚里,從嬰兒到老朽仿佛只相隔一天”,以及“這弄堂,這亭子間,這閣樓”和“我在煙紙店拷醬油,從踮起腳到佝僂背,仿佛只相隔一天”。
所擷取的“生活細節”,全部來自底層人民,弱勢群體。“窮人的命不值錢”這一副題,便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