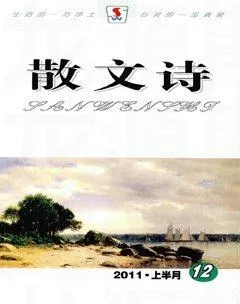雪落村莊
2011-12-29 00:00:00廖淮光
散文詩 2011年12期
這個冬天,在大雪覆蓋的屋檐下,請允許我以淚水的姿勢,成為村莊最后熄滅的火焰。
遠山近水的白,直抵心境,超越任何一部靈魂的詩稿。而我的喉嚨塞滿風塵,我必須牙齒切住牙齒,我不配說出雪地里正在拔節的油菜和麥苗,正在慢慢醒來的蟲子以及小草。
我還必須側著身,給風讓路,好讓一朵雪花抵達另一朵雪花;我還必須踮起腳尖,騰出沉重的空間,任圣潔的光鋪滿大地。
無論怎樣的歌者,都歌不盡綿延雪野的村莊。四處是天籟,遍地是詩行。
我從遠方趕來,一場雪是盛宴。而抵達我的雪還在路上,承載雪的風停在河對邊的柳枝上。
我知道我沒有到達,但必須停下。我要和雪下的白菜站在一起,在這不足二十平米的房間,小小的爐火旁,像母親新添的青柑柴一樣,噼哩啪啦眨著眼睛,淌出血液里沸騰的愛和溫暖。
我知道天空沒有“春運”,燕子會準時回家;我知道覆蓋在村莊的雪被,很快會給草姑娘、花姑娘、蜜蜂公主、蝴蝶仙子收起來。
我知道我們很快又將消失在沙干子坳口;身體里圣潔的光,也將在遠方的路上黯淡下來。
在與父親母親越來越短暫的對視中,一部分已早早地融化。我們無法阻擋一場抵達他們頭頂的雪,哪怕從身體里掏出一千零一個春天。今夜,我的詩歌陷入絕望,在雪落村莊的心底,又厚厚地加了一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