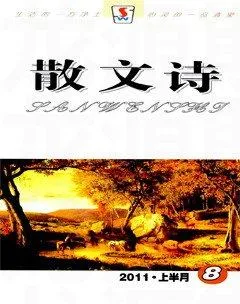人生藝術之眼
陶潛:淡眼
其實就是那么一念一息,就粉碎了人生的沉重與艱難。
斷然不為五斗米折腰,那就優雅地一揮手、瀟灑地一轉身,便把趨附、奔波、奉迎,化作了輕松、超然與悠閑。
精神空間眨眼間就從逼仄變得曠然寬廣。
將又耿又硬的脊梁,掩在寬大樸素的布衣之內。荷鋤,在大地上穩穩站定。
不屑于憤世嫉俗,不屑于桀傲狂放。
頓悟散懷之后,情感的濃度都稀釋在云淡風清的自然大象之中。
只剩下閑適、悠然的淡眼。
連笑意都是很淺很淺的一種深度。
連血流在舒緩中都變得有些微涼。
扶著竹籬,但沒在意它雨中的蕭疏。
采枝老菊,但沒去嗅它霜后的冷香。
連看到南山那美妙的風景,都是無意之中抬頭一瞥的偶然。
淡眼的灑脫,將靈魂高標在孤傲曠達之上。
朱(大+耳):白眼
人生之巢傾覆在比死亡更恐懼的懸崖邊緣之后,人生命運與藝術人生便開始在脈管里奔騰成一種血腥與沉重。
只得抓住寒枝突兀站立,憑借天才的羽毛,擺脫道德的引力,在自由孤寂的半空中漂浮。
酒精在靈臺之上瘋狂舞蹈,無奈與絕望中,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因陶醉而呻吟。超越沉醉與麻木之后,審美意識便置換了悲劇情感。從老莊與魏晉風度那里借來一份瘋癲與超脫,國仇與家恨便蛻變成枯葉蝶的兩只翅膀,人生憑借靈性的力量,掙扎著飛翔起來。藝術氣質的氤氳彌漫,麻醉了改朝換代的慘痛。靈魂的另一種呈現,便在宣紙與水墨的黑白之間萌生。
生命的悲苦、孤傲與沉重,在悲切之美中變成了出神入化的鏡像。把心中對整個世界的態度,都付與了那瑟瑟的羽毛與陰冷眼眸。
白眼,亦僧亦道亦俗,是孤憤反叛后的曠古絕唱;白眼,孤絕飄忽怪異,是悲劇風格的極端詭秘之美。
那鳥兒或側頭瞟眄于傲視,或梗脖閉盱于蔑視,或抬頭瞪眼于憂憤,或閉目養神于不屑,或者干脆在風雨中梳理自己的羽毛,無視于亂世與紅塵。其實,它們都在翻著白眼,逼視那恐懼而無奈的外部世界。
是誰,遠遠逃遁在用天才營造的心理風景之外?他的側目一定也是一串白眼。
“日光七彩,融入一白”。滄桑幻化,盡在其中。雖然孤巖冷寂,鳥兒卻不曾飛去。
頓悟人生的極度卑微之后。禪心慧智又意識到生命的極度珍貴。
那是一只被緊緊縛住的蠶蛹,于無邊的黑暗中,哪怕僅擁有白色的絕望,也要用它來詛咒黑暗的罪惡。
于是,在無法改變的厄運中,他得到一個詮釋苦難價值的機會,讓絕望長出了隱形的翅膀。白眼的深處,是險惡而美麗的風景。
魯迅:冷眼
五千年的專制的文化,加上一個瘋狂的亂世,才孕育出一個把冷眼玩成人生藝術的大師。
破帽遮顏,看鬧市中的百丑之相:漏船載酒,在濁流中將獨醒的孤傲,揚成一片靈魂的風帆。把眉橫成干將與莫邪,不懼千夫所指,冷對血腥的世界。
擲投槍,持匕首,操柳葉刀,以斗士的堅韌與毅然,不茍同,不妥協,不放棄,戰斗不止。對所有的專制、強權、暴政都嫉惡如仇。
冷眼,是白刃上的精光,時時切入一個時代病灶的深處:是真理上的芒刺,每每讓腐朽的體制,產生驚痛的深度感覺。
冷眼。看透五千年“吃人”的舊文化,總把一種悲劇與批判的冷峻,滲透到社會與人生的每個細節之內。
在大師冷眼犀利的鑒照之下,一切用神圣偽裝過的似乎有價值的東西,都黯然失去了耀眼的光環,顯現出它固有的骯臟與丑惡。
“石頭、火種是不會滅的!”
在大師的冷靜與尖刻、固執而傲然的目光背后,深深地隱藏著正義與良知的希望之光。
這光穿透血腥與殘忍的無情世界。
這光穿透虛偽與蒼白的倫理屏障。
這光,成為面向未來世界高擎起來的旗幟與火炬。
石頭的冷峻之中,蓄藏著永恒的火種。
犄角俯首,原來是為百姓大眾馱起自由、尊嚴與幸福的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