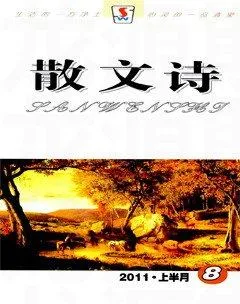節(jié)段與抽象詞語(yǔ)
這樣的現(xiàn)象不難碰到:某個(gè)作家的藝術(shù)追求或欣賞習(xí)慣會(huì)在另一個(gè)作家的作品中得到證實(shí),盡管這兩個(gè)作家相距萬(wàn)里,彼此從未打過(guò)交道,談不上切磋、借鑒,只能以“靈犀相通”“英雄所見(jiàn)略同”加以解釋。
瑞士的法語(yǔ)作家夏爾一費(fèi)迪南·拉繆于1903年出版的詩(shī)集《小村莊》,其中不少篇章采用了散文詩(shī)體。據(jù)譯者陳瑋分析,其因就在于:“散文詩(shī)靈活多變的節(jié)段、意味深長(zhǎng)的抽象詞語(yǔ)引人幻想,它讓思想繞過(guò)瑣碎的事物展翅翱翔,它溝通人和大自然的力量,讓他在風(fēng)與光中盡情徜徉。”而日本著名詩(shī)人谷川俊太郎的散文詩(shī)《棲息的條件》正是這樣的作品。
先看它的節(jié)段。全文共7段,其中第6段“(看似回歸,迷失方向)”又相當(dāng)于一個(gè)小節(jié),確實(shí)“靈活多變”。
再看它的抽象詞語(yǔ):“柄息”及其“條件”,是一連串的動(dòng)作——“隆起”“伸展”“扭曲”“洞開(kāi)”“緊縮”“抽動(dòng)”……確實(shí)“意味深長(zhǎng)”,又確實(shí)“引人幻想”。
正是在節(jié)段與抽象詞語(yǔ)的作用下,作品的思想展翅翱翔,“轉(zhuǎn)瞬之間找到平衡”,盡管“很快就靜靜地扭曲著滑走”,盡管動(dòng)作還在進(jìn)行,但已生出了新的意義:
力從彼方來(lái),力在此生力,力與力較量,被力之網(wǎng)捕獲一般掙扎著,又因力而無(wú)限地?cái)U(kuò)展開(kāi)去,在決不會(huì)被切斷的不規(guī)則性中,孕育著來(lái)路不明的律動(dòng),漫無(wú)邊際——
這也是對(duì)“瑣碎的事物”的“繞過(guò)”,是對(duì)人之力和大自然之力的“溝通”。當(dāng)我們讀到最后一段:
沒(méi)有微觀也沒(méi)有宏觀。星星搖籃里的肉質(zhì)搖籃,我們棲息,享受無(wú)限的暈眩。
不能不對(duì)“生命”“生活”“人性”這幾個(gè)為谷川俊太郎常寫(xiě)的主題加以思考:生命需要平衡,平衡來(lái)自力的較量和互補(bǔ),快樂(lè)地棲息也近乎詩(shī)意地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