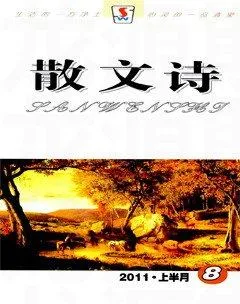走出尷尬的“我們”
我曾提到過,我們不要為了散文詩的“名分”糾纏不休,關鍵的問題在于我們寫了什么,怎么寫的。
如果,我們沒有寫出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我們寫不出具有沖擊力、具有時代特色的作品,那么,在讀者與學者心目中沒有地位,那是自然的,你怨不得誰,只能怨自己。
上個世紀80年代我寫了一篇寓言式的文章,說的是小時候在街頭乘涼的孩子圍在一起講鬼故事,小孩子心理是既想聽又駭怕,說明鬼故事是充滿了魔力的。而散文詩是不是也該有那樣的“魔力”呢?那是在說散文詩怎么寫的事,就是說無論我們用什么辦法,要讓這一文體有“魔力”,能夠吸引人們去讀,這一文體才能在讀者心中有位置,才能在理論家與學者那里獲得“名分”。
“散文詩應該是美的。而生活中那些令人心顫的事,表面看去往往不甚美,甚至是丑的,而丑中又往往有著潛在的美。如果把和諧說建立在表層上去認識,則在生活的開掘上會流于膚淺,就會忽視了潛伏在生活深處的美。只有在生活中深深地開掘,不回避美丑間的碰撞才能達到更高層次的和諧。這當然需要在技法上講究一點,去充分調動起讀者的審美意識,充分利用多維空間。”這是我在1989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詩集的后記里寫的。
一首小詩可以寫得振聾發聵,驚心動魄,一章幾百字的散文詩能不能呢?當然可以。而且短小精悍,恰恰是散文詩的優勢與特征之一。
今天的城市正上演一出前所未有的悲喜劇,中國人都在面臨著一場遷徙,一場心靈的遷徙。就像30年前面臨思想解放的中國,舊的觀念與思想認識阻礙了那時候的社會發展,中國人扇動著沉重的翅膀,掙扎著從舊的巢穴里緩緩地啟動。“清污”“反自由化”“全盤西化”等等,一次次思想交鋒,思想解放在磕磕絆絆中還是走過來了。任何一個歷史關口,都會有“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矛盾。而30年后,我們回顧當時的社會矛盾,結論是不言而喻的。而今天的中國,又面臨著一場變革,是由農村向城市的遷徙。今天的城市如同一個大的意象,在表面形象的后面包含著巨大的欲望,是由貪婪與奢靡組成的欲望。窮怕了的中國人,一旦有了錢更可怕,恨不得吞下整個地球。早已超過警戒線的兩極分化現象導致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無時無刻不在昭示著老百姓生存的艱難。70年前夏衍先生寫下了不到九千字的報告文學《包身工》,在老人95歲生日的時候,他說r這樣一句話:我覺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來。報告文學這一文體的出現與報紙有關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而五四以后,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中國的思想、文化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報告文學在題材和思想內容上取得了巨大突破。許多文學巨匠都寫過這一文體。同情人民生活疾苦、揭露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罪惡、尋求中國出路等等有銳進思想的內容出現在那個時期的作品中。然而這個時期還沒有出現文體的自覺,直到1930年“報告文學”這一名詞才正式被引進應用。從此,被列為詩歌小說散文戲劇評論之外的又一文體,這就是我們要說的“名分”。夏衍先生可以說一生中也是著作等身,可他覺得可以傳世的大概不到九千字的《包身工》是會有地位的。
這里說的大都是些舊事,不是70多年前的事。就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可見這都是一些老生常談了。說得再好,再徹底。也還是那么回事,散文詩是否扣緊了時代,是否有深刻思考與重大命題?這里要說的便是寫什么的問題了。當然,如何將重大命題舉重若輕地寫出來,還是屬于怎么寫的問題。
去年在北京土城子的幾位散文詩人發起了“我們”——北土城散文詩群的態度,用一種強勢的姿態。在今日詩壇謀取一席之地。響應者眾。我瀏覽了部分作品,可以說確實有新銳之感,時至今日,已經在一些報刊上展示了這個群體的面貌。前不久我們雜志社到寧波與《文學港》進行交流的時候,詩人榮榮便向我不客氣地提出。散文詩還是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許多刊物干脆不發散文詩,也就是不予承認,有的刊物勉強接受,但總處于邊邊角角的位置。雖然我的心里覺得更尷尬,但這是事實。
我覺得今天能在這里出席這樣一個百人的散文詩研討會,是近年來很隆重的事情,特別是有了去年的“我們散文詩群”行動的基礎上,再召開這樣的會議,將會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讓我們扎扎實實寫出好作品,寫出反映這個時代,表現真實生活的作品,令散文詩真正走出尷尬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