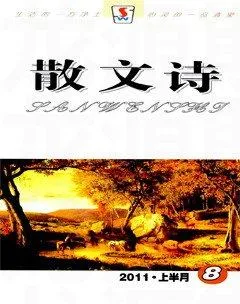覆蓋大地的耳朵
一滴雨落下來(lái)。打在耳朵上:
又一滴雨落下來(lái),打在耳朵上。
如果我在半夜醒轉(zhuǎn),一定是雨水落在了屋外的紅苕葉上。一滴,又一滴。仿佛就從我耳邊滴下去的,蓬的一聲,隨即便滑入了地底。屋外千萬(wàn)只綠色的耳朵都豎起來(lái)了。此刻,村莊都已入睡,只有我一個(gè)人醒著。聽(tīng)見(jiàn)了它們交頭接耳的話語(yǔ),偷窺了它們與土地的聯(lián)系。我感覺(jué)雨水透過(guò)窗戶滴進(jìn)了我的耳朵里,自己也變成了一株紅苕秧,加入到它們中去了,弟兄鋪天蓋地。
第二天我去看時(shí),它們的耳朵平下來(lái)了,一副守口如瓶的樣子。我想說(shuō),我知道它們乘著昨夜的雨水長(zhǎng)高了自己,我知道它們的紅腳板蹬壞了土地的棉被。可是它們?nèi)疾焕砦遥@使我不得不懷疑昨夜的雨水,是不是我的一場(chǎng)夢(mèng)。
整整一個(gè)冬天,我都穿著一件破棉衣。
紅苕怕冷,跟捧瓜(佛手瓜)一起住到了地下的苕洞里。洞口用苞谷稈封得死死的。我去看它時(shí),得提著馬燈,沿一架長(zhǎng)梯上下出入。
一個(gè)冬天快完的時(shí)候,紅苕也就快從苕洞中走出來(lái)了。只是走出來(lái)就再也沒(méi)有回去。留到最后的,就走到了地膜里。
我偷偷地去打開(kāi)地膜看時(shí)。它們?cè)诩S水和熱氣中酣睡。又去看時(shí),就已經(jīng)睜開(kāi)眼睛了。再去看時(shí),紅紅的胳膊就伸出來(lái)了,嫩嫩的,像嬰兒。跟蕃茄苗站在一起,兩小無(wú)猜的樣子。
我常常在想,要是紅苕秧永遠(yuǎn)長(zhǎng)不大就好了,這樣它就可以留在地膜中,就用不著走進(jìn)土地,長(zhǎng)成紅苕,最后又回到地洞里。
就像跟我一起上學(xué)的海昌,如果他永遠(yuǎn)長(zhǎng)不大,就永遠(yuǎn)是我上學(xué)的同伴。就不會(huì)成為南下打工者,就不會(huì)穿我丟棄的破棉衣。
我和他之間的距離,就僅僅是,一棵紅苕秧和一株海椒苗之間的距離。
多年以后,我在遠(yuǎn)離高坪村的一個(gè)集鎮(zhèn)上再次與一群紅苕秧相遇。它們與一群海椒苗相偎在一起,腳上盡是泥土,身上沾滿露水,一束稻草捆縛著腰身。出賣(mài)它們的農(nóng)人,也是一模一樣的打扮,仿佛它們的老父親,或者親兄弟,兩手抄攏,蹲在街邊,沉浸在自己的玄想中。那一刻,我竟有些買(mǎi)下它們的沖動(dòng),有些回到土地栽種莊稼的沖動(dòng)。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多少來(lái)路已無(wú)法返回,我的身份已反轉(zhuǎn),我的土地已荒蕪。
人群擁擠,市聲喧嚷。我像一個(gè)失魂落魄的人。漫無(wú)目的地在集市上穿來(lái)走去。一街盡了,又原路返回……我像一個(gè)闖入者。來(lái)到了一個(gè)上古的小鎮(zhèn)里,又像一個(gè)回鄉(xiāng)的游子,令一村人都感覺(jué)到了陌生,只有我自己發(fā)現(xiàn)了一絲熟悉。
不知什么時(shí)候,紅苕秧和海椒苗不見(jiàn)了,也不知是賣(mài)出去了還是被農(nóng)人順著原路背回了村莊。地上還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們留下的痕跡。街道空了下來(lái),仿佛一個(gè)戰(zhàn)場(chǎng),剛剛還人聲鼎沸,如今卻只剩下了一地狼藉。人們從買(mǎi)賣(mài)中迅速撤退,立刻消失在時(shí)間深處。他們仿佛約好似的,一哄而散,把我一個(gè)人,丟在了集市里。
鳥(niǎo)聲如洗的村莊和樹(shù)林
組建一座村莊其實(shí)很簡(jiǎn)單。只需一二瓦房,三四薄土,五六樹(shù)林,七八牛羊。
最多,再添九十鳥(niǎo)聲。
可是那時(shí)候,我沒(méi)有聽(tīng)到過(guò)鳥(niǎo)聲,我只聽(tīng)見(jiàn)麻雀、鴉雀、毛蓋雀、大娘點(diǎn)、黃凍兒……它們一直在為什么而爭(zhēng)吵,嘰嘰喳喳的。
我沒(méi)有聽(tīng)到鳥(niǎo)聲。
我聽(tīng)到鳥(niǎo)聲時(shí)是在深夜。這是我有生以來(lái)第一次在半夜里醒來(lái)。仿佛就在我的屋外,又仿佛在青木轉(zhuǎn)深深的樹(shù)林里。仿佛一只,又仿佛若干只。我不知道是什么鳥(niǎo)叫的,它披著夜色的衣服,反正是我從來(lái)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的。人們深深地睡著了,去了另一個(gè)世界,把我一個(gè)人丟在黑夜中,沒(méi)有人可以回答我的問(wèn)題。我確信黑夜的高坪村此時(shí)只有一個(gè)人醒著,來(lái)面對(duì)這些鳥(niǎo)叫。我感覺(jué)到夜涼如水,在鳥(niǎo)聲里緩緩地流動(dòng)。它飄忽、閃爍、停頓,使夜顯得更加幽深和曠遠(yuǎn)。
第二天醒來(lái),我再也找不著它們的痕跡,仿佛跟黑夜一起消失了。我只看見(jiàn)樹(shù)椏間仿佛有它們站立過(guò)的身影。我查對(duì)過(guò)麻雀、鴉雀、毛蓋雀、大娘點(diǎn)、黃凍兒……這些村莊里所有我見(jiàn)識(shí)過(guò)的鳥(niǎo)類(lèi)。我相信鳥(niǎo)聲絕不是這些鳥(niǎo)發(fā)出來(lái)的,那應(yīng)該是一種體形更大的鳥(niǎo),它在夜晚人們都睡著了的時(shí)候飛臨,用翅膀和叫聲籠罩了村莊,讓它沉浸在睡眠和黑暗里。
我特意觀察了村頭那棵百年梨樹(shù)上巨大的鳥(niǎo)巢。自我記事起,它就一直懸掛在那里,高高在上,仿佛村莊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它的高度和球形隆起,足以成為村莊的標(biāo)志性建筑。年年都有鴉雀飛來(lái),在上面筑巢。我確信鳥(niǎo)聲也不是那上面的鴉雀發(fā)出來(lái)的。它跟村莊里的人們一樣,天一黑就睡了,忙于休整疲憊和生兒育女。
從那以后。我就經(jīng)常聽(tīng)見(jiàn)了鳥(niǎo)聲。它將我的夜晚攔腰切斷,把睡夢(mèng)中的我活生生地扯起來(lái)。我相信我的煩惱就是從那個(gè)夜晚開(kāi)始的。從此以后,我不得不在鳥(niǎo)聲叫醒我的夜晚想一些不著邊際的事情。我的夜晚開(kāi)始變得不連續(xù),既漫長(zhǎng)又短暫。在此之前,我的夜晚和白天是完全斷開(kāi)的。我一睜開(kāi)眼,直接就走向了早晨。
我一直以為,村莊是從木格窗的四方嘴里開(kāi)始天亮的。多少個(gè)夜晚,我忙于長(zhǎng)大,錯(cuò)過(guò)了鳥(niǎo)聲。它們也許從半夜就開(kāi)始工作了,用夜色練習(xí)聲帶,磨礪硬喙,一聲聲呼喚著睡去的村莊和長(zhǎng)大中的我。這天夜里,我迷迷糊糊地醒來(lái),突然就聽(tīng)到它們了,是鳥(niǎo)聲。像洗過(guò)一樣,靜靜地流過(guò)瓦房和樹(shù)林。我感覺(jué)到一滴露水正在輕輕滑過(guò)一棵杉樹(shù)的枝頭,我甚至感覺(jué)到身體中的我正在慢慢蘇醒。很久以來(lái),我都不知道,它們一直和我一起住在同一個(gè)村莊里,就在我屋外石墻邊的樹(shù)林中。如果沒(méi)有鳥(niǎo)聲,村莊一定會(huì)睡得太沉忘了醒轉(zhuǎn),而我,也許就不會(huì)知道在睡夢(mèng)中醒來(lái),學(xué)會(huì)思考和傾聽(tīng),就再也不會(huì)長(zhǎng)大,永遠(yuǎn)停留在那個(gè)夜晚以前的夜晚,不顧大人呼喊,沉沉昏睡——夜晚一定是村莊溫柔的蛋殼,無(wú)數(shù)不知名的鳥(niǎo)用喙將它一點(diǎn)點(diǎn)啄破,迎來(lái)了黎明。
多年后,我認(rèn)識(shí)了一些字。那些兩個(gè)黃鸝鳴翠柳的黃鸝,一行白鷺上青天的白鷺,哆啰啰哆啰啰寒風(fēng)凍死我的寒號(hào)鳥(niǎo)……我不知它們?cè)诟咂捍宓拿郑抑溃鼈円欢ň烷L(zhǎng)在高坪村的林子里。不被我看見(jiàn),卻叫聲不斷,清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