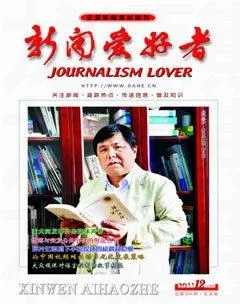論電視成就報道內容的創新因素
摘要:與以往重大成就報道不同,央視“回眸十一五”大型系列報道《我的這五年》首次聚焦普通中國人的夢想故事,讓表情訊息代替成就數據進入公眾視野,讓前臺主題信息退至后臺,歸因模式更加開放和務實,編碼方式更加體現協商性而非主導性,從而在與觀眾的心靈對話中實現了輿論引導。
關鍵詞:《我的這五年》 成就報道 輿論引導
從2010年11月10日開始,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新聞頻道隆重推出了“回眸十一五”系列報道《我的這五年》,首次聚焦“普通人的中國夢”,每天為觀眾講述一個尋常百姓的故事,前后持續了4個多月,共100多集。同樣是主題報道,但這次的報道卻讓人耳目一新,直達靈魂深處,讓人久久不能釋懷。那么,這些報道中究竟有哪些元素吸引并打動了我們,又有哪些成功經驗值得我們今后借鑒和汲取呢?以下,我們可以從表情訊息公共化、前臺信息后臺化、歸因模式理性化、編碼方式協商性等層面來加以剖析。
表情訊息公共化
美國社會學家埃爾溫·戈夫曼在他的一項社會交往分析中,曾區分了“表情”和“傳播”這兩種概念。他認為,“表情”指的是姿勢、符號、聲音、標記以及某個環境中某個人出現所產生的運動。而“傳播”則指的是使用語言或類似于語言的符號,有意識地傳遞“訊息”的行為。按照這種區分方式,一個人可以隨意地開始或停止傳播,但是他不能停止表情的表達。傳播是有意識地進行,表情則是無意識地“流露”。而在電視上,表情的重要性通常超過語言——“電視上演講的政治家即使引用了其他人的文章或詩句,這也能反映出他的個人哲學,這也會使觀眾高興。相反,如果某位政治家讓別人代替自己發表媒介演講,他將會疏遠觀眾,即使那些話都是政治家親自寫的,效果也一樣。”①可以說,電視上豐富的節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的是表情訊息而不是傳播內容。
但是,回顧以往的電視主題報道特別是成就報道,見事不見人,很多都是總體性的陳述和枯燥的數字羅列,是傳播內容,而不是表情內容。即便是所謂的“點面結合式”報道,“點”的表情內容也是有限的和被遮蔽的,是為了說明和印證“面”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但是,在《我的這五年》大型系列報道中,作為公民的個人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等表情訊息卻成為報道的主體,進入了公眾視野。看完報道后,作為觀眾,可能不一定會記得主人公在這五年當中到底取得了哪些成就,但他們的音容笑貌和人格魅力卻給觀眾留下了永遠的記憶。如長期堅守大山無暇顧及家庭而在班會上向女兒道歉的青年教師馮雪紅,靠賣羊肉串維持生計卻矢志資助貧困學生的樸實漢子阿里木,懷著拍電影的樸素愿望并堅持不懈一點點靠近夢想的彭家兄弟,騎著自行車上街以防代管、以幫代管的“最美城管”楊維勛……這些人物的一幕幕影像活生生地留在了人們的記憶深處。
與表情內容的傳遞相適宜,系列報道很多都采用了第一視角、訪談、音樂等表現手段。如《孫恒:音樂老師變身博物館館長》開篇就是一段內心獨白:“我叫孫恒,今年35了,我出來打工12年了,我干過很多工作,有過很多夢想,也實現了一些,比如他們叫我團長,因為我是新工人藝術團的團長;他們叫我校長,因為我是同心打工子弟學校的校長。但說實話,再怎么做夢,我也沒想到我能成為一名館長,現在我是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館長。”而《阿里木:賣羊肉串的慈善家》則在報道的最后安排了一段配樂的、類似意識流的心愿表白:“我覺得我烤的羊肉串太好吃了,我太厲害了,旺季的時候我就想烤羊肉串,淡季的時候我就想娶老婆,我要一個不打麻將的老婆……”這些無疑進一步增強了報道的感染力。
前臺信息后臺化
美國社會學家埃爾溫·戈夫曼認為,所有社會角色的行為實際上都是表演,是一種有選擇的展示。任何人在某個環境中的行為都可被分為兩類:前臺行為和后臺行為。在前臺,他們要扮演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概念的社會角色;而在后臺,他們可以放松地演練、琢磨將來演出的策略。基于這一面對面交往理論,美國傳播學者約書亞·梅羅維茨提出,電子媒介的廣泛使用創造出了新的社會場景,這一場景融合了前臺行為和后臺行為,帶來了人們對“恰當行為”觀念的改變,其重新塑造行為的程度遠遠超越了它所傳遞的具體信息。
這一觀點正在被現在的媒介現象所證實。新媒介環境下,人人都是公民記者,人人都可隨時發布信息,前臺信息和后臺信息的交織融合作為一種新的信息傳播模式和信息消費習慣逐漸被觀眾所接受。而以往傳統媒體單一的前臺信息或前臺信息與后臺信息的不一致都會極大地降低報道的公信力。當然,所謂的前臺、后臺也是相對而言的。如果說我國“十一五”期間的巨大成就是前臺的話,那么諸多小人物的艱苦奮斗就是后臺;如果說典型人物的事跡是前臺的話,那么他們為此所作出的巨大犧牲就是后臺;如果說他們的態度是前臺的話,那么整個社會的普遍看法就成了后臺。而后臺信息往往因為比前臺信息顯得更真切、更誠實而更容易得到認同。因此,如何來分配、組合前臺信息與后臺信息,就決定了一則報道的可信度和影響力。以往,我們的成就報道只有“成就”的前臺信息,而沒有為之付出的“人”的后臺信息,這種報道自然難以讓人信服。而在《我的這五年》中,這種傳播模式已然發生變化。圍繞成就的人的奮斗和拼搏成為前臺,而政策的雨露、時代的進步則成為后臺。如致力于打造百年農業企業的盧國平,如果沒有糧食補貼和農機補貼的好政策,恐怕很難成就一番事業;建成北京最大養老院的宋玉梅,如果沒有國家對民營養老機構的優惠政策,最后也只能宣布破產;還有讓集團70%~80%的員工都能買房、買車的沈陽雜技演藝集團(原沈陽雜技團)董事長安寧,如果沒有國家文化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他和他的員工恐怕也只能黯然接受被市場淘汰的命運。但是,這些主題信息在報道中并非顯性的、前臺的,而是隱性的、后臺的,這種主題的“退卻”反而使得內容更加真實可信、深入人心。
歸因模式理性化
社會心理學的歸因理論認為,人們對行為的解釋主要有兩類:一是認為行為的發生是由于情境因素所致,被稱為外向歸因;二是將行為發生的原因歸于行為者個人性格或其所具條件,被稱為內向歸因。
而對于成就報道或主題報道來說,其實也都涉及一個歸因的問題,即成就緣自什么因素。以往的報道經常通過采訪對象或記者點評來揭示這一因素,而這也往往就是節目的主旨所在。但是,綜觀大多數成就報道,這種歸因基本上都是封閉的、單向度的。要么把成就歸因于“人定勝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要么一味地歸因于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這種歸因簡單片面,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也難以起到輿論引導的作用。而在《我的這五年》系列報道中,歸因是多元的,也是客觀務實的。報道中的這些主人公,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既得益于國家發展的大背景,也是個人堅守夢想并努力奮斗使然。甚至可以說,沒有個人的內在因素,外因是很難起作用的。因此,我們看到,每篇報道的最后,記者現場出鏡都會提到“理想”、“夢想”、“幸福感”、“人生價值”這樣的字眼。如《彭家兄弟:一部傳奇電影的誕生》中最后說道:“其實在我們小時候,對于長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這些大大小小的夢想就像種子一樣種在了我們的心田,長大以后有些夢想并沒有走遠也沒有消失,只是被我們深深地埋在了心靈深處。如果用虔誠的情懷去善待這些夢想,在條件合適的時候,它們就會發芽,就會結果,就會夢想成真。”再如《付新華:尋找心中的螢火蟲》中,記者最后說:“付新華的故事給我們的最大啟示就是:浮華之下,雖然理想的光亮有時候會顯得很微弱,但它值得我們每個人去追尋去守護,因為它終將照亮我們的人生。”這里的歸因,沒有豪言壯語,也沒有嗆人的宣傳味道,而是一種基于現實考慮的、與觀眾之間的心靈對話。這種對于成功的歸因是開放的、多元的,也是能引發觀眾思考并被觀眾所接受的。
編碼方式協商性
英國學者斯圖亞特·霍爾認為,電視觀眾對電視節目的解碼實際上是一個意義的再生產過程,即解碼過程并不是完全依據編碼來進行的,二者不是同一的。霍爾由此假設了解碼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三種不同狀態。一是“主導—霸權地位”。受眾的解讀完全在編碼者主導符碼范圍內進行操作,根據用以將信息編碼的參照符碼把信息解碼。二是“協調的符碼或者地位”。在這種狀態下,受眾的解碼包含著相容因素與對抗因素的混合:它認可主導性定義界定的合法性,同時又在一個更有限的層次上制定自己的基本規則,并使這種主導界定適合于它本身團體的地位。三是“對抗符碼的操作”。受眾有可能完全理解話語賦予的字面和內涵意義的曲折變化,但卻以一種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碼信息。
依照這一理論,我們會發現,以往的成就報道主要是一種基于“主導—霸權”地位的編碼方式——大而空的報道視角,枯燥乏味的報道內容,居高臨下的報道語態。而出于對傳統媒體特別是官媒背后的意識形態的信任和敬畏,這種傳播模式曾長期存在并曾在凝聚人心、鼓舞士氣、教育群眾等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新媒體時代,網絡、手機使得每個人都能夠搜集、發布新聞信息,每個人都是“自媒體”。媒介的接近權、使用權成為每個公民的共識,由這種權利衍生的媒介素養問題日益受到重視并得到不斷提高。同時,在文化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傳統媒體市場化進程加速,政府與媒體的關系日益松動,單純的喉舌功能已很難概括媒介的全部社會職能。因此,今天的成就報道如果繼續沿用以往的編碼模式,非但不能贏得公眾的認同,反而極易遭遇受眾的“對抗式閱讀”。畢竟,在今天這樣一種傳播語境中,作為傳統媒體的記者編輯,不論你知道多少,總有人比你知道得更多;不論你的分析如何專業,總有人比你還專業;不論你的立論如何公正,總有人能夠指出你的不足。因而,改變傳統的編碼方式自然就成了一種必然選擇。
在央視《我的這五年》系列報道中,我們看到,以往靜態的、宏觀的“國家成就”演變成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的經歷。在這五年中,他們有夢想、有波折,五年來的國家成就并沒有遮蔽作為個體的人的磨難和苦痛,而且,恰恰是因為這些個體的奮斗和拼搏才有了國家層面的發展。可以說,這一事實建構幾乎符合所有群體的現實語境,因而顯得自然親切而不至于遭到部分社會群體的對抗解讀和輿論抗議。同時,報道素材充分調動畫面、同期聲、音效等電視手段,堅持用事實來說話,用故事和情節來說話;記者的點評也是在事實分析和他者言說的基礎上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見解,溫和中肯,啟迪人心,絲毫沒有說教的意味。
例如,在《旭日陽剛:春天里的怒放》中,記者向觀眾介紹了農民工劉剛和王旭的愛好、執著、艱辛和一夜成名。在報道末尾,記者點評說:“有人感嘆,是網絡讓旭日陽剛一夜走紅,有人說,農民工身份給了他們許多感動的元素。但我想,他們所引發的共鳴,更多的是來源于他們和許多普通的勞動者一樣堅持一個簡單的信念——只要付出,就有回報。”這樣的評論在充分體察他者意見的基礎上給出了記者的“我”的觀點,沒有頤指氣使,也沒有居高臨下,是一種人格化的傳播,也是一種協商式的編碼方式。而正是這種編碼方式的轉變,才使得成就報道洗盡鉛華,進入了觀眾的內心。(本文為孝感學院湖北小城鎮發展研究中心2010年度開放科研項目“新媒介環境下大眾傳媒的鄉村傳播與社會穩定研究”的部分成果,項目編號:2010K07)
注 釋:
①約書亞·梅羅維茨[美]著,肖志軍譯:《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頁。
(黃欽為孝感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王文春為江西電視臺廣告中心企劃部主任;熊欣為孝感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學生)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