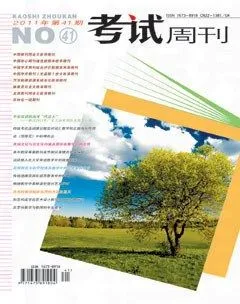孽海之花
摘 要: 小說《孽海花》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關系及其發展作為一條主線,描述了近三十年的政治文化變遷狀況,顯出了作為歷史小說的厚重內涵。本文重點論述了《孽海花》的人物性格的刻畫,傅彩云就是《孽海花》中最具光彩的一個,文章從人物性格、結構價值、倫理思想方面寫出傅彩云對自由的追求和向往是與傳統妓女形象的最大區別。
關鍵詞: 小說《孽海花》 傅彩云 形象描寫 形象意義
小說《孽海花》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關系及其發展作為一條主線,描述了近三十年的政治文化變遷狀況,顯出了作為歷史小說的厚重內涵。這種“長線穿珠”式的結構雖然具有涵蓋巨大時空的功能,但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卻不能兼顧。但若與同時代創作相比,《孽海花》的人物性格的刻畫是相當成功的。傅彩云就是《孽海花》中最具光彩的一個,“從接受的角度看,《孽海花》中最有吸引力的人物是傅彩云(賽金花)”。[1]“她有見地,有手腕;又溫順,又潑辣;剛毅果斷,伶俐聰明;既苦于受人虐待,又善于虐待他人。她早年的可憐的賣笑生涯,迫她鍛煉出一付討人喜歡的伶俐性格;接下來的豪侈的命婦地位,又使她養成一種令人痛恨的殘忍心腸。這些,作者都描寫得很好。全書凡寫到彩云的地方,莫不有聲有色”。[2]
曾樸之子曾虛白在《虛白附識》中這樣評價傅彩云的結構價值:“在《海》本身的中心意義來說,她是一個無關文化的推移,無關政治的變動的絕不相干的人物。”他認為,組織上重要的人物,不一定是一個必須有特點的人物。也許他認識到了這種說法的偏頗,他又說了這樣一句話:“彩云還有她的‘美貌’與‘色情狂’。”[3]由此可見,傅彩云的價值并不體現在結構中,而體現在審美意義上。雖然作者的側重點在政治文化方面,但在傅彩云的身上,卻反映了其藝術審美情趣的超功利性。
自《霍小玉傳》始,傳統小說中塑造了一大批妓女的形象。這些生活在下層社會、屈辱環境中的女子,把自己的出路寄托在讀書人和做官人身上,面對強大的男權社會,這些柔弱女子的想法本無可厚非,但能夠像《李娃傳》中的李娃那樣有個美滿結局的,幾乎是絕無僅有的,明代小說《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杜十娘落得財破人亡的結局就是打破這種幻想的證明。《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的美娘則把她的視角轉向了做生意的李重,是對這種模式的一次突破。《孽海花》中的傅彩云又體現了妓女的另一種寫法,在才子佳人的基礎上,更多地染上一層現代性色彩。
傅彩云不同于傳統妓女形象的最大特點是她的獨立個性,在這一點上,也許可以說她是“覺醒的杜十娘”。她與金雯青是一見鐘情:“雯青一雙眼睛好像被那頂轎子抓住了,再也拉不回來,心頭不覺小鹿兒撞。說也奇怪,那女郎一見雯青,半面著玻璃,目不轉睛地盯在雯青身上。”這是一種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如果這樣寫下去,也脫不了傳統小說的手法而陷入俗套之中,傅彩云也就成為“類”中的一個了。曾樸不是抱著贊美或是同情的思想去描寫傅彩云。在他的無意識深處,女性降為物的等級:“那國民自以為是:有‘吃’,有‘著’,有‘功名’,有‘妻子’是個‘自由極樂’之國。”這自由之國的國民自然是不包括女性的。但受過西洋文學寫作技巧影響的他還是有著不同于傳統的思維方式,寫出了“中國帝制的封建社會里寫妓女的壓陣之作”。[4]
傅彩云表現出獨立個性的開始,是在隨金雯青出使國外的船上,在傅金的對比中,顯出了傅彩云的機智聰明和金雯青的懦弱無能。他們倆同隨夏雅麗學德文,金雯青是因為羨慕夏雅麗的美貌風度,苦于無法親近;彩云卻是早有學文之意,“不到十日,語言已略能通曉”。當夏雅麗亮出手槍責問金雯青的無禮時,金雯青“倒退幾步,一句話也說不出,還是彩云老當,化解了此事”。“使臣為一國代表,舉動攸關國體”,金榜題名的狀元金雯青表現如此,也足以窺見大清國的氣運了。“才子”不再是封建社會女性心中的偶像,他們地位的衰落,也反映了在西方文化沖擊下知識分子者的心態轉變。
對自由的追求和向往是傅彩云與傳統妓女形象的最大區別。當然,我們也可說“從良”是妓女追求自由的一種表現,盡管那只不過是從一種不自由變成另一種不自由,從眾人的所有變為一人的專有。她們的故事在虛幻的幸福結局中落幕,而幕后的故事才是女性生存的真實——守德或是守節,在“三從四德”中度過無愛為私的一生。傅彩云沖出了綱常倫理對女性的重重包圍,走上了個性自由的道路。她不是一個遵守三從四德的家庭婦女,并沒有因感金雯青的知遇之恩而戒守婦道。在自身的意義上,她將自己作為一個“人”而不是一個“女人”來看待。女人和男人一樣,都有著七情六欲。金雯青恰恰是在這一點上忽略了,所以才不斷地有傅彩云與仆人阿福的私通,與瓦德西的相慕,與船主質克的“風波”,以及與孫三的勾搭,硬把一個金科狀元活活氣死。她好于阿福的伶俐、瓦德西的英武、孫三的俊俏、金雯青的才氣,肆意地玩弄著男人世界,而這些人只是垂涎于她的美貌和錢財。最后,她又懸牌于燕慶里,重操舊業。也許,她就是維亞太太所說的“放誕的美人”。她認為,對于男人,“只可我玩了他,不可被他玩了去。況且一個女人家,就不得自由,何苦脫了一個不自由,再找一個不自由呢?”自由花神,豈肯付東風拘管?傅彩云依據生命欲望原則所展示出來的“放誕”活力,使以倫理道德為基礎建構起來的男性主體顯得蒼白而虛偽,這應該是傅彩云身上承載的時代意義的價值所在。
封建社會中一部分優秀知識分子認識到了女性的悲慘境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也僅在有限的范圍內,且兼有說教色彩。所以,那些由婦女自己發出的反抗心聲,便具有振聾發聵的效果。在金雯青發現彩云與阿福之事后,傅彩云說出了這么一段話:“你們看著姨娘本不過是個玩意兒,好的時抱在懷里、放在膝上,寶呀貝呀的捧;一不好,趕出的,發配的,送人的道兒多著呢!……當初討我時候,就沒有指望我什么三從四德,七貞九烈,這會兒作出點兒不如你意的事,也沒什么稀罕。你要顧著后半世快樂,留個貼心服侍的人,離不了我!那翻江倒海,只好憑我去干!要不然,看我侍侯你幾年的情分,放我一條生路,我不過壞了自己罷了,沒干礙你金大人什么事。……老實說,只怕你也沒有叫我死心塌地守著你的本事嘎!”這幾句話“句句刺心,字字見血”,掀開了蓋在金雯青一類封建士大夫臉上的假面具,活現了他們的丑惡靈魂和污穢行為,是女性對男性的不加掩飾的正面抗爭。女性無論從身體上還是從心理上都是柔弱的,一旦走上徹底的決絕之路,她們的反抗便具有摧枯拉朽、橫掃一切的能量,籠罩在她們頭上的男性陰影也消失殆盡。在男權社會中,女人一直作為男人的附屬物存在,女人敢說這樣的話,確實是驚天動地的。即使潑辣如王熙鳳者,在發現賈鏈偷情一事后,也只是小吵小鬧一番,將此事不了了之。盡管她已成為賈府重要人物,但一旦她脫離賈鏈,她也就脫離了賈府。失去了經濟基礎,女性只能生活在男性的鼻息之下。傅彩云為了自由,卻可以拋棄公使夫人的身份、地位、財富,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來源,雖然是重操舊業,可是在那個社會,女人似乎再沒有別的途徑來自謀生路了。她們的一切都是男性給予的,唯一能支配的就是自己的身體。如果連這一點也做不到,女人就不成為人,她們自己也覺得是物了。從良的妓女就是最終放棄了這種身體權力回歸到男權社會為女人規定的位置上。傅彩云的“重操舊業”是對身體權力的尋求,從而試圖找回為“人”的真正含義——盡管是以屈辱和沉淪作代價,可在“孽海”中,這也只能是一種別無選擇的選擇。
作品是作家世界觀的反映。傅彩云的形象似乎寄托了作家曾樸的某些倫理理想,但事實并非如此。雖然曾樸在政治文化方面表現了先進思想和開闊視野,但就倫理思想來說,他還是具有非常濃厚的封建性——他一直就不承認傅彩云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并且,傅彩云批駁金雯青的那段最激蕩人心的話,只是一種寫作技巧上的處理,而非他思想的映射。曾虛白曾這樣為這幾句話作注腳:“作者當時的本意是要表現彩云的刁,和她挾持雯青的手段,純粹是設身處地客觀地描寫彩云應付這樣難題的巧妙,并不是在表現彩云處事的人生觀。這幾句話,也許都是彩云的謊話,只可見她的狡,不能信她的誠。”[5]其實,這段話倒真顯出了傅彩云的誠,倒是她向張夫人要求放她走的話,才顯出了她的“狡”——她話中處處為金家著想:一怕毀金家名聲,二怕化缺銀錢,其實這才是真正的挾持金家。
最重要的是,雖然曾樸寫出了傅彩云對男性世界的揭露與反擊,但這卻是在一個迷信的、“因果輪回”的背景中展開的。在開篇詞中,他就這樣寫:“孽海漂流,前生冤果此生判。”說傅彩云是贈金雯青進京趕考盤纏的煙臺妓女梁新燕,金中了狀元后,違背前約,使梁上吊自殺。那么,金雯青和傅彩云因有了這樣一個“楔子”,他們的一見鐘情是自然而然的,傅彩云以放蕩成性的方式對金雯青進行報復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因為這樣一種報復在傳統文化觀念中是被認可的。這樣一來,傅彩云身上蘊涵的社會意義便被解構了,小說又呈現出傳統小說說教與警世的特點,頗有幾分《三言二拍》、《警世恒言》的遺風。先進的政治思想和落后的倫理意識在曾樸身上滑稽地對立起來,透露了站在現代性門檻前的中國早期知識分子的復雜心態。
當然,傅彩云的形象描寫并非盡善盡美,這既有作者思想的不足,又有時代的局限。就形象意義而言,她體現了近代女性的覺醒意識,雖然有些朦朧,并且還是一個“被娼妓、納妾制度扭歪了性格的女性形象”,[6]沒有體現出更積極的色彩,但畢竟透出了女性追求獨立自由的曙光。從這個意義上說,傅彩云可視為“五四”時代沙菲們的先驅者。
參考文獻:
[1]歐陽健.《孽海花》難以終篇的內在原因——試論傅彩云的配角地位社會科學輯刊,1991,6.
[2]張畢來.孽海花·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魏紹昌編.孽海花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00-201.
[4]陳遼.中國文學中的別一景觀.江蘇社會科學,1999,3.
[5]魏紹昌編.孽海花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01.
[6]王祖獻.孽海花論稿.黃山書社,1990,6: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