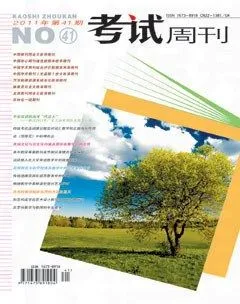尹雪艷:永遠的上海象征
摘 要: 臺灣作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說集《臺北人》以《永遠的尹雪艷》為開篇之作,描寫了動蕩變遷時代之下的眾生相。尹雪艷公館儼然成為眾人沉湎舊夢的場所,而尹雪艷本身就是上海的一種象征:精英文化,貴族氣息。眾人在尹雪艷及其公館尋得在時代洪流中失落了的身份認同。作為上海象征的尹雪艷,似乎在娛樂中只身抽離在外,而這種冷漠背后卻潛藏深刻的時代痛感。
關鍵詞: 《永遠的尹雪艷》 尹雪艷 上海舊夢 “符號”
臺灣作家白先勇通過塑造從大陸去臺灣的各色人物,并賦予他們豐富的內涵。《永遠的尹雪艷》是短篇小說集《臺北人》的開篇之作,以尹雪艷為中心,描繪了動蕩變遷時代之下的眾生相。透過眾人的眼睛,在紛繁的內涵之中卻看到尹雪艷成為一個“上海”的符號和代名詞,身份模糊的眾人試圖在她身上尋找丟失了的身份認同,縫補社會變遷下的時代痛感。
在白先勇的《游園驚夢》中,人在歡娛中的錢夫人仍不免懷想過往的日子,那些在南京的日子如繁花錦繡。唱戲,始終是貴族人才有的閑情;戲子,總歸是要有臉面的人去捧才不致作賤。坐席間,她的一把好嗓子贏來眾人的期待與喝彩。然而眾人期待的確是錢夫人嗎?也許不過是在酒席朦朧間,乘興而忘乎俗世名利地位種種一切,眾人開懷一心玩樂。到最后,錢夫人與眾人等在站臺,看著歡聲消散,卻要尋輛的士離去,不盡的是濃濃的失落感。《游園驚夢》里多談及對往日的眷戀,人物在現實中無可適從,只能從舊日回憶中找回自己的身份想象。而在《永遠的尹雪艷》中,硝煙彌漫的變遷時代給歷史洪流中的大小人物帶來濃濃不盡的悲哀,人物失去了身份認同,面對時代變遷的失落感顯得更加沉重。
尹雪艷的形象并不突出鮮明,更確切地說,尹雪艷不過是一個“符號”——一個關于上海舊夢的符號與象征。正如文章中多次提到的:“不管人事怎么變遷,尹雪艷永遠是尹雪艷。”符號化的尹雪艷象征著上海生活的奢靡,其實是“不管人事怎么變遷,奢靡的上海生活始終是一代人揮之不去的美夢”。尹雪艷沉睡在眾人的上海回憶中,是眾人眼中的上海舊夢,每個人都在這里尋得昔日的身份認同、身份想象與時代想象。
大人物如遭受社會地位突變的吳經理,時不時哀怨自已無用;小人物如體形變得肥胖了的宋太太,對美好年華的戀戀不舍、無限追憶……對這些失去了昔日身份的人的心理描述,使得文章處處無不彌漫著對過往上海的深深眷戀。上海在王安憶的筆下,被刻畫成典型的文化符號,“作者在整篇小說中無法掩飾地流露出對于舊上海的眷戀,王安憶把舊上海的令人眷戀的種種特征添加在王琦瑤身上,讓讀者在王琦瑤身上嗅出舊上海的味道,聽到舊上海的旋律,再見舊上海的繁華”,充滿情調。而尹雪艷,是典型奢靡上海生活的典型代表:“在小花園里挑得出最登樣的繡花鞋兒”,“紅樓的紹興戲碼,尹雪艷最在行”,“論起西門町的京滬小吃,尹雪艷又是無一不精了”。更何況,“尹雪艷公館一向維持它的氣派。尹雪艷從來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飛路的排場”。凡此種種,都是精英文化的象征,凝聚貴族氣息。眾人喜歡流連于尹公館,看似貪圖其間的醉生夢死,更深層次的心理因素是貪圖曾擁有過、而今不復返的種種虛華,企圖借此尋回身份認同。大家曾經“有他們的身份,他們的派頭”,而如今有些人是“過了時的”,但是,“一進到尹公館,大家都覺得自己重要……經過尹雪艷嬌聲親切地稱呼起來,也如同受過誥封一般,心理上恢復了不少優越感”。在尹公館這個舞臺上,尹雪艷一手制造了上海種種的舊夢,不斷召喚起眾人的身份意識及遠去的身份優越感。
浮華之下,也無所謂有情、無情,相盈其間,盡是歡娛,然而這背后盡是一個時代裂變帶給人們的痛感。徐壯圖本該是“年壯而有所圖”的中年男人,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年輕有為,是個雄心勃勃的企業家。然而,卻因著一雙眼的流波百轉,而性情大變。文章細寫了徐先生與尹雪艷的交會,在打麻將間曖昧味濃。卻是借徐太太的口,轉而用她的視角,講述了一個月來她眼中徐先生與尹雪艷的來往,徐壯圖沉迷于外遇中。本該濃墨重彩描寫的兩個人,卻又只托由徐太太等人講出徐先生之大變,故事急轉直下,以徐先生突兀的死來突兀地結束這段故事,讓人始終摸不著尹雪艷的感情——醉笑歡宴百余場的尹雪艷究竟是否動了真情。此部分似乎顯得粗糙、突兀,欠缺真實感,然而這樣的處理也許別有意味。尹雪艷去吊唁,“凝著神,斂著容,朝著徐壯圖的遺像深深地鞠了三鞠躬”,引起靈堂眾人一陣驚愕,卻又沒有留下只言片語,“卻踏著她那風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殯儀館”,把靈堂弄得“一陣大亂,徐太太突然跪倒在地,昏厥了過去”,卻沒再描寫尹雪艷之后的心情,尹雪艷和徐壯圖之間的故事結束了。敘述正像尹雪艷的來去如風,空蕩、缺乏飽滿內容的支撐,白先勇只提供了零碎的線索,剩下的內容留待讀者去追蹤與想象。這種敘述處理正暗示著尹雪艷公館的特征:虛浮、飄渺、來去無痕。徐先生與尹雪艷有所糾纏,投入感情的動心曖昧,卻轉而消散。這正像是上海,每個人沉湎其中,做過一場場繁華舊夢,而今美夢褪去,只留只身空白,路過了歷史上的上海,又走進了一個真相不明的新世界,每個人都只是匆匆過客。原先個人與國家社會的身份想象是子與母的關系,如今卻要斷裂母子關系,抽身離開了所熟悉的時代社會,給具體的個人產生了巨大的時代痛感。
故事的結尾,是笑吟吟的尹雪艷站在歡醉場,依然說著那無關痛癢的話,仿若什么事也沒發生過。尹雪艷就如一個虛幻的存在,然而雖是虛幻,卻存在著——小心翼翼地為著每個人服務,滿足他們一顆追憶昔日上海的心。尹雪艷這個符號象征只有服務的功能,自己的其它一切都置身事外,也許對徐壯圖動過情,不然怎會親自來吊唁,動作嚴肅莊重;但也許沒有,不然怎會轉而又是一個笑語吟吟的尹雪艷。
有情無情間,盡是荒涼。也許這是一個舞女的歸宿,就如《游園驚夢》里的戲子,始終是要依靠人去捧的。正如人們附庸風雅、風雅,總歸要讓一群人去裝模做樣作秀一場,方才顯得高貴。兵荒馬亂時代,誰還能把風雅當回事呢?也許是尹雪艷看得太清晰。一顆心那么淡淡從容,不是憑白而來的,總歸是看透了某些東西的。于是,沒有選擇,也沒有聲音,任生命里來來往往,匆匆步伐抑或滯留,尹雪艷就這么淡淡地迎來送往,把自己的時間耗于別人的回憶——除此之外,還能有什么價值呢?生命走到最后總不免走入“寂空”之境,最可悲的卻也在于此,“寂空”之后,少了激動,也沒有追求。來來往往,盡是歡愉。笑語吟吟間,透過那氤氳的醉人迷霧,看到的是一群人,依然搖搖晃晃做著一個關于上海的浮華的夢,在自欺的短暫歡娛與麻木神經背后沉潛著無法言語的痛,看到的是一個小舞女湮沒在大時代突轉中的眼淚與傷痛。
參考文獻:
[1]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
[2]白先勇.白先勇文集[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
[3]張園園.永遠的象征——白先勇筆下的奇女子尹雪艷形象分析[J].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9,(10).
[4]朱美祿.斑斕的色彩 豐富的意蘊——白先勇小說《永遠的尹雪艷》色彩意象分析[J].名作欣賞,2007,(7).
[5]錢理群,溫儒敏.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6]金嵐.舊上海的影子——談王安憶《長恨歌》中的人物[J].安徽:銅陵學院學報,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