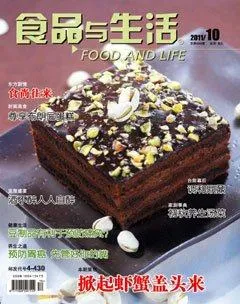“人類和海鮮的關系,將在2048年結束”。這是《海鮮的美味挽歌》一書強烈提出的警告。這絕對不是聳人聽聞,作者格雷斯哥是一位有良心的海鮮愛好者,他從加拿大的老家出發,走訪了北美、歐洲、亞洲的十多個國家。在深入調查海鮮供應的源頭之后,格雷斯哥震驚地指出,經歷了好幾個世代的努力吃喝,加上失控的污染現象、回避規范的捕魚行為以及日益嚴重的氣候變遷,人類捧為最佳營養食物的海洋資源,終究將枯竭殆盡。生態學家同意了他的觀點。
最初接觸到“海鮮”兩個字,是二十多年前我從上海移居香港后,滿街滿巷的海鮮餐館和餐廳門口大大的水族箱,看得我目瞪口呆。當時的上海別說活魚,連像樣點的死魚也是一年吃一次,過年的時候家家戶戶都會配給一條青魚。智慧的上海人一魚幾吃,炸的,熏的,炒的,溜的,狠狠地滿足了累積了一年的饞癆,足以存儲耐心再等待一年。
格雷斯哥在上海,居然還到過銅川路海鮮市場。我每次回上海,媽總要準備一些好吃的,海鮮必不可少。每次她都會自豪地說:“這是從銅川路買來的。”她認為銅川路的貨色才能和香港人喜歡的生猛海鮮搭上關系。
香港人很講究用詞,在海鮮前面冠上“生猛”兩字。海鮮身份的普遍,并不是海洋產品越來越富足的表現,而是人們看到了這種最低廉的蛋白質是可獲利巨大的商業用品的后果。記得當年洋夫帶我去舊金山一家據說是《阿甘正傳》生活原型開的專吃蝦的餐廳,里面還陳列著電影里的道具。還記得那艘拖網捕蝦船嗎?駕著它在墨西哥海灣捕蝦的場景,給傻傻的阿甘平添了幾分英氣。不過現在已沒有人這么做了,“藍色革命”(工業化水產養殖的別稱)之后,全世界的蝦產量有3/4是來自發展中國家。俗話說,眼不見為凈,可格雷斯哥偏偏去親眼目睹,還在書中記錄道:“事實就是,當今市面上所見到的廉價蝦子,幾乎全部來自貧窮的熱帶國家,養殖在水質混沌、病毒充斥,而且有灑滿了殺蟲劑和抗生素的池塘里”。
最近一次回香港,發現家附近最平凡的屋村街市(小菜場)居然有活的鯧魚才25港幣一條,而以前矜貴的石斑魚,居然也只有100港幣,隨時有交易,而且絕對是生猛。我是毫不猶豫地買的,因為我不會去追究它們的出生地,如果什么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那很快會餓死。所以當我在舊金山的朋友們冒險在被洶涌波濤圍繞的大礁石上釣石斑魚時,我想勸他們,不要以為沒有圈住的海域里的海鮮就是安全的。
看到這,大家不要悲觀,并不是原生態的海鮮已經滅絕。去年在香港小住,恰逢兒子從美國和他臺灣女友一起來港度假,到香港怎么能不吃生猛的海鮮呢?本著有良心地吃海鮮,不給海洋生態添麻煩的宗旨,我還真找到了青山綠水環抱中自然生長而成的海鮮,帶他們去享受了別開生面的海膽餐。
海膽是一種古老的海洋生物,與海星、海參一樣同屬棘皮動物,全身長滿尖而長的刺,每根刺的基部有活動的關節。它的身體呈圓球狀,有堅硬的外骨骼,再加上根根長刺都可用于行走,所以它走起路來像一只刺猬,還有一個愛稱叫 “海底刺猬”。
那天我們從香港著名的西貢碼頭坐上小船,航行了差不多45分鐘,來到了糧船灣的海膽養殖場,這個養殖場并不批發出售海膽,而是自辦餐館,現捕現燒地招呼海鮮愛好者。
糧船灣相傳古時是官兵存糧的海灣,故得名。灣內是漁業養殖區及全港唯一的海膽養殖場。聽老板娘說,他們是原居民,看到這兒細沙清水的,就決定以休閑的方式來養殖海膽。老板親自在附近水域潛泳,找到海膽幼苗,就將它帶到糧船灣的水域,它吃海藻長大,天生天養,所以每年有一半的時間養殖場關閉,等待海膽長大。這種雌雄同體的動物,從受精到產卵,自己可以在體內一手操辦,完全不假于人手。
糧船灣那里的水質特清,餐廳就在碼頭旁,一眼可以看到伏在海底的海膽,所以捕撈捕捉根本就不是問題。海膽是營養極其豐富的海珍品之一,含有大量的蛋氨酸和不飽和脂肪酸;用其性腺為原料加工而成的鮮海膽黃、海膽醬不僅味道非常鮮美,還可美容;其殼入中藥可醫治頸淋巴結、積痰不化、胸肋脹痛、胃及腸道潰瘍、甲溝炎等癥,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
雖然海膽長滿長刺的外殼很唬人,好像無從下手,但拿上手并不覺得扎手。餐廳的女工在水龍頭下,用剪刀輕巧地將殼剪開后,除了5條布滿卵子的生殖腺,其他都是空空如也,無骨無筋。我們用小調羹把淺黃色海膽肉身放入嘴里,可以蘸醬油和芥末,但我選擇純口味。說實話,送入嘴的那瞬間,有點不忍,因為很美,美麗的五星,可惜這個念頭很快被人類的貪婪壓抑了,口感不錯,有點腥,但敵不過滿嘴的鮮味。之后我們又吃了海膽蒸蛋,還有紫蘇炸海膽、海膽炒飯,加上其他海鮮酒水,兒子買單剛過千,年輕人連連說劃算。
好東西要大家分享,不過現在應該說,好東西要和好人分享,因為碰到那些以自己利益為重,忽略生態,或是利用生態牟取暴利的人,很快,糧船灣的海膽也會搬去那些人為它們準備的蝸居,嗚呼過日。所以請讀此文的好人,無需聲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