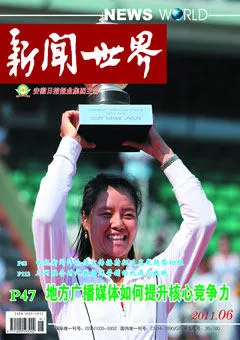中日災難報道的差異
【摘要】在3月11日本特大地震發生后,日本媒體的表現得到了世界的贊許與肯定。在這一類災難新聞中,對比國內的媒體報道,日本媒體在報道的采訪、內容、導向性上有著許多值得國內媒體學習的地方,中國的媒體在對于特大自然災害的報道中需要對自己報道的標準、方法進行不斷改進。
【關鍵詞】災難事件 中日媒體 新聞報道
近年來,世界各地頻發地震等自然災害。中國媒體在這類事件的報道上投入的力度也越來越大。但縱觀這幾年的災難報道,中國媒體由于缺乏經驗,在報道的方法上還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與中國相鄰的日本是一個自然災難頻發的國家,在災難新聞的報道上有著許多可供我們借鑒的經驗。對比中國的汶川地震和日本最近發生的“3·11”特大地震的新聞報道,可以發現中國媒體對災難事件的報道有得得改進的地方。
一、中日媒體在災難事件采訪上的差別
首先,在對比地震中采訪對象的選擇上,中國的媒體比較喜歡采訪地震中的受災群眾,希望能夠從他們的口中獲得關于地震發生時的情況以及他們現在的情況。從專業的角度來看,這些受難群眾是地震災難的當事人,在他們身上必定具有許多有價值的新聞,但為了盡快獲得這些新聞,中國的一些記者在對于采訪時機的把握上通常顯得不夠慎重。在汶川地震中我們可以見到像這樣的情況:被埋者在廢墟中奄奄一息,記者卻要求暫停營救,先行采訪,并阻止救援人員搬開懸掛在被埋者上方搖搖欲墜的天花板;在地震災區臨時醫院里,醫生正準備給傷員動手術,記者在沒有消毒的情況下強行進入并要求采訪,導致醫療設備被污染,類似的情況并不是個案,在一些極端案例中,由于媒體的不當采訪,間接導致了被采訪者的死亡。
與之相對應的日本媒體,在“3·11”大地震中,日本媒體也會將采訪的鏡頭對準災民,但在采訪的時機上,普遍遵循了不得干擾救援工作進行的原則。對于在廢墟下進行的救援過程,日本媒體也會采取直播,但在其過程中,不會采訪任何救援隊員,因為擔心影響救援進度,也不采訪受害者家屬,因為此時他們已痛苦萬分,日本媒體認為任何強行采訪在此時都只會給家屬徒增傷痛。瀏覽日本關于地震的新聞,可以發現那些對驚魂未定的災民進行采訪的新聞很少,電視臺的記者一般安靜地拍下他們和生還的親人、朋友擁抱或者沉默的情景。在采訪時機的選擇上,除了不干擾地震救援人員的工作之外,日本的媒體也非常注意災民的心理情緒是否適合接受采訪,避免由于自己的采訪對其心理造成二次傷害。
除了選擇采訪對象與采訪時機之外,記者在采訪中的提問方式也表現出其職業素養。在汶川地震中,中國的一些媒體為了獲取信息或在報道中突出某種目的,常常對采訪對象采取“侵擾悲痛”式的采訪,這種采訪如果方式不當,就會對被訪對象造成很大傷害,某電視臺對女警蔣敏的采訪就屬于這一例子。
而日本媒體在面對這種可能會“侵擾悲痛”的采訪時則表現出來了更多的人文關懷,提問的內容通常也只是點到即止,絕對不會對受災群眾進行任何的追問。例如,一名主持人在采訪一位災民時,問到他“你的家人找到了嗎?”當得到沒有的答案時,主持人安慰他“請加油。”①短短的幾句話中,已經傳遞出了很多的內容,而主持人此時并沒有再繼續追問他更多的關于其家人的情況。這種采訪雖然比較短,但并不煽情、也不會侵害到被采訪者的個人情感和尊嚴。總結日本媒體在地震災難中的采訪,其角度和語氣都顯得比較平和,話語中充滿了人情味,采訪的過程就是對災民的一次安慰。
二、新聞圖片的搜集、新聞素材的選取上的差別
中國媒體所選用的新聞圖片通常喜歡將鏡頭對準受傷的災民甚至是遇難者,一些報紙還將這種照片作為頭版新聞圖片來使用,為的是突出新聞圖片的視覺沖擊力和影響力,但有可能會對遇難者的心理造成傷害,并有可能會令讀者感到不適。這種對傷者、遇難者進行直接拍攝的新聞照片和電視畫面在報道中較為常見。
與此相對應的是,在“3·11”地震中,日本媒體所選取圖片看不到遇難者,甚至是災民的痛哭、昏厥也未出現過,目前可以看到的關于日本地震中遇難者的照片基本都是來源于國外的媒體。日本媒體在災難影像的選取中普遍奉行“尊重生命”的原則②,除了在新聞圖片的選取上要求避免出現遇難者和災民的出現,電視媒體在對受災者進行采訪的時候,也很少拍攝他們的面孔,很多受訪兒童一般只露出背影或鞋子。
三、報道時所體現的價值觀和導向性的差別
日本在災難報道方面所奉行的是“安心報道”的原則。在報道重點上側重傳遞出目前最重要的信息,并力求準確、全面、迅速,有關消息一經確認,就立即反復輪流播放。NHK電視臺當獲悉福島縣第一核電站第1號機有可能爆炸后,馬上中斷正在直播的對官房長官的采訪,轉而反復播放核輻射時的生活指導及相關避難信息,每隔幾分鐘就提醒民眾注意安全,日本各大媒體在第一時間把輻射量每小時1015微西韋特的準確數據傳播出來,并告知“這相當于普通人一年可以承受的輻射量”③,報道在細節上顯得認真、詳盡,使受眾能迅速理解這些信息。另外,在報道時,日本媒體考慮到可能有不會日語的外國人身處受輻射污染的區域,在報道中使用了英語、漢語、韓語等語言來進行報道;在報道災難時保持克制、冷靜。雖然偶爾也會發現主播和前方記者的聲音略有些顫抖,但他們始終保持著鎮靜、堅強的面容,加上報道的畫面中沒有出現恐慌、失控的畫面,穩定了觀眾的情緒。及時透明的信息、冷靜沉穩的播出風格,使得日本媒體在災后能夠迅速穩定人心。
反觀在中國在汶川地震的報道中,我們報道的重點顯得不夠明確,一些信息傳遞上也顯得不夠及時,這些情況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例如成都市關于自來水污染的傳聞就引起巨大的恐慌,這一方面是由于信息公開不及時所造成的,另一個方面也是由于前期的新聞報道所普遍傳遞出來的災難恐慌情緒導致了市民們內心的不安定。
此外,媒體報道的導向并不僅表現在對災情的最新情況的報道上,也表現在對政府的監督上。日本“3·11”地震造成了福島核電站的泄露,日本在及時報道災情的同時,也對政府進行了批評和監督,對政府在核泄漏事故中監管不力、隱瞞信息等方面進行了批評,這種批評甚至達到了一種逼問的地步。東海大學華人教授葉千榮在微博上面記錄了東京電力公司副社長藤本孝等六名干部鞠躬謝罪的場景:
記者厲聲逼問:“三號機組會不會堆心融解?!”藤本回答:“目前尚不清楚。”記者吼道:“把話說清楚了!到底會不會!別含混言辭!”他不得不答:“情況是嚴峻的。”④
中國在災難事件中很少出現輿論監督報道,有人還質疑輿論監督多了,會不會對災難的搶救工作和團結穩定的救災情緒造成影響。其實只要把握好監督性報道的度和方法,監督性的報道與救災性報道是并不矛盾的。
其實中國媒體在災難報道中表現出來的不足,正是中國媒體缺乏經驗的表現。縱觀歷史,日本在災難報道中的做法和所呈現出來的報道理念也并不是與生俱來的,這些做法與觀念也是通過長期的報道實踐所總結出來的。例如,日本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報道中,媒體在影像中曾大量使用航拍扭曲斷裂的高速公路,成為火海居民區等具有沖擊力的畫面,這樣的做法反而導致了許多關于災難的基本信息和大量的救災場景被忽略,日本媒體也因為這種報道曾遭到日本國民的批評。此后日本媒體在類似的新聞報道中吸取了教訓,以更加專業、人文的理念對待各種災難事件。對于日本媒體這些在災難報道中總結出來的經驗,中國媒體需要進行學習,并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報道方式進行改進。
首先,在采訪的過程上,媒體要注重其活動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不能在采訪中表現得過于功利,不能因為自己的新聞工作而破壞現場的正常救援。對于災區中的群眾在采訪時要盡量注意其心理狀態,避免對其造成“二次傷害”。
其次,在報道的過程中,適當篩選采訪中所獲得的材料,引導讀者在災難事件中的視線。災難中的一些震撼性場面會使受眾產生出“感覺后象”。即當刺激物對感官的作用停止后,人們對刺激的感覺并沒有立即停止,而是繼續維持一段很短的時間。因此,媒體在報道大災難的時候,不能盲目地追求轟動效應,避免因一味地追求震撼性場面而對受眾造成刺激;對于災難現場的死傷情況最好是概述而不宜描寫;文字表現應以不令讀者驚懼、反感,以大多數讀者可以接受為限;避免在內容上出現血腥和暴力的新聞素材和圖片。
最后,報道時盡量莊重、嚴肅,以正確地引導觀眾的感情。在報道的全程中顯示出冷靜、理智的態度。這不僅是對災難中的個體的尊重,也是媒體對受眾負起社會責任的重要表現。■
參考文獻
①舍人,《激震中的日本:即使傷痕很深 也要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