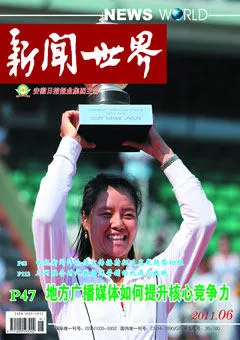《晨報》副刊與思想文化公共領域的建構
【摘要】在中國近現代史中,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利用報刊表達自己的思想,報刊成為他們參與公共生活的媒介,也成為公共意見形成的主要陣地。本文選擇李大釗主編時期的《晨報》副刊來分析在新文化背景下,現代知識分子是如何利用報刊來構建屬于自己的思想文化公共領域。
【關鍵詞】知識分子 思想文化公共領域 李大釗 《晨報》副刊
一、公共領域與報刊
公共領域的形成與大眾傳媒有著密切的關系。對公共領域的研究起源于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結構轉型》。①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是指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領域,某種接近于公眾輿論的東西能夠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開放這一點得到了保障。當公民以不受限制的方式進行協商時,他們作為一個公共團體行事,對于涉及公眾利益的事務有聚會、結社的自由和發表意見的自由。在一個大型公共團體中,這種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來傳遞信息并影響信息接收者。今天,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就是公共領域的媒介。②無疑,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肯定了大眾傳媒對公共領域的建構作用,他認為,“新聞媒介是社會之公器,是全體公民窺視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共同管道和從事公共事務討論的公共論壇,在現代國家的公共領域中具有頭等的重要地位。”③
報刊作為早期的重要媒介,對公共領域的建構發揮著重要作用。報刊公共領域指借助報刊媒介得以形成公共意見的公共領域形式。④傳播信息、啟迪民智是報刊的主要功能,面對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基于報刊的功能,紛紛辦報,表達自己的思想,報刊成為他們參與公共生活的媒介,也成為公共意見形成的主要陣地。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是介于私人領域和公共權威之間的一個一種非官方的領域。它是各種公眾聚會場所的總和,公眾在這一領域對公共政策和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做出評判。⑤知識分子辦報所形成的報刊公共領域,實際上是對公共問題的批判或進行引導或者注入知識的元素,使公共問題的討論趨于理性或者使其朝著自己的意愿進行探討。
二、李大釗編輯時期的《晨報》副刊
中華民國成立后,中國并沒有按照革命者的理想發展,現實的國情,致使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寄希望報刊來推動社會的變革,于是辦報成了他們宣傳新思想的主要手段,《晨報》副刊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
《晨報》副刊于1918年底由湯化龍、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團體創辦。1919年旨在推動社會進步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后,介紹和傳播新思想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傳播的重要內容。《晨報》副刊繼承和順應了這種新時代潮流,始終保持了對新思潮的高度關注。
1919年2月7日至1920年6月,李大釗擔任《晨報》副刊的主編,對《晨報》副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晨報》副刊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得到了改變,副刊的地位也得到了明顯的提高。李大釗主編時期的《晨報》副刊是由一份舊式副刊向新式副刊轉變的重要階段,新思想成為其傳播內容的核心,同時,外來學說和思想的翻譯在《晨報》副刊的傳播下得到了推廣。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晨報》副刊對西方社會運動方面的學說、尤其對馬克思主義學說和俄國革命等方面內容的介紹特別熱忱。而這些與李大釗密不可分。李大釗作為受中西方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感于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⑥在注重“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的同時,更看重借助報刊這種傳播媒介探索中華民族的發展之路。
三、《晨報》副刊與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文化公共領域的構建
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的出現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公共領域必須具有公共性,即超黨派,是在政治權力之外建構的平等的討論空間;二是參與者必須能運用自己的理性獨立表達自己意愿,并廣泛參與公共事務;三是公眾所討論的是公共政治問題。⑦這些條件分別從場所、參與者、問題對公共領域的形成進行了界定。筆者在對李大釗編輯時期的《晨報》副刊進行分析得出,《晨報》副刊在構建知識分子思想文化“公共領域”的過程中,具備了哈貝馬斯所提出的三個條件。
1、公共性
哈貝馬斯認為公共性是在公共領域中每次論辯實踐的交往前提都在于參與者消除和超越黨派偏見與自身的特權。⑧這兩個前提必須得到實現,這甚至應當成為辯論的成規。這說明公共領域的公共性具有雙層內涵。首先,它是獨立于政治權力之外,超黨派的;其次,它所建構的是平等的討論空間。⑨而我國的近代報刊在面對憂患中的現實國情,代表先進文化的知識分子,希望借助辦報“立言”來改變現狀,報刊不僅是其獨立于政治權力表達自我的一種渠道,更是知識分子聚集在一起探討問題的場所,報刊實際上充當著代表知識分子發表言論的新話語空間。學者李歐梵曾認為,晚清(也可能更早)以來,知識分子利用報紙媒介,開創了各種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評的“公共空間”。在他看來,晚清以后的報業與原來的官方報紙(如《邸報》)不同,其基本的差異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場消息的傳達工具,而漸漸演變成一種官場之外的“社會”聲音。⑩
李大釗擔任《晨報》副刊主編期間,對《晨報》副刊進行了大范圍的改革,《晨報》副刊不僅經歷了從舊式副刊到新式副刊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其在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逐漸成為了一個傳播新思想的舞臺。報紙版面上其設置了“名著新譯”、“馬克思論壇”、“自由論壇”、“世界新潮”等內容,超越政治權力的先進思想得到了充分傳播的平臺,知識分子可以比較自由地在其中發表他們對各領域的想法,《晨報》副刊在李大釗主編期間面貌的煥然一新,實際上構建了一個平等的獨立于政治權力之外的討論空間。
盡管現實的政治時常破壞著當時自由的風氣,對知識分子思想文化“公共領域”的構建造成威脅,但是當時李大釗等知識分子還是堅持用報刊來爭取表達的權利,堅持《晨報》副刊的獨立性和公共性。1920年,胡適、蔣夢麟、陶履恭、張祖訓、李大釗、高一涵在《晨報》副刊上聯名發表了《爭自由的宣言》。他們在宣言中說到:“我們本不愿意談實際政治,但是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礙我們。自辛亥革命到現在,已經有九個年頭,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經歷了種種不自由的痛苦仍同從前一樣。政治逼迫我們到這樣無路可走的時候,我們便不得不起一種徹底覺悟,認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發動,終不會有真共和實現。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發動,不得不先有養成國人自由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的空氣。”⑾政治權力的腐敗和現實國情的憂患,在一定程度上使知識分子難以脫逃現實去辦報,而這種反思反過來又會促進報刊作為一種“公共空間”傳播新思潮和討論中國的前途。
2、知識分子的理性參與
李大釗個人的經歷以及其作為最早關注俄國十月革命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識分子,其主編時期的《晨報》副刊相比較孫伏園和徐志摩主編時期,對思想性的傳播尤為關注。“啟蒙”是當時《晨報》副刊的核心內容,胡適曾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啟蒙精神,作出了這樣的闡釋,即是一種“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⑿《晨報》副刊在李大釗主編時期的啟蒙批判的就是當時社會的舊風氣和舊思想。
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報紙副刊都是以消閑娛樂為主要基調。新文化運動改變了這種局面,副刊也得以轉變成為宣傳新思想的重要舞臺,《晨報》副刊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李大釗認為,中國思想界太沉悶,死氣沉沉的原因“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總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⒀李大釗想利用《晨報》副刊這一輿論武器,建立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思想文化的公共領域,來營造一個公正、理性、自由的言論氛圍,在這一領域中,知識分子的各種思想和言論可以自由發表,靠理性來評判是非真偽。
3、關注的問題
李大釗主編《晨報》副刊期間比較注重思想性,盡管這一時期的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及俄國“十月革命”的理解尚處于起步階段,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中國民族自身的災難中,他意識到現代文明的罪惡。雖然李大釗這時還沒有系統理性地接受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深入研讀馬克思主義的原始文獻,但他以超人的敏感性意識到馬克思主義代表了歷史進步的方向,并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實踐中,領略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偉力了。⒁這些后來都直接反映到他所主編的《晨報》副刊上。這一時期,《晨報》副刊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翻譯介紹占據了不小的比重,《晨報》副刊專門設置了“馬克思研究”專欄,輸入馬克思的主要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不僅在其的宣傳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同時結合中國現實問題的思考也成為其致力的重要內容,馬克思主義借助《晨報》副刊這一輿論平臺在中國的傳播不再是一個硬搬生套的理論,更多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結合現狀探討的理論。
同時,《晨報》副刊還關注西方近現代自由主義民主思想,對國外社會主義動態的介紹,對“科學”的介紹等,雖然《晨報》副刊的版面空間小,但它容納的內容卻是多元化的,對改造中國社會,宣傳新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①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91
②展江,《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與傳媒》,《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2(2)
③羅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