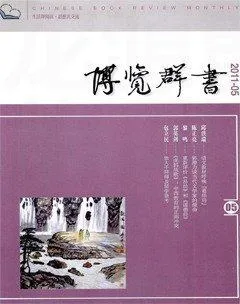郭潛力談當代文學家的使命
經歷
問:你是怎么走上文學之路的?何時開始從事小說創作?當時是什么讓你有了用小說表達的沖動?
郭潛力:這世界最有趣的是,不在于你選擇了什么,而是什么選擇了你。我的創作之路多少有些類似。1989年,我受內地一家單位委派,去當時剛成立的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搞企業。那時候的海南島真可謂風云際會。正當我們掙脫內地的繁文縟節,滿懷豪情想干出一番大事業來時,波詭云譎的形勢變化讓敏感的特區歸于沉寂。可很快,形勢又逆轉,導致比上一輪的開發更加瘋狂。渴望財富的人們時不我待,貪婪無度導致了另一輪的調控。近十年的爛尾樓在特區的土地上像經歷了一場殘酷的大戰,觸目驚心。我們就是在這種過山車般的變化中,瓦解了曾經寄托一幫年輕人美好愿望的企業,各奔東西。有的人回到了內地,有的人自此脫離了公職身份,義無反顧地奔吸金的地方而去。我膽小,回內地又不甘心,裸身下海又畏首畏尾,于是,將組織關系調入了當地一家單位。說件好笑的事,當時原單位領導在我多次懇求下,決定以一場乒乓球比賽的勝負來裁定我的去留。我們當時甚至都不知道對方是否會打球,一幫見證人聳立一旁,領導顯得十分嚴肅。我去意堅決,絲毫不敢怠慢,平生打了一場既不敢過分又得守住底線因而極度口干舌燥的球賽。三比二,贏了,我得以繼續以公職的身份在椰風海韻中混了下來。正因為這段闖海的經歷和茍延殘喘的時間,我寫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海口干杯》,也算走上文學之路了吧。反正以后一發不可收拾,《城市狩獵》、《我的年代》等,一百來萬字,如數出爐。
需要強調的是,我始終是業余的。盡管這樣,文學的確是我心底的烙印。我一直認為,文學是人類心靈的映照,一個有足夠閱歷、時刻感懷的人,他的內心世界一定是精彩紛呈的。只要他能專注,能進入,那種宗教般的博大、彌撒般的禪想,作為精神的舒張很自然會流淌出來,當然,稱之為“宣泄”也不為過。但我認為,文學應該是高山潺潺的流水,春天無聲的細雨,苦澀咖啡后的回味。有時候我常為“什么是美”而犯愁,過去古人審美是“櫻桃小口”,可如今嘴大了才性感;過去是笑不露齒,如今最好能露出槽牙。如果說“這人長得很文學”,語境的闊大也許會讓所有人噤聲。總之,文學是人類慰藉的天平,自贖的良方,審美的暢想。它與物質發不發達無關,精神的寫意才是人類終極的命題。正因為我對精神的感受追求得更多一些,創作便成了一種自覺。但如何讓這種自覺成為所謂文學,還需更多的磨礪。
我常說我們這一代人挺幸福,我們只用了短短30年的時間就感受了西方七八代人才完成的200多年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的文明進程。什么叫翻天覆地?美國大片里的時光隧道活靈活現地展現眼前,就沖這咱們也算沒枉活過一回。唯一遺憾的是,這有可能被扣上“暴發戶”的罪名。最最遺憾的是這只是財富的暴發戶,而不是文化意義上的暴發戶。我多么希望是第二種暴發戶啊!但文化需要沉淀。否則厚重從何而來?它不可能像財富那樣輕浮地一蹴而就。所以,文學只與時間、寂寞有關。當然,你可以說它還與感情有關,與憤怒有關,但真正的文學它必須出離。否則,至少它難以成為經典。
問:批評家洪治綱說你有“獨特的家庭背景,頻繁漂泊的成長經歷”,能否介紹一下?
郭潛力:其實也沒什么,只是我們生長在一個比較特殊的歷史時期。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自然與“文革”結下不解之緣。那是一個激情四射又令人無比彷徨的年代。我父母都是軍人,軍人在那個動亂的年代,注定要承載更多的使命,“文革”時代同時也是北有蘇修南有美蔣亡我之心不死的年代。作為軍人家庭的孩子,自然要隨父母馬不停蹄地東奔西走。
我至今記憶猶新,小時候常躥進營房,與戰士們一道臨時抱佛腳學實用俄語:斯舵依(站住)、盧基·維勒赫(舉起手來)、斯大基·阿盧日耶(繳槍不殺)。好像這仗明天就要開打了,興奮得腦海里全是英雄人物,要么寧死不屈,要么堵槍眼,要么手舉炸藥包,濃濃的革命英雄主義豪情燥熱得不行。興奮啊!所以,父母們往哪走——不論城市、山溝、沙漠、草原——我們都樂意相隨。當然也有被當作累贅“留守”在部隊大院的時候,過著沒有大人管束的生活,這讓我們有了如魚得水的搗蛋機會。正因為如此,我們較之一般地方孩子有了軍地兩面性。就地方生活,我們也不是象牙塔,因為父輩們也“三支兩軍”也大三線建設,也像在部隊時一樣,頻繁換防,所以我們也沒少穿山打洞無孔不入。我至今留戀的地方生活就是湖南湘西那一段,風景風俗和沒被“文革”全面污染的樸素邊民。我在長篇小說《城市狩獵》的作者簡介里這樣介紹過自己:
因為父母均為軍人,大江南北,三四年一個“稍息”后的輾轉,又猛然“立正”去面對一個全新的環境,自小就與“客居”二字結下了不解之緣,時至今日,仍無強烈的“老鄉”感,也不能被生長之地的人所認同,頗有幾分像“邊緣人”。
問:可以具體談談這些經歷對你的文學創作有什么影響嗎?
郭潛力: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雖然受了高等教育,但我不敢說自己讀了多少書,但走了萬里路還是有點譜的,也算有一定見識吧。“文革”,說到底,它是一場文化意義上對傳統的顛覆。不管統治者意欲何為,它客觀上造成了一場民族文化的大浩劫。西方有文藝復興,我們是文化革命,兩者結果大相徑庭。我們這批60年代出生的人,實際上就是在摧毀的文化中混沌入世的,好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很快來臨,不至于讓我們越陷越深,有機會喚醒我們浸淫在血液中的文化傳統。經歷了大事件的人,是難以寂寞的,總有一種要去表達的沖動。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有過幾次全民反思,這讓文學成了寵兒,“文學青年”成了高尚的字眼。多少人徹夜疾書,夢想成為作家、詩人。
如何面對過去、幻想未來?文學似乎成了一個載體。其實,就我的創作而言,更多的是,將一段截面、截圖當作一種鏡像,讓不同心境的人能有趣、能觀照、能從中感悟。30年的變化,對財富來說也許可以速生速成,但對文化來說,還需要更多更深的沉淀。一個有5000年文明的民族,這30年的縮影甚至連滄海一滴都算不上,當然也不至于“神馬都是浮云”那么淺薄。我想得更多的是歷史不要輪回,哪怕是那些曾經無比輝煌過的歷史,精神崇高比什么都重要。
時代
問:中篇小說集《我的年代》是你少年時代的記憶,也可以說是你的心理傳記。耐人尋味的是,你對“文革”有自己深刻的認識,卻還是通過少年的視角來反映它。阿廖說:你既不是出于祭奠,也不是再現,更不是反思;你說是回顧與尋找。你在尋找什么呢?其中的隱喻又是什么?
郭潛力:孩童的眼睛清澈無瑕,是人類最早的純樸所在。所以,選擇孩童視角,更能產生強烈的投射,同時,也更有趣,不至于讓人把神經繃得太緊。比如這個中篇集子里的《朵朵木》,我特別想說明一下,“朵朵木”是江南某城市對“傻瓜”、“果子”的方言表述,說這人傻,就是“朵木”,說這人很傻,就是“朵朵木”了,也就是“傻到家了”的意思。朵朵木有個習慣,他喜歡倒立,當然,起先他是“被”倒立,后來他發現倒立能給他帶來很多樂趣。當一個師道尊嚴的老師在那正襟危坐口若懸河時,他卻從倒立中看見了女老師裙裝的F半身,甚至還有私處。上下對比,霎時讓朵朵木看到了事物的兩面性。從此他倒立得愈發起勁,行為也愈發乖張。“朵朵木”自然也被人叫得更加嘹亮。還有《豹子灣》、《逃》以及《今夜去裸奔》,這些故事通過善與惡、貧與富、虛榮與勇氣的對比,張揚合乎道德的行為,顯示人性固有的力量和弱點。所以,如果一定說我在尋找什么,那應該就是這些了。換句話說,正是通過這種文學創作,去實踐著一個理想和追求。
問:作為60年代人,你如何認識這一代人的特點、優劣?
郭潛力:一言難盡。就我個人經歷,頗有小跟班的意味。就像紅小兵追著紅衛兵跑,那桿理想主義大旗只是湊熱鬧和好玩的標志。不是有一種說法叫“紅旗下的蛋”嗎?對于一個小學生而言,那是陽光燦爛的日子,無拘無束,更不可能與政治發生直接沖突。可要說完全是一個旁觀者也不全面,畢竟童年少年是最長記憶的年齡,浸淫在那樣一個全民喧囂的環境中不可能不怦然心動,只是年少無法化作行動。所以有人說“有記憶無經歷,有思想無行動”是60年代人的一個顯著特征。他們無法像上代人對理想執著較真,也無法像下代人那樣身輕如燕,敢想敢干也敢不負責任,因為從來不需要想起,時刻也不會忘記的那段歷史成了他們身體的一部分。尷尬中常被邊緣,邊緣后又于心不甘。總之,他們負重前行。而這負重并不是外力所致,更多的是一段人生臆念的陰影在閱歷中的放大。邊緣其實是一個很傷感的詞——邊疆、邊城、邊陲、邊塞,“邊”出了一幅畫外的蒼涼。具象的表達有些像一腳里一腳外,里外不是人。文學的表達就是長亭外古道邊了。這些其實說的都是一種心境。所以,邊緣也隱含距離,距離產生的美有天涯咫尺的情愫。邊緣也是交叉,就像人有交感神經,主導著我們愉悅的中樞。60年代出生的人邊緣處世,大概很難堅定,搞創作較為合適。
問:你對當代文學,特別是網絡文學有什么看法?
郭潛力:我感覺,當代文學太當代了,當代得有些不假思索就奮筆疾書。我現在就怕逛書店,每年成百上千的新書摞在那里,大多只是當代文字,這情景足以讓許多純文學作家喪失再創作的勇氣。人們覺得房價高,于是《蝸居》了;腐敗叫人痛恨,于是《駐京辦》、《市委書記》了,人們當下關注什么就有什么。早年留學熱,就有《北京人在紐約》、《上海人在東京》。很多出書人滿足的是迎合,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層次,很難看到作者內心的真誠。而最深層次的世俗關懷、抵達人性之根的純文學作品,卻讓如今習慣快節奏的讀者難以卒讀。難道我們民族的文化修養只是滿足于紀實與獵奇嗎?現在有些批評家指責純文學故作姿態、媚雅,但他所指責的那些不正是我們這個社會所迫切需要提升的東西嗎?
由此對那些以速度表現在寫作、閱讀及反饋上的網絡文學,是否真能像有些人預測的那樣改變國界,改變人類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我持保留態度。我的小說《今夜去裸奔》在《十月》發表后,很快我就發現有一篇自稱根據《今夜去裸奔》改寫的《開著寶馬去裸奔》掛在了網上,作者和書中的人物名字全部保留,故事也基本雷同,只是多出許多亂七八糟莫名其妙的東西,充斥著小資情調、風花雪月,那些跟帖、灌水更是將作品肢解得支離破碎,看得我目瞪口呆!網絡文學顯然是給那些找樂子和游戲的人準備的。
盡管我早已用電腦寫作,但我更看重投稿出書。發表一部作品,經過編輯、一審、二審、終審,一校、二校、三校,發表出來有種神圣的感覺,至少不會錯字連篇語法混亂,有這么多人把關,對得起“文學是精神產品”的稱號。不過,我也不抵觸網絡文學,如果有一天寫手們能不狹隘地宣泄,快樂地墮落,更重要的不濫用自由表達的權力,也許吧,只是網絡太過便捷,人們何苦再去勞神咬文嚼字、文心雕龍呢。碼出一堆文字,呼啦啦沒有任何障礙地發泄出去,坐等速度飛快的回帖“我頂”、“頂你個肺”。我相信,這樣的網絡寫手是不會被自己的文字所打動的,那種為自己杜鵑啼血出來的人物命運所感動而痛哭流涕,渾身顫抖,食不甘味的體驗,他們很難體會。連抄襲在粉絲眼里都不再是恥辱,那我們還如何能相信“文學”呢?
問:我看過一些網絡小說,全是對話的鋪陳。沒有社會大背景,人物性格、情節設置缺乏邏輯性。也許,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那文學的使命何在?你現在的工作,能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這都是極好的素材。作品不僅要反映時代,更要反映被時代沉淀下來的東西并能夠流傳下去,作品自然也便成了經典。希望你能寫出這樣的作品來。
郭潛力:文學應該是劃時代的,因為世俗關懷,人性之根是永恒的。網絡文學是信息時代的產物,它所依靠的是一種新技術,所以,它的意義更多的是表現在技術的層面,而難具有哲學和文化的內涵,至少目前是這樣。有人將網絡文學比作原生態,較之純文學而言,它直接率真,不矯情。如果原生態是這樣一種理解,那我們人類盡可以重新回到樹上去了。
至于文學的使命,探討這樣的問題會不會招人拍磚?過去我們走了一段彎路,過分強調文學的政治意義,屏蔽了文學本來的面目,導致全民起膩,反理性、反崇高、反英雄一度成了詩歌的主旋律。后來與之對應的反思文學、尋根文學蓬勃起來,只是“以‘世界文學’的視鏡從中國文化尋找有生命力的東西”還來不及縱深挺進,社會便被商業大潮所吞噬,網絡文學的興起,多少也加重了文學不再沉重的落寞。毫不諱言地說,文學的使命就是那種建立在與宇宙,與大自然靈感溝通后的探尋生命終極的過程,是實踐著的理想和追求。也就是說真正和宇宙,和大自然有靈感溝通的,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創作。這樣出來的作品,才可能成為經典,才可能流傳下去。
城市
問:《海口干杯》、《城市狩獵》和《今夜去裸奔》都是反映城市現實生活的。評論家們或名之為典型的“城市書寫”。或稱其內核是作為城市主體的人的精神世界,是對變革時代的人的精神生活的記錄和抒寫。如《海口干杯》在90年代的城市文學浪潮中引起廣泛的關注,被稱為“特區文學的一支新秀”;何振邦稱《城市狩獵》是“新都市文學”的一個重要的新的收獲;李潔非說,這兩部城市小說“顯示了作家城市意識的深化”。從個人英雄歷史主義的理想空間轉到了復雜性。而到了《今夜去裸奔》,則是關注成功人士的生存問題,揭示出城市生活的殘酷性。你對這些評論怎么看?你對現實城市生活是如何理解的?
郭潛力:《海口干杯》嚴格意義上說是一部浪漫主義的作品,從舊體制下掙脫出來,身心沐浴在自由的空氣之下,在物質基礎幾乎空白的一張白紙上,人們精神自由馳騁,縱橫開闊。你想,從閉塞走到洞開,那是一種什么感覺?一句話,充滿了新鮮與激情,也就是改變命運的英雄主義的吟唱。可很快,市場經濟的貪婪剝開了美麗的外表,悲劇的一面呈現出來。《城市狩獵》大抵就是這一復雜性的寫照。《今夜去裸奔》表現的是城市人精神層面的探索,是有一定物質基礎之后的上層建筑。如果我們還像過去那樣面對光怪陸離的世界都以“游戲規則”來搪塞或回避,那我們是不會健康前行的,就像金融危機給人類帶來的發展觀和經濟運行結構的深刻反思。在去年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上,有人疾呼:市場經濟太罪惡了。資本主義的貪婪,少數金融寡頭窮兇極惡地賺錢,讓全世界為之付出代價。終于世界提出了重新反思。反思市場經濟所管控不到的地方,反思人類是否要永無遏制地貪婪地開發地球資源,人類的發展觀需要重新認識、重新設計、重新架構。城市作為人類文明演進歷程中的凝結,其發展的終極目標,是讓生活在城市的人們更滿足、更舒適、更有尊嚴、更有幸福感,單獨偏重某一領域是與精神和物質一起構成的和諧相抵觸的。
問:有評論認為,你筆下的人物在追求世俗的成功的同時,不放棄個人理想,要追尋精神的解釋。從而,你的文學認識和敘事傳達達到了新的深度。《今夜去裸奔》以一種隱喻的方式,頗具荒誕感地敘寫現代生活的精神圖景,現代人的精神奔突。洪治綱說,它是現代人心靈焦慮的二個精神范本,它也是現代人尋求精神救贖的一個精神范本。你把財富當作基礎,精神追求的東西更多一些。作為作家,你的追求是什么?
郭潛力:我覺得有一個詞特別好——流連。匆匆的腳步如何能讓美定格在你的腦海里,沉淀在你的血液中?這個社會發展得太快,人們實際上并沒有做好應付這種快節奏的精神準備。《今夜去裸奔》的主人公從標志身份的起名開始,就已身不由己進入一種迷失的漩渦狀態。80年代,父母望子成龍給他取了“李大為”,指望他大有作為。后來獨生子女了,父母又給他改名叫“李葆存”,最低要求,平平安安存在就行。大學畢業后父母又雄心勃發恢復了他的本名。成為職業經理人后,他又被MBA老師借鑒一些歌手改名成功走紅的范例,被改名為“韋瑞”,隱含偉大人瑞的意思。他到外企工作后又有了附庸風雅的英文名“拜瑞”。他自己都經常犯糊涂。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斷了線的風箏,迷失在認同里。而他身邊的同事也莫不如此。對手段敘叫哈里,情人梁琴叫杰茜卡,頻繁變化的名字,折射了角色的不停變換,更是中國人這30年的精神變遷。中文說出我愛你,詰齒聱牙百口莫張,英文哎拉夫有,脫口就來,不是母語,像是戲言,自然少了一份責任的語境。人們一旦沒有面具,便對自己周遭的一切很難自信,心力交瘁大汗淋淋。這世界變化太快了,這個快得益于科技發明的迅猛發展,它使我們生命的年輪無法再勾勒出那一道道美麗清晰的弧線,像潑墨,但不寫意。有種觀點說現在哲學已跟不上科學,有失偏頗,他們將科技發明與科學相等同。科技發明并不一定具有科學的永恒性、普適性和唯一性,在博大的宇宙之中,它興許只是雕蟲小技,是一次抖機靈。而愛智慧的哲學恰恰與科學的本質相生相伴。所以,對更看重實用、濟世的科技發明,我們有理由說,在極端利益驅使下它還有可能成潘多拉的魔盒。
現代的西方靠著科技的發明,采取掠奪式的經濟發展,嚴重拉大了人類的不平衡,導致了近百年的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這個災難不能不說有科技發明帶來的責任。如果說冷兵器時代,人們還會在相互屠殺中筋疲力盡而休養生息的話,那科技時代,歇斯底里的精神病患者會瞬間毀滅地球。所以,《今夜去裸奔》里的主人公才會發出“人類不能這樣利欲熏心永無止境,到一定時候得將創新發明統統宣布為非法,就像取締邪教那樣見一個滅一個”的駭俗之言。
問: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發展更快了。相應的,城市也病了。如何讓城市生活更美好,文學家不能缺席,不僅要用文學來記錄城市的發展,更要表達你們的思考。從2007年到現在,三四年過去了。你還沒有新的作品問世,一定是蓄勢待發吧。能透露下一步作品的主題嗎?
郭潛力:我其實一直在寫,之所以沒有新的作品出來,一是我畢竟是業余創作,還要花很多時間去工作,去謀生,還遠沒達到“人生”的地步;二是發表一些作品后,已經沒有了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銳氣。我現在對文字充滿了敬畏,每一個字從電腦上敲出,總覺得馬虎不得,要反復推敲。今年應該會有一部新作出來,主題還是城市背景下的人物命運。
(本文編輯:謝